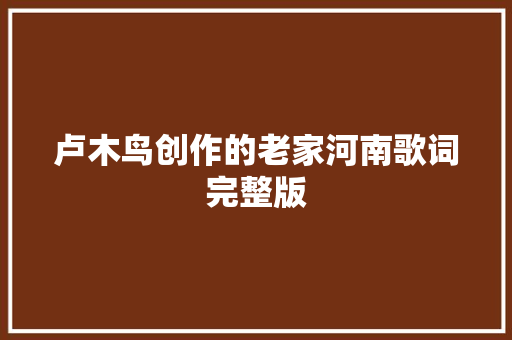盘绕在巍巍太行半山腰上的红旗渠,也像神话一样平常传奇。站在渠埂上,举头,是陡立千仞的峭壁;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渠水悬在半空,悄悄流淌,像一条天河。
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故事,出自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流淌了半个世纪的红旗渠,出自劳动者保持不懈的实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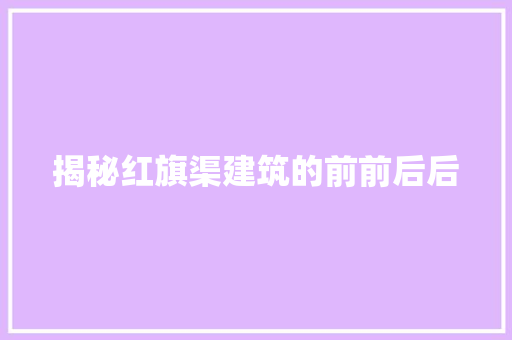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满地见告国际朋侪:“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培植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公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放诸今日,在英雄常被庸俗解构、空想信念会被现实消解的时候,红旗渠就像一个英雄主义、空想主义的符号,高悬在太行山上,让人仰望,更带给人精神力量的震荡。
水之困
蜿蜒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主干渠。
众所周知,红旗渠是为干旱缺水而修。带着这个印象去河南林州,不免会有一种预设:那里是一片干旱的地皮,黄土、丘陵、荒山该是常见的景象吧?
出乎猜想的是,坐在从安阳到林州的长途车上,沿途满眼都是绿色。路旁的绿化带草木葱茏,田里的玉米密欠亨风,一片墨绿。随风轻摇的玉米叶反射着阳光,田地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熠熠生辉。渐行渐近的山峦也被植被严密包裹着,活气盎然。
面前的林州看不出一丝干渴、荒凉之象,绿化、植被不输于任何一座北方城镇。每个林州人都自满地将这些绿色归功于红旗渠。
红旗渠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蕾当过多年的讲解员,还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述红旗渠。先容当年林州的缺水之困时,她可以信手拈来大量的故事、事例。比如林州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挑水吃。桑耳庄村落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落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落边去接,欠妥心把一担水倾了个精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上吊自尽了……
只是,这些悲惨、凄凉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听上去间隔面前的林州实在迢遥。红旗渠发挥浸染已经半个世纪,绝大多数林州人早已习气了它的惠泽。那个干旱缺水的林州,仿佛只存在于先辈们的讲述之中。
对红旗渠通水之前的林州更真切的认识,来自李蕾的一句问话:“从安阳过来的一起上,你瞥见水了吗?”
回忆一下,几十公里的一起上,竟然没有看到一条河流、一片池塘。在千百年逐水而居形成的北方城市,这么长的间隔见不到地表水,极不屈常。
但是,就此说林州没有河流并不确切。林州市境内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河流,均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只是这些河流都是时令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韶光处于干涸状态。而且,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边缘地带,即便是丰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区域能得到滋润津润。
大概是天意弄人,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变得丰沛起来。间隔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殷墟遗址就坐落在安阳的洹河之滨。
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更是难觅。地质资料表明,林州位于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西部地壳以上升为主,而且侵蚀成密集的沟谷,太行山东侧断层较多,地壳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样渗出着浅层基岩中的水分。
根据林州地下水勘探的资料,全体市域内,可方便开采浅层地下水的区域只有8平方公里旁边。别的地区的地下水,多贮藏于山丘区及盆地的灰岩地层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质构造繁芜,开采难度大,代价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开拓利用。
在红旗渠通水之前,林州最仰赖的水源便是雨水。这里的年均匀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区并不算很低,但受制于分外的地质布局,雨水降下来却留不住。“靠天用饭”的林州,彷佛很少得到上天的眷顾,雨降得多一些,便是顺着山势奔驰而下的洪涝磨难,正常年景之下,雨水会很快流走、渗漏殆尽。因而,干旱缺水就成了这里的“正常年景”,“十年九旱”成了最写实的描述。
干旱给林州祖辈留下了悲苦的历史。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多数岁月里,林州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据1995年版《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建筑之前,林县(1994年之后撤县设林州市)550个行政村落中,有307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落要跑5公里以上打水吃。林县每年因打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便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韶光,抛洒在那些漫长的打水山道上。
林州有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叫“荒年碑”,那是历代林州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落的“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回顾荒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去世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落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去世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那些干旱困苦的日子,随着红旗渠的滚滚水流而一去不返。而提到这条彻底改变了林州命运的人工天河,林州人都会带着感念提及一个人,“没有他,就没有红旗渠!
”
他便是当年的林县县委布告杨贵。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红旗渠工程中,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图为县委布告杨贵(前一)带领修渠大军上工。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中共林县县委第一布告。那时的杨贵年仅26岁,却是一个有着11年党龄的老党员。1943年时,15岁的杨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方武装事情。
成为林县县委布告之前,杨贵是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林县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干旱——此前半年,杨贵是安阳地委派到林县的抗旱保苗事情组组长。
而今的杨贵已是耄耋之年,虽满头银发,却身躯高大,精神矍铄,提及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仍是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
初到林县的一个场景,杨贵曾讲述过无数次:他带着事情组到马家山下乡调研,一起风尘仆仆。到了庄家家想洗把脸,主人端上来一个铁洗脸盆。杨贵瞅了一眼,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是半盆。这倒不说,这边厢洗着脸,那边厢一直地“叮嘱”:“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
杨贵说,林县给他这个年轻的县委布告准备了三道“杀威棒”:林县旱,林县生活苦,林县“要命病”多。
“要命病”指的是当地多发的食管癌、皮肤病、甲状腺等疾病。深究病因,还是由于缺水,饮用水水质差。三道“杀威棒”的根源便是一个:缺水。
林县的症结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办理的路子再明显不过——兴修水利。但是谁都清楚,这条路绝非坦途。林县的历史险些便是一部与干旱不断抗争的历史,千百年来未见本色改不雅观,新一届的林县县委能有什么善策?
杨贵到林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中央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发动各级党政干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气”。
所谓“摸大自然的脾气”,便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探求办理缺水问题的办法。
一场大兴水利的公民战役在林县风风火火展开了。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公民激情亲切飞腾,林县水利工程成效显著。
《公民日报》以《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为题揭橥长篇通讯,宣布了林县两年水利培植取得的造诣:“从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三四千年韶光,林县只有一万多亩水浇地……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韶光,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举动步伐灌溉的地皮达到23.7万亩。”
现在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气险些都来自红旗渠。而杨贵见告,其实在红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县就由于山区水利工程而有名全国。1957年的全国山区事情会上,林县被树立为全国范例,杨贵登台先容了履历,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当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扬林县捉住了山区事情的紧张抵牾,夸杨贵讲得生动,“有了水,闺女就往山上走,没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
带着全国山区事情会上的名誉和鼓舞,杨贵回到了林县。当年底,林县县委提出了比办理缺水问题更具气概的目标:“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成事在人”,是那个时期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这个不雅观点大概值得商榷,但在当时,这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培植新社会的豪迈宣言。
几年后,比林县更著名的全国范例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着回顾,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不雅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绝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概,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不过,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的操持之中,并没有红旗渠。杨贵回顾,那时候有很多叱咤风云的豪言壮语,像“让太行山低头,让淇、淅、洹河听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县境内。林县挖了英雄渠、天桥断渠、淇河渠等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建筑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库,水利工程的规模前所未有。
“护身符”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布告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高兴快地洗个澡。在水无比金贵的林县,沐浴都是一种奢侈。
刚把身子泡进澡堂子,雾气腾腾的浴室门口忽然有人高喊:“杨贵同道在里边吗?”来人是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杨贵赶忙答应。
高雷紧接着喊:“快穿衣服,有急事!
”
杨贵顾不上擦干身子,湿漉漉地套上衣服,就随着高雷上了吉普车。这时,高雷才见告他,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主席要和地、县委果同道漫谈。
回忆起那次与毛泽东的发言,杨贵至今仍难掩激动。他说,毛主席的话让贰心里有了底,这才敢连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
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经由全国山区事情的前辈范例,变成了“大跃进”的“后进分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紧张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事情”都没做好。
地委哀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勾引,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而附近的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前辈”。
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央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险些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培植无以为继。
见到毛泽东,杨贵开门见山地“放了一炮”。
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委布告,一见面,就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
漫谈开始后,毛泽东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卖力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公民公社的情形,杨贵据实回答。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阁下的人捏了把汗。非但如此,杨贵还当面向毛泽东“抱怨”起来:“林县这几年兴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长得很好。可是精壮劳力都出来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丰产却没有丰收。”
出乎猜想的是,毛泽东不以为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说着,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这之后,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公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缺点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这次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连续被提高。
但是在林县,由于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泽东的那次漫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坚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培植工地。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的大丰收,也印证了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发布,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被办理了。
但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已修的水利举动步伐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须要它们发挥浸染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干旱带着几分揶揄地见告林县人,林县的山河远没有如他们所愿地被重新安排。
引漳入林
红旗渠培植过程中的凌空除险作业。很多爆破事情须要在绝壁上打炮眼,工人们也是这个悬空的姿态。
此前几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却没能使林县摆脱缺水的命运。这些是“无用功”吗?杨贵不这样认为:“倒该当感谢1959年那场干旱,它让县委从陶醉中复苏过来。我们对林县境内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还是不足。这就证明只盯着林县,在家里打主张弗成,逼着我们去县外找水。”
1959年6月,林县的旱情日益严重起来。杨贵和县长李贵、县委布告处布告李运宝带队出发,分别沿着浊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探求新水。
这样的组合让有些不解,找水这件事何需林县一二把手亲力亲为?杨贵说:“水在林县是天算夜的事。要想干事,领导干部便是要冲锋在前,这便是我们的事情方法和作风。没有这种做法,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
三个找水小组,一起步辇儿,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小组都失落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
沿着浊漳河一起攀山而上的杨贵,却有了大喜过望的创造。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敷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彭湃。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时令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繁芜,支流浩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愉快得彻夜难眠,一遍各处用红笔在舆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详细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一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搜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
实在,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只有理解林县地貌,才能明白杨贵的苦衷。
林县的浊漳河从阵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培植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便是由于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地皮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赶过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赞许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申报请示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折衷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
林县是革命老区,战役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布告陶鲁笳就曾在林县事情,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操持一起绿灯。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也便是后来的红旗渠。不过,林县县委果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奉告: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期间的开始。此前罔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再加上自然磨难,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期间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合作。乃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蕴藉地进行了劝阻:“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的性情却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转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重新演绎一遍。
杨贵回顾,当时有领导私下里劝他,语气很不客气:“你林县有多大荷包,要包这么大的粽子?”杨贵答:“我们有55万人。”
不过,杨贵也承认,林县对引漳入林工程的谋划过程,确实太过乐不雅观了。
1960年的春节,林县县委没有安歇,一班人聚在一起做“算术题”。
出题的是杨贵:“引漳入林人工渠全长七万一千米,宽八米,高四米三,上七万一千人,每人承包一米,咱们多永劫光能修成?”
县委组织部部长路加林先表态:“老百姓盖五间房,也不过个把月,一人挖一米,也就三四十个土方,两个月怎么也干完了。”
县长李贵比较“慎重”:“山上石头不好挖,算三天挖一方,大概一百天吧。”
共识很快形成:引漳入林工程2月开工,大干三个月,争取“五一”建成主干渠。
千军万马战太行
排险队长任羊成在工地上的留影。他的门牙是被落石打掉的。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
近4万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搜集。
末了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也就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低落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赶过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军队,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职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微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觉得到了困难。
工程培植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增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这个“家底”中,最主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创造,有人反响到主管财贸事情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通情达理。”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杨贵说:“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
红旗渠真的是林县人用双手挖出来的。
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器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便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每每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珍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利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张。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身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落成后,林县才对全体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个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引漳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林县,立时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杨贵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4万人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而此前,林县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严重不敷,“五一”建成总干渠的目标本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布告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每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屋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能职员不足,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立时在工程总指挥部调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顾说,这次会有两个浸染,一是鼓劲,群众的激情亲切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灰心。第二是调度计策,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匆匆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度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浸染。在开工8个月后,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仅仅这一段,林县人就斩断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山头,填平了85道山沟……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地振奋着林县人连续修渠的激情亲切。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培植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终极得以全线贯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授予了一个更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为有捐躯多壮志
1966年,红旗渠干渠建成通水。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落去了一位主要的技能员——工程技能股副股长吴祖太。
在王家村落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涌现了裂痕。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疏松构造,为增加安全系数,卖力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响,洞壁上涌现了裂痕。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旧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真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
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职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便是由他担纲。
杨贵回顾吴祖太:“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杨贵至今仍清楚地记住吴祖太那张年轻、腼腆的面庞。
红旗渠选址详勘的过程中,吴祖太每天都在山上奔波。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期间的第一年,干部口粮是每个月29斤,不敷支撑每天繁重的野外勘测任务。一天,杨贵叮嘱食堂蒸了顿肉包子,慰劳大家。一群人吃得狼吞虎咽。杨贵问:“祖太,吃了几个?”吴祖
太不好意思地搓动手:“七个,嘿嘿。”
建筑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培植过程中,共有81人捐躯在红旗渠工地上。
红旗渠培植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培植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卖力人禁绝许,赵翠英说:“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事最小的培植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了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说的是干活不要命的红旗渠培植特等劳模任羊成。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打消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举为排险队长。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峭壁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贯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打消干净。这个事情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田地去打消危险。
“我‘去世’过五回。”任羊成说,“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不收我。”
这份危险的事情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过,没有摔去世,可是掉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永劫光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韶光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直到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了任羊成。这一次,穆青写了反响任羊成业绩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真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这便是红旗渠精神!
这便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红旗渠的红旗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心发出关照,全国实施“百日休整”,红旗渠被哀求歇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连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磨难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培植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心有令,林县不得不屈服,但并没有完备实行:绝大部分民工复临盆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连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中心哀求休整,是由于当时粮食紧张,停滞工程培植,全力担保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心指示要实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纵然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永劫光。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见告,在三年困难期间,红旗渠的培植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增援灾区。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常常派人下来检讨。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不雅观察哨,一旦创造有小车经由,急速挥舞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滞施工。等车走远后,又连续干。
这样暗度陈仓的“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还在大搞红旗渠培植,非常生气。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正在新乡开会,不但不认错还直言谭震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谭震林指示新乡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职,随后召杨贵到新乡开会,准备把林县树成反面范例。
到了会场,杨贵先接到了河南省委布告处布告史向生的纸条:“争取早发言,深刻检讨,争取主动。”
杨贵知道,这是史向生在保护自己。这位省委领导一贯尽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着红旗渠培植。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难的时候,史向生还曾登上峭壁绝壁上的施工现场,慰问青年突击队。
但是杨贵没有做检讨,而是感情激动地讲起了林县的干旱,讲起了55万林县人为建筑红旗渠的拼搏……
谭震林没有表态,会后立时派出调查组到林县理解情形。这之后,谭震林成了红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职务得到规复,红旗渠培植又得以大张旗鼓进行了。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培植项目。全凭独立重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培植,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始终满怀敬意:“谭副总理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形后,对红旗渠培植一贯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立时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均匀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
红旗渠培植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津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培植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去世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罢免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随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末了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公民日报》几位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响杨贵的情形,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建筑人工渠,人们常用开挖土方数来解释工程量,但在红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这样一组数字:削平山头1250个,钻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座……
红旗渠落成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形后,说话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独立重生,艰巨创业,联络协作,无私奉献。
修渠时,林县人靠着这股精神打消万难,勇往直前;渠成后,红旗渠勉励着中国人的精神,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四十多年过去,红旗渠汩汩流淌,依旧是林县最紧张的水源。在供水之外,红旗渠还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在这里,人们的日常所用,从小吃、酒水到住宅小区,处处可见红旗渠的品牌。
红旗渠修成之后,杨贵的命运在“文革”中风雨飘摇。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杨贵被调到北京事情,曾在公安部、农业部任职,1995年离休。
离休后的杨贵居住在北京方庄,他在自家院子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个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杨贵说。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3年9月10日
本期作者:董少东
【版权声明】本头条号所发布的内容,除注明来源外,均来自微旗子暗记“北京日报纪事”(bjrbjishi),版权均属北京日报社所有,任何媒体、机构或个人未经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帖或以其他办法复制发布或揭橥。违者将由北京日报社依法深究任务。
欢迎转发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