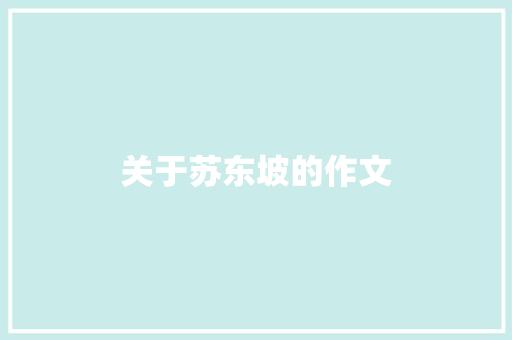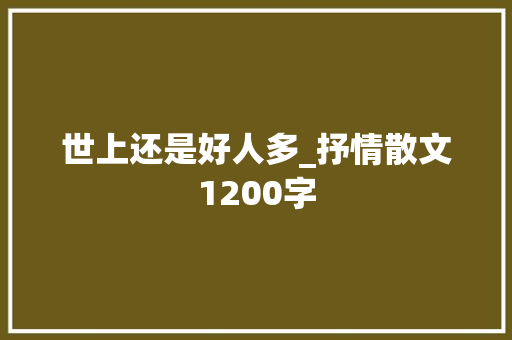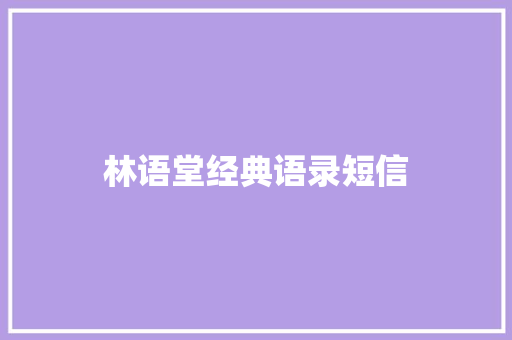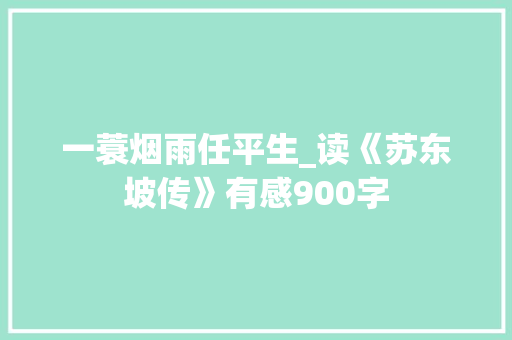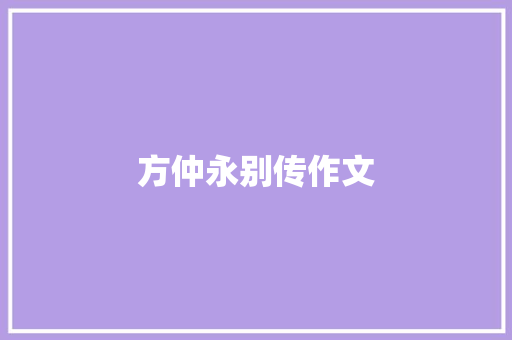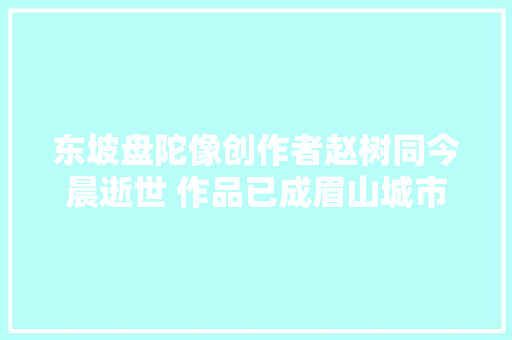“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这是王国维师长西席在《人间词话》中的定评。
实在,苏东坡从未自称文艺家,苏门中人亦反对类似说法,秦不雅观便认为,这是“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生命的末了一年,苏东坡给亲戚苏伯固写信,并未提及自己的那些“千古名篇”,反而称:“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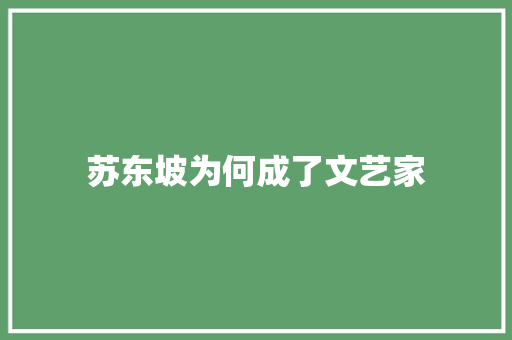
然而,少有人关注苏东坡的这三本书,《论语说》在南宋时便已散佚。
当然,不可否认苏东坡的诗、文、赋、小令、慢词、书法、绘画等均称当时一流。此外,他还是美食家、哲学家、实干家、诙谐大师……为何苏东坡如此多能?难道他是100个人的合称?
美国学者艾朗诺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揭出原形:只有一个苏东坡,只是先遭朱熹扭曲,再经元人涂改,后被明清文人集体误解……在文艺家这个镜像中,只有苏东坡的倒影,水波流动,一散为百,看上去无比丰富,却不真实。
真实的苏东坡究竟如何?本书呈现了接管美学的力量。
真正梦想的是出将入相
接管美学关注人物、作品被接管的过程。换言之,当我们提及苏东坡时,未必是他本人,而是我们共同误解的苏东坡,从干系研究中,可得启迪。
苏东坡生于1037年,1061年考中制科(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非常规考试)第三等。此试无一、二等,此前百余年,仅一人至三等。宋仁宗称:“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另一是苏辙)。”
显然,苏东坡是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以出将入相为人生目标。
为通过科举,苏东坡写过许多散文,包括《留侯论》《乐毅论》等“代表作”,他后来自评:“妄论短长,搀说得失落,此正制科人习气。”颇为不屑。
苏东坡看重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但生不逢时:北宋积弊已深,又逢王安石变法。从结果看,变法增加了民间包袱,官员数量从1067年的2.4万余人,增至1080年的3.4万余人。
可不变法又弗成,北宋养活125万军队,1065年时,军费占政府整年支出的83%,司马光的“节流”操持已失落败,宋廷不得不转向“开源”。
苏东坡意识到现实困境:“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并试图在理论上证明王安石错了。苏东坡创造,王安石信“心光”,节制了它,便节制了至理。“心光”高于感官认知,亦无法习得,只有集中央志,达到“一”的境界,方能悟到。
依据“心光”理论,王安石认为儒家经典皆不可靠,遂不遗余力,编出《字说》,试图从造字中理解古人深意,却搞成大笑话,比如:
姜(薑):姜能彊(强)御百邪。
富:同田为富。
贫:分贝为贫。
这些毫无证据的望文生义,被王安石当成“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于此书”,苏东坡挖苦说:“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怎么也实现不了的“理越辩越明”
王安石犯了一个常见缺点:将推论当成事实。既无逻辑印证,又无事实依据。
然而,苏东坡也不节制相应的思辨工具,致辩论只能在低水平的层面上展开——在王安石看来,苏东坡无实际事情履历,不敷与论;在苏东坡看来,王安石已陷入理性迷狂中,以为靠直觉能节制绝对真理,犯错亦无法自知。
苏东坡的见地不无道理,可他说不清楚,只好转向人身攻击,常以夹枪带棒的办法。见人收藏金石,他扯到“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于政”;朋侪赠茶,复书感谢,偏加上“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慵”……
苏东坡成功激怒了论辩对手。新党报复旧党时,苏东坡受害最大,差点去世于“乌台诗案”;旧党复辟后,苏东坡又是“元祐党人”中被贬最远的。
苏东坡自称:“余性不慎措辞,与人无亲疏……必吐出乃已。”个性凸显,本是“唐宋革命”的成果,但精神发展与现实未同步,他的好友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黄庭坚说的未必对:没有“好骂”,苏东坡岂能“文章妙天下”?苏东坡科举成功的那些文章,并无新不雅观点,只因用语锐利,被当成新不雅观点。宋代士大夫好辩,却做不到“理越辩越明”,反而造成私怨。苏东坡也未能免俗。
他首创了宋词的两个传统
在实际事情中,苏东坡实行力强、有远见、勤政爱民,却因党争,一次次被贬。在诗作中,苏东坡非常达不雅观,晚年被贬到广东惠州,他写道:“宣布师长西席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仇敌章惇看后大怒,说:“苏某尚尔快活耶?”
在诗中,苏东坡反复提到陶渊明,实在二人境遇不同。陶是主动归隐,苏东坡是被动流落。赞陶是为表达自己的快活,以激怒敌手。苏东坡写了很多参禅诗,但本日赞颂,来日诰日又嘲讽,表示不愿受约束。苏东坡还写了《前赤壁赋》等,极言达不雅观,可在私信中,他常流露出愤怒、迷茫、悲观的感情。
苏东坡把写诗当成战斗,后人常批评他的诗中乏情,可读者便是喜好。一方面,苏东坡找到了新的抒怀办法,看似参禅,实在饱含生命关怀;另一方面,苏东坡不想用诗来传情,由于他创造了词。
35岁前,苏东坡险些没写过词,他承认不懂音乐,且他的词每每唱不了。苏东坡首创了两个传统,其一,以词为自传,其二,将现实入词。这前所未有地扩大了词的境界,不论是否喜好苏词,都会承认它是独一无二、有个性的。包括书法与绘画,苏东坡都唾弃基本功演习,强调发挥。
被贬期间,苏东坡曾躬耕陇亩,为五斗米折腰,乃至遭遇过暴力……我是谁?我该向何处去?如何度过今生……苏东坡用词、用书法、用画来追问,由于它们的规范不严格,可为所欲为。
“制造苏东坡”是去世胡同
苏东坡去世时,好友道潜夸奖他经纶如古伊尹,辞章如班固与扬雄,雅量如东晋谢安,高才如诸葛亮,雄辩如子贡,识人如东汉郭泰……并没提到李白、杜甫。
朱熹时,笔锋突转:“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冲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妄,无所不为。”“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
朱熹不喜苏东坡,因苏东坡与程颐反目,称其诈伪,并当面戏弄程颐。朱熹恨屋及乌,乃至讨厌苏东坡的书法,他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朱熹意识到,苏东坡的诗影响巨大,只有予以策略性的承认,才能加上“都未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吟诗饮酒戏谑度日”之类的评判。在朱熹努力下,苏东坡成了有才无德的墨客。
元代文人走向专业化,个人发展被限定在文学上,不免仰望宋人的清闲,苏东坡遂成追捧工具,到了明清,人们更是只见苏东坡高度自我的抒怀办法,至于他的“治国平天下”,被彻底忽略,苏东坡终于成了文艺家。
“制造苏东坡”的代价,是让苏东坡难以理解——没来由的创造力、过分张扬的个性、玩世不恭式的游戏精神……名垂青史,仅仅由于他的“文笔好”,可这正好是苏东坡最反对的,他乃至提出:文章应句句有用,不必雕饰。苏东坡梦想建功立业,却意外成了洒脱、清闲、旷达、反内卷的代言人。层层滤镜之下,阔别现实的假苏东坡光彩照人,而那个愁苦、执着、诚恳的真苏东坡,还能否归来?
本书抽丝剥茧、针脚绵密,呈现了专业史学研究的睿智与诚挚。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多矣,我愿视这本为最佳。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