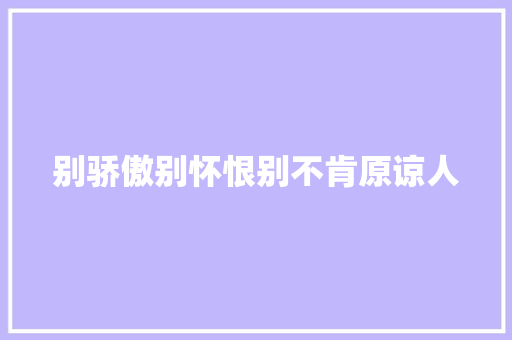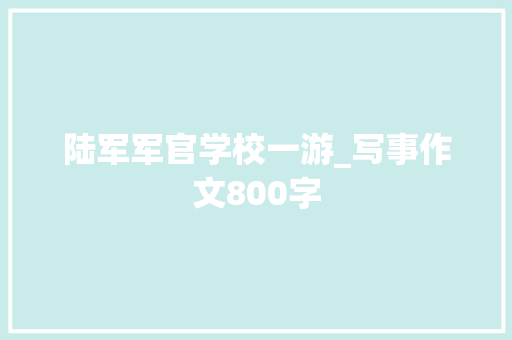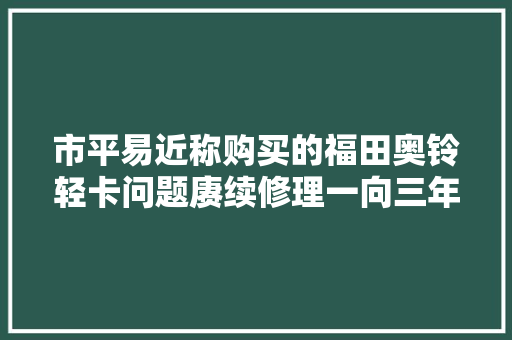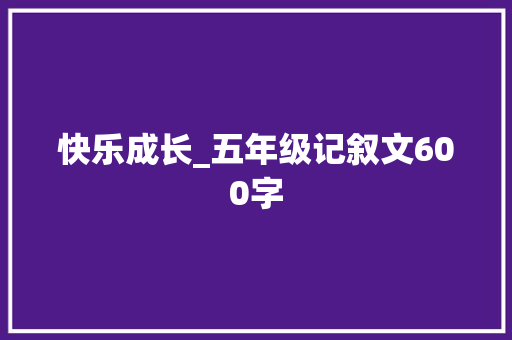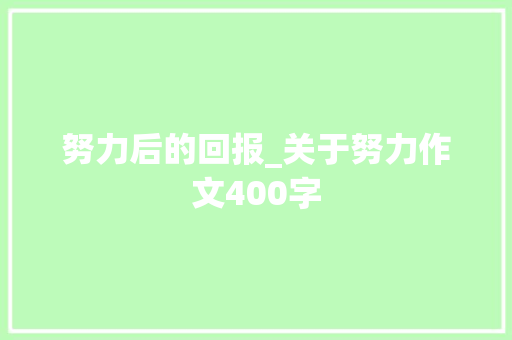我们的初中学校是公民公社期间遗留下来的几间仓库,八零年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建,开了窗户,镶上玻璃,差异于粗狂的青砖阔堂,又加盖了几排婉约风情的红砖瓦舍,居然也就成了一所远近有名的重点中学。
但是,置身其间,除了房梁上垂挂着的吊扇和日光灯管,统统都与堆放粮食前并无二致。这使得我在教室上打盹醒来又尚未复苏的时候总是感到光阴倒流,时期错乱,恍惚生产队的食堂又在敲铁开饭。这种觉得让人浑身霉味饥饿难忍,以是每当瞥见历史老师擦掉黑板上的勾股定理,涂上当代历史的时候,我就莫名地心力干瘪,愿望着尽快讲到小平同道南下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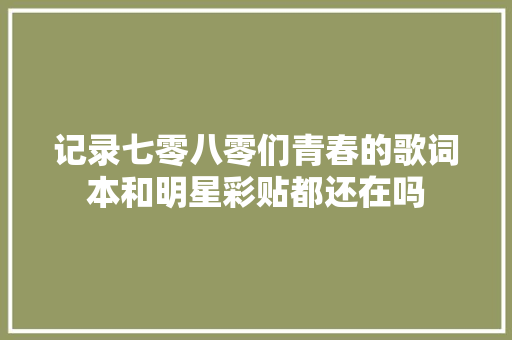
因而在那些光芒昏昏的粮仓里困难修学的日子,唯有数学老师临时客串的音乐教室才是我们真正感到快活的光阴。在那声宛如秋收叛逆枪声的上课铃声之后,我们个个如秋收后颗粒饱满的粮食般整整洁齐堆在课桌上,在霎那间穿越几十年的光阴,走进改革开放的妖冶春天。
我们彼此交流着喜悦的眼神,从桌洞里取出风格不一的歌词本,虽然也有音乐教材,但歌词本才是我们共同的盛行音乐启蒙和学霸条记。我们斗志昂扬斗志昂扬,摇头晃脑随着数学老师的指挥棒干嚎。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也不会忘却,初中音乐课的第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后来,音乐教室的指挥棒交卸到了英语老师手上,英语老师是邓丽君的虔诚拥趸,我们从壮怀激烈的革命歌曲一下子切换到了歌词本上的靡靡之音。有时候下午昏昏然的英语教室,英语老师也会回归客串身份,用歌词本上“一杯接一杯”的咖啡来点醒昏昏欲睡的“粮食们”。
和武功秘籍一样,歌词本也分配别,当然与“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的江湖流派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那时候我们能够买到的磁带也就港台和内地三大盛行音乐“圣地”。与少林武当领衔的江湖一样,歌词本的流派也是有鄙视链的,以台湾派封顶,以内地派垫底。我们一贯认为,兼职音乐的英语老师,除了邓丽君,该当还有满满一大本英文歌词。
那个时候,我们乐此不疲地翻着一盒盒磁带的封面,背面大多数记有歌词,但印刷模糊,间杂无数的错别字,是盗版与翻录双重浸染的效果,但它们在那个贫瘠年纪里也算得上一份别样温和的抚慰,让周遭的光阴仿佛一下子变得缓慢浪漫起来。到了初三,我终于也学会了安静和从容,默默地开始积蓄自己的力量,悄悄等待着自己十五年来最主要的七月战役。
但男生们显然还没故意识到中考的主要性,他们的家长倒巴不得他们中考失落利,家里那十多亩水旱轮作的耕地,正短缺卤莽如牛的劳力。当金庸的武侠小说被一次次搬上黑白电视荧屏,引领亚洲收视率的时候,我们小镇中学的风尚前沿也终于由记歌词变成了练武,所有的男孩子都在抱负一夜之间成为武林高手,于是,毕业班雄性动物们之间的攻击频率骤然升高起来,放学时分,总能频频撞见两个嘴上无毛的夕阳武士,在落日余辉里大展拳脚,决斗于围墙之巅。还好他们都没有捡到葵花宝典的秘籍,不然,我敢打赌一定会有重大流血事宜发生。而大多数女生则开始猖獗搜集黄蓉和小龙女们的彩贴,在封二整页和每一页的右上角贴上精选的彩贴成为歌词本的标配。
在这个月光淌过的夜里,仿若光阴缓缓走过窗外,我瞥见旧时往事如一张张古老照片,在夜色里一张一张淡淡漂洗出来。而现实戴着发展的假面,正不怀美意地雕刻着我的年轮线。疲倦迎面而来,我把自己埋进床褥里,垂下一双不再青春的眼睑,却依旧听得见,青春被韶光的车轮碾成碎片,只残留下那极浅极淡的一点点印迹,在中年梦里时隐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