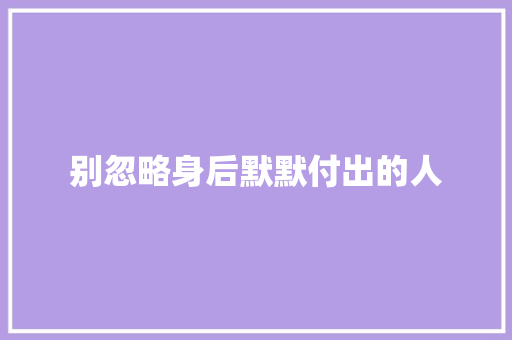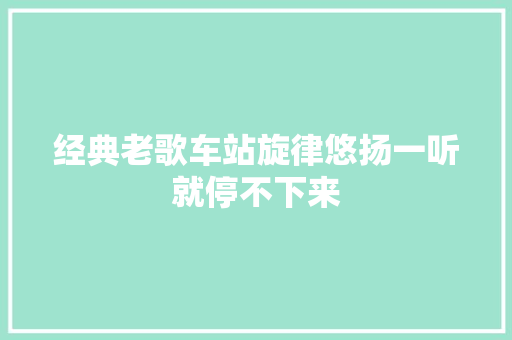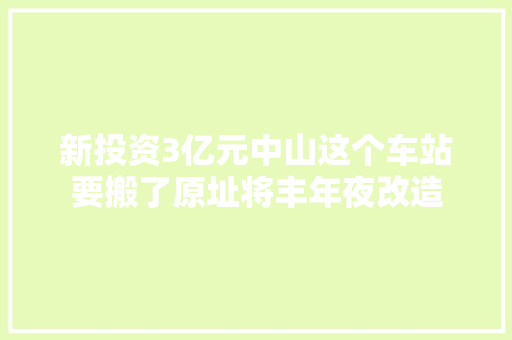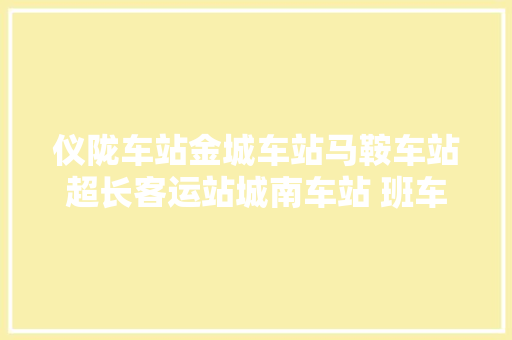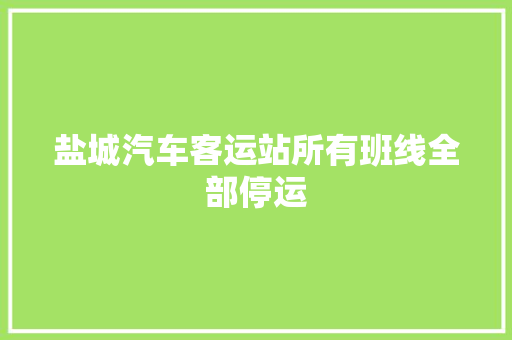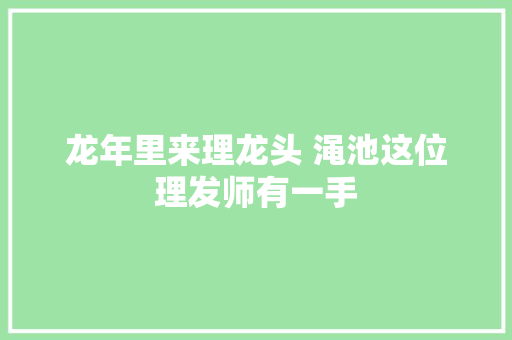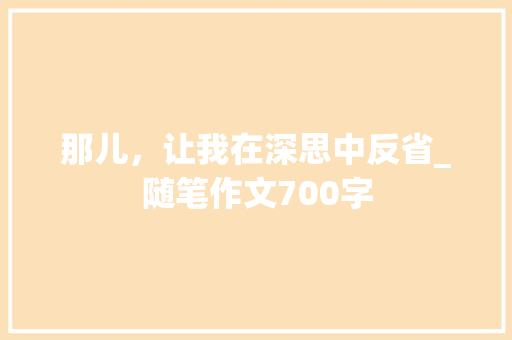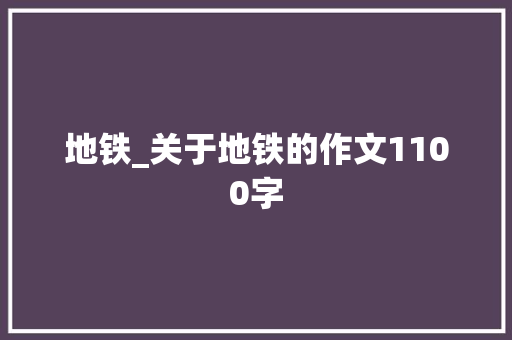注:渑池站,建于1915年,是陇海铁路上的车站。渑池站在陇海线上行间隔连云站759公里,离兰州站994公里。

昨天写了长达4000字的渑池老街,老同学爱军眼尖,说你不该漏掉渑池车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是很不应该。渑池老火车站位于百货大楼往东方向,详细位置就在一里河范围内,听说渑池车站现在还在利用中,有人说褴褛不堪,但这正解释它古老,有历史和岁月的味道啊!
渑池现在也有动车了,高铁车站彷佛设在果园乡,离县城可谓十万八千里。和梧州南站一样未便利,而老车站离老县城不到1公里,间隔新县城也不过3公里以内吧。
提及渑池车站,我也是有话可说有故事可讲的。我们县最主要的铁路是陇海铁路,我们家解放前就住在陇海铁路边。原来面粉厂这一片都是荒地和窑洞,时时还有野狼出没,爷爷用不知多少斤粮食换了几孔窑,不久邻居回民兰大爷紧挨着我们家也买了几孔窑,兰大爷比我爷还大几岁,听说是给火车烧锅炉的工人。孟春的爷爷老孟,对面的老刘,老王,老马,老张陆陆续续都不知从哪里迁移进来,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复兴街。复兴街和陇海铁路走向同等,都是东西走向,长度也就百十米,中间是条马路,南北两侧都是街坊邻居。
关于渑池车站,我印象中,民国期间就有了,但还不在现在的位置,老人说就在我们家不到三百米处,也便是复兴街的第一代居民我爷爷和老兰头原来便是看中车站附近的上风才到此安家的。民国期间我爷爷除了种地养家,便是在车站阁下摆摊卖胡辣汤,烫面角,他很会做菜,他的烫面角听叔叔姑姑们说是他的拿手绝活,该当算渑池最早的地方小吃了,放到现在他便是烫面角第x代非遗传人。最原始的车站我当然没见过,该当也很热闹,派头。
爷爷在世时也说民国期间渑池已经有铁路了,那时铁路除了运货,拉客,也运兵。不知是抗日还是内战期间,爷爷说只见一车一车的伤兵往西边拉。最残酷的是,到了渑池车站,伤兵车就临时停靠。有人到车上把已经去世掉的,半去世不活的,缺胳膊少腿的,奄奄一息的,从车上抬下来,就在铁路边的荒地里,挖个坑,就地掩埋。最惨不忍睹的是那些还没去世的伤兵被活埋时心犹不甘的呻吟和挣扎,这种事一样平常都发生在三更半夜。活埋伤兵之后,火车就窟咚窟咚开走了。爷爷赶紧拿上铁锨,锄头等工具到活埋的地方偷偷救人,挖开表层的土,只要还有一口气的,爷爷都想法营救。详细他也说不清救了多少伤兵,他记得大概有六七个在我们家养了好长一段韶光伤,伤势规复好的会帮爷爷加工胡辣汤和烫面角,等生活基本能自主就告别爷爷去找生路自求多福了。
几十年后,只有一个回县城找到爷爷表示戴德,但爷爷经由辨认回顾后,说他认错人了,自己没救过他。其他人都不知所终。貌似爷爷救人也没什么回报,但他本来也不图什么回报,他一辈子就喜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虽然脾气刚烈暴躁,吸烟又饮酒,但他还是活了92岁,这该是最大的回报吧。我爷爷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尾月生的,2001年10月3日驾鹤西去。爷爷说,民国时,他在车站卖胡辣汤,有带兵的国军头头见他身强力壮,仪表堂堂,曾奉劝他从军,他武断推辞掉了,他虽然年轻,已经是当家掌柜,家里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十几口人靠他顶梁,哪里能当甩手掌柜呢?此外,他虽然没经历过战役,但亲眼见过那些被抛弃的伤兵结局是何等悲惨,因此说什么他都不去从军了。现在不知渑池档案馆或者居民手里还有没有人保存有民国车站的老照片,那样我也能看看我家最初的样子,爷爷摆摊卖胡辣汤和救人的位置。
话说远了,再回到现在保留的老车站。昨天文章里说至今老街保留下来上规模的老建筑只有百货大楼不对,老车站也算一个了。这个老车站我预测该当是解放后才从我家附近迁居到一里河新建的。我们家离铁路还隔着一个粮食局的宽度,大约有六七十米这样子。紧挨着铁路有铁路局自己建的家属房,邻居黑月他爹是修道工,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他们家就住在家属房里,离铁路在三米以内,由于顶梁柱倒下,他们家孩子又多,印象中最少五个以上,以是整条复兴街他们家算是最困难的。一年四季小孩常常衣衫褴褛,流着鼻涕被陵暴。现在黑月爹妈估计都不在了,但听说他家的孩子都过得还不错,穷汉的孩子早当家适宜他们家。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岳立波住铁路边,他爸妈是铁路职工,他爱集邮,我用邮票换了他几十本小人书。
渑池车站对付儿时的我算是迢遥的地方,大姐大哥他们拾煤核常常去,而我那时走路都不稳,铁路都少靠近,更别说车站了。我印象里有次爷爷带我去洛阳二叔家住,堂哥堂姐他们都不怎么爱吃鱼,有顿饭配菜恰好是油炸鱼,他们都不吃,见我狼吞虎咽,他们把炸鱼都夹到我碗里给我吃了。当时吃得过瘾,谁料过后上吐下泻,切实其实止不住。爷爷便把我送回渑池,我记的是夜里到家的,我趴在爷爷背上,他背着我下了火车,沿着陇海线一步一步走回家门。车站的红绿灯一闪一闪,回家的路感到很漫长,旗子暗记灯的红绿光至今还在我脑海闪烁。我还记得家里东边老屋的电灯很亮,妈妈赶紧下厨给我熬汤滋补,而我拉肚拉得像一条软面叶,迷迷糊糊地感想熏染着家的温暖,大人的呵护。从那往后,我长达二十年旁边不碰鱼,直到来到南方,饭吃米,菜吃鱼为主,我也只好入乡顺俗,从星星点点到大口大口吃鱼了,不过,南方做鱼的味道清蒸为主,偏淡,我再也吃不到二叔家的油炸鱼的味道。
我终年夜后关于渑池车站的再一次印象便是父亲早上四五点钟送我去开封读书。那是玄月过了,初秋清晨,玉轮还没落,空气有点清冷,父亲扛着被子,我背着大包,沿着张村落铁路,一步一步一前一后走向车站。天亮前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铁路的红绿灯。越靠近车站,红绿灯越多,从三三两两到仿佛万家灯火一样模糊约约忽明忽暗,加上一动不动地停着又黑又长的火车,大抵就知道进站了。 渑池车站面积不大,还没有梧州汽车站大,也是一栋三四层楼的建筑,分前后两个门,前门是进的,对着一里河;后门是出的,对着站台。后门有检票口,和电影院、戏院的检票口差不多,是U型的铁栏杆围成的,出了后门,到站台,要下一个高高的台阶。然后再穿过两条铁路才到了站台。我影象里模模糊糊还有两三岁时爷爷带我去洛阳候车的画面,那时以为什么都大,车站有好多关于文革,关于毛主席,四大伟人的画像、宣扬标语,长长的绿皮车上有很多穿着很革命的叔叔姨妈,站台上还有很多只有火车站才有的好吃的。父亲送我上大学,那次火车是早上六点发车,绿皮车上人还很多,我只有站在过道上,连和父亲挥手告别的机会也没有,绿皮车就载着我去开封求学,也是踏上实现文学梦的旅途了。我读书第一年回家给爷爷买了一条红盒的汴京烟,给父亲他们买了开封的花生糕。
渑池车站平时人不多,前门口都是冷生僻清的,不像电视上中国式春运那么万头攒动。车站前门东侧实在有个侧门,也能走到站台,逃票的人有时便从这个口进出,它可以通到后门的下站台的台阶处,但有一个小门挡着,多数时候锁着,知情者每每从墙上翻越小门出站。也有人下了火车,不走正门,沿着铁路一贯向西走,走出火车站的范围,就可以成功逃票了。我读书时,有次火车也是清晨到家,由于买半票的次数满了,为了省钱,我们几个同学只买到义马,但车坐到渑池才下。这样半路上的查票不怕,又可以节约用度。一样平常到了渑池,也就到了自家的地盘,我们就有恃无恐了。谁知道,刚下车,站台上一样站着两个事情职员监督搭客通过检票口出站,当时我们大概三四个人。下了车,迅速兵分两路,我和一个学中文的沿着铁路头也不回一贯快走,其余一个化学系的上了车站台阶,立时向右拐,翻墙躲避检票。
我听到背后有人喊站住,我们不仅没站住,反而脚步更加飞快。化学系那个同学由于离车站太近,事情职员穷追不舍,我们是成功逃离了,化学系的老乡同学被捉住没有,不得而知,转眼现在二十多年又过去了,也不知他身在何处?名字记不起了,只记得瘦瘦的,高高的,挺文静帅气的小伙子。那年那月那天黎明我们一起坐过火车,逃过票……
爱军还给我发了一张现在渑池车站大门的照片,比以前俊秀多了,但老建筑还在,没有拆迁,没有扩建,也没有人隐士海,而且有了高铁,停靠普快的老车站门前恐怕更加门可罗雀了。绿皮车不知还有没有,我对外人先容家乡,除了仰韶文化,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秦赵会盟的故事发生地,再有便是我家就在陇海铁路上的渑池小站附近。小站在,家就在,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男儿梦也在!
2018.6.3晨龙行苍梧一指禅2021.1.7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