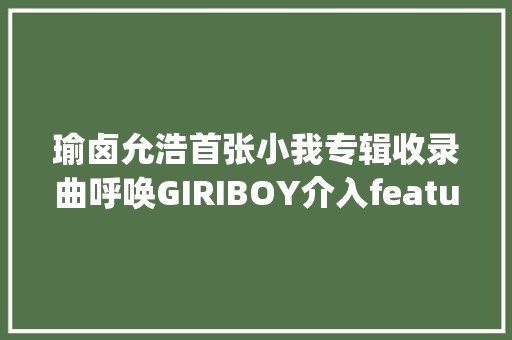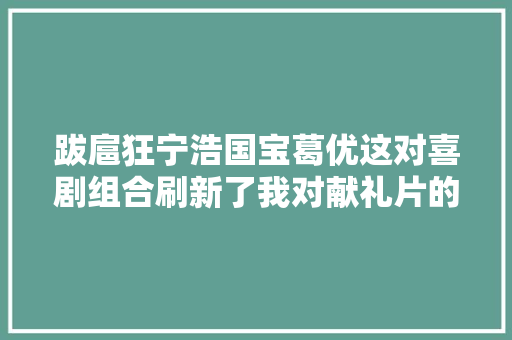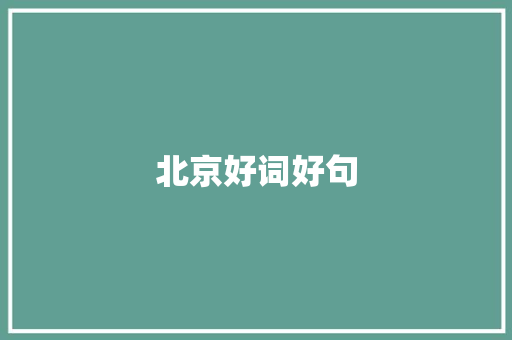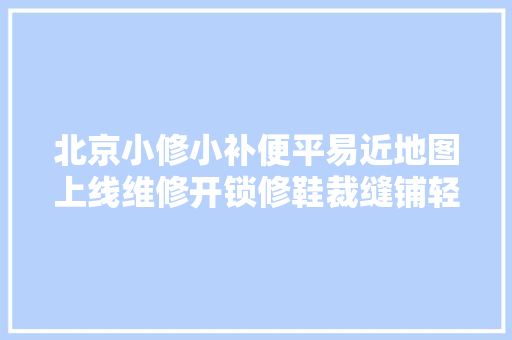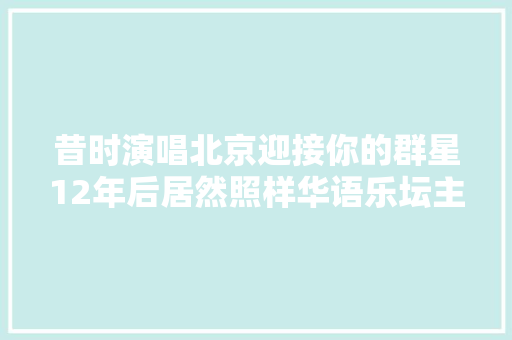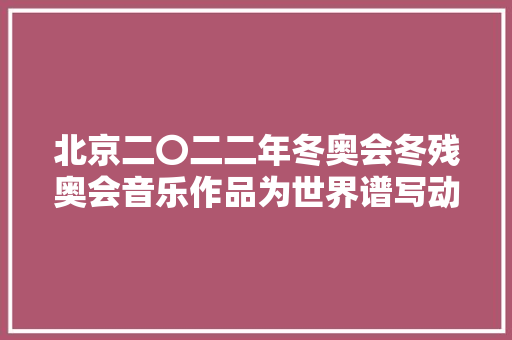当时,朱棣虽故意迁都北京,但迫于舆论压力,只能打着效仿太祖“中都之制”的名义,施行南京、北京的两京系统编制。
“中都之制”中的“中都”,在朱元璋老家凤阳,是明早期的三都之一。中都皇城是南京和北京的紫禁城原本,还比北京紫禁城大12万平方米。可惜的是,明中都培植6年即遭罢建,逐渐泯没无闻,连正史中也鲜有痕迹。

幸亏有精通明史和历史地理的学者王剑英,在“文革”下放时创造此城,为北京找到了“前世”。随着考古推进,这座被重新创造的中都,正成为研究明代北京城的一个主要参照。
明中都皇城航拍图
01.
穷县有个阔皇城
1969年,安徽省凤阳县黄泥铺村落,来了一位奇人。荒凉的村落庄公路上,他光着膀子,顶着寒风或烈日,常常跑上十几公里。当地的老乡大概从未见过这种景象,也没听说过马拉松,常问:“这人是不是神经有点毛病?”
这位跑者叫王剑英,是江苏太仓一名门王谢的后裔,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的末了一届研究生,公民教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辑。20世纪50年代,他曾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当历史舆图组组长,可见其学识渊博。
王剑英在凤阳宣讲明中都的历史文化
48岁是做学问的黄金年事,但在“文革”那个分外的年代,他却被下放到了凤阳教诲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磨炼。
干校学员每天写反省,作交代,接管批驳,还要干养猪等脏累的活儿。别人有此境遇,难免颓唐,王剑英却仍旧跑步、打拳、寻古探幽。他是明史专家,自然知道这里是朱元璋的老家,于是一有机会就到处探访。
盛夏的一天,干校学员到总部集中。王剑英听说离县政府不远,还有一座“老县城”,是清朝的凤阳县治所所在地。一个凤阳竟然有两座县城,王剑英以为蹊跷,便趁午后的空闲韶光前去查看。
明中都皇城城墙
走近“老县城”,他立即被雄伟的城墙震荡了。城南门内外须弥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内巨大的蟠龙石础,更让他木鸡之呆。凤阳是个远近有名的穷县,怎么会有这样一座雄壮威严,富丽精细的“老县城”呢?
登上南门的断壁残垣,他碰着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农,便打听此城的来历。老农见告他,明代开国,要在此建都,智囊刘伯温反对,建了都城而未定都,就留下了这座空城。
老人的话,王剑英并未当真。研究生三年,他师从邓之诚教授专修明史,如果在南京、北京之外,还有个都城,他岂能不知道?
其后,他又常常来到这里,不过不是来寻古,而是来拆城墙的。1969年是扒拆墙砖的高潮,“老县城”内外,人隐士海,砖垛从墙根一贯码到河边,一角五分一块的墙砖不仅在当地很抢手,而且还远销上海。当时凤阳新盖的公私建筑,险些清一色用的都是那种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11厘米,每块三四十斤重的砖,“五七”干校也不例外。
1972年元旦刚过,干校遣散学员,仅留下小部分有“历史问题”的人,转移至凤阳城内的干校总部,王剑英也在其列。
设在安徽省第四监狱内的干校总部,砖墙高耸,阴气逼人,王剑英却被周围的墙砖给迷住了。每当检讨交代的空隙,他就在监狱墙砖上探求笔墨,并逐一记录。
他创造,这些砖上刻有江西、湖广等明初数十个府县的地名,有的还有官员名和工匠名。这些地名砖、人名砖,大概是当时为了担保质量,溯源问责,而进行的标注。如此高档级的明砖,在北京都不多见,难道老百姓口中的废都真有其事?带着疑问,王剑英迈出了稽核明中都的第一步。
这一年,恰逢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馆,他被暂时调回北京,再次主持开馆前的舆图设计、绘图、修复事情。历史博物馆与北京故宫仅咫尺之遥,事情之余,王剑英常到故宫溜达,他创造故宫午门竟与“老县城”的南门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再仔细比拟,创造更是惊人:
我原以为北京故宫的建筑一定是全国最精细、最豪华的,是无与伦比的。可是竟然完备跟我主不雅观的想法相反:“老县城”南门须弥座上是绵延不断的、十分精细生动活泼的浮雕,有飞龙、翔凤、麒麟、奔鹿、双狮耍绣球,各种花卉和图案,而北京的午门仅两端有上点程式化了的图案装饰,别的全都是光秃秃的白石。
“老县城”的石栏板两侧都是精细的浮雕,北京故宫石栏杆两侧则全是光板,没有浮雕;“老县城”的石础是270厘米见方的蟠龙石础,而北京太和殿石础只有160厘米见方,没有任何雕饰,凤阳的建筑构件竟然比北京的精细,标准高。
1973年初,他作为专家参加了《中国历史舆图集》审图会,并借机在复旦大学查到了乾隆期间编纂的《凤阳县志》,这部书勾勒出了明中都的兴衰。
原来,凤阳那座“老县城”,只是明中都的宫城部分。洪武二年(1369年),42岁的朱元璋下诏,以临濠(凤阳)为中都,按京师之制,加紧营建。“功将完成”时,他却溘然敕令罢建。以举国之力,耗时6年营建的城市,从此成了一座废都。
此后历经天灾人祸,明中都逐渐埋没。清代,凤阳县衙曾经驻在中都皇城里,这里就被当作县城了。600年后,不仅凤阳人不知“中都”称谓,就连分管全县文化、文物的部门,也对明中都一无所知。
通过文献研究,王剑英创造,明中都曾经伟大奢丽,不仅有皇城,还有与北京相仿的三重城;不仅有宫殿,而且还有太庙、社稷坛、圜丘、方丘、城隍庙、元勋庙、帝王庙等坛庙建筑;不仅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等中心官署,还有国子学、会同馆、不雅观星台等文化外交机构;不仅有金水河、百万仓,还有许多开国元勋的宅第、宅兆等。
明中都皇城午门石雕
02.
一人重现一座城
遥想当年宫宇重重,再看如今荒草萋萋,王剑英不禁悲从中来。他意识到,这些国之宝贝,若不抓紧稽核研究,让它重见天日,过不了多久,连遗迹也将被毁灭。
为了揭开中都面纱,他向干校卖力人张健(后任中心教诲科学研究所所长)做了申报请示。张健破例赞许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稽核,还借给他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少了三米的大卷尺。此后多年,王剑英仍对此善举念念不忘,他常对女儿王红说:“如果没有张健同道的支持,《明中都》这本书就写不成。”
从1973年4月起,一位年过50的外地人,操着浓浓的吴音,到处翻砖头,搞丈量,逢人就打听凤阳的历史传说,成了当地一景。
王剑英在丈量石础直径
回顾起对王剑英的第一印象,凤阳县人大原副主任陈怀仁曾说:“只见全身灰尘的王师长西席身背相机、水壶,正用皮尺丈量明中都承天门遗址。不远处是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车阁下置一个化肥塑料袋,盛满了破砖碎瓦。当地干部背后揶揄他,这个人是高教部‘五七’干校的下放干部,神经有点问题。”
虽然看起来像捡褴褛的,但王剑英做的研究是高水准的。他根据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的传统方案思想,以及从明中都到南京、北京,明朝先后三个都城建筑格局的继承规律,以“小心求证”的研究态度,实地勘察、考证,印证明中都城墙、宫殿和皇陵的位置、长度、间距。
缺少测绘工具,他就围着宫殿和城墙绕圈,通过步数来测算间隔。如果是较大间隔,他就在车轮上扎上红绳,以数车轮迁徙改变圈数的办法测距。后来创造,他用“计步测距”和“自行车测距”土办法测出的间隔,竟与用当代仪器测出的结果完备吻合。
1973年国庆节期间,“五七”干校组织留守学员在安徽境内参不雅观旅游。王剑英则利用这段韶光,自费去全国各地查寻史料,以便与半年来的实地稽核相互印证。
当时没有检索复印设备,许多主要古籍也没有整理出版,为了在海量文献中探求有用的材料,他泡在图书馆善本室,抄录了20余本资料,“垒起来得有一米多高”。
王剑英的夫人陈毓秀在回顾这段时写道:
一度我们失落去了联系,我乃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南京还是在上海?住在南大招待所还是投宿哪个小旅店?或者已经回到了凤阳干校,白天骑着自行车啃着干粮咸菜拜访社员,晚上开夜车赶写他的稽核报告?
附近春节,“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大多回到北京过年了,仍不见到剑英的踪影。搬家不见人,过年不见人,他彷佛把我和孩子们完备忘却了。
知夫莫若妻,陈毓秀知道,“他是把他自己忘却了”,在那种忘我的境界中,不幸和非议,与创造带来的震荡和喜悦比较,又算得了什么?
刘建桥是当时凤阳县文化馆唯一分管文物考古事情的干部,他对“老王”早有耳闻,见面却是偶遇。
当时,王剑英正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与皇陵碑上的字逐一对照。皇陵碑高达7米,碑文是竖排的,他每看一行,便从木梯上爬上爬下一次。几个来回下来,50多岁的人,已全身是汗,短裤背心全湿透了。
这一幕打动了刘建桥,几经波折,他把王剑英借调至文化馆,专职稽核、研究明中都。研究凤阳花鼓的夏玉润便是这时在文化馆与王剑英相识的:
“那天,室外39度,屋内一无电扇、二无蚊喷鼻香,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师长西席,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赤脚插在水盆里,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明中都城考》书稿。为了防止汗水湿透稿纸,他在右臂下垫了一块干毛巾。桌上、地上摆满了各种书本、资料、舆图,他时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师长西席的情景,这一画面永久定格于我的脑际中,虽时隔数十年,恍如昨日。”夏玉润说。
从酷暑到隆冬,王剑英夜以继日地事情着,为的是与扒拆遗址者赛跑:从1973年到1975年,是中都城遭受严重毁坏的多事之秋。眼看地面下的大桥一条又一条地被扒拆,西安门遗址下的木桩被吊起堆积如山。他忧心如捣,“担心材料还没写完,遗址倒先拆光扒尽了”。
纵然是在撰写书稿最紧张的日子,凡是有单位请他先容明中都的,不管路途远近,韶光早晚,景象好坏,他都一律接管。只要听说城西公社水利工地开工,他必拍照绘图,拿出政策制止,讲述历史感化。
他的执着,看似无用,却让当地人逐渐改变了对“破砖烂瓦”的态度。一些机关干部得知遗址的新创造后,立即关照他,并陪同他一起赶往创造地;社员在遗址上挖掘出的龙瓦、凤滴水,也主动地送给他。
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终于脱稿。凤阳县有打字机、打字员的单位,都乐意免费替他录入。由于经费问题,书稿最初仅油印了150本,一部分送至省、地、县有关部门及领导,一部分由王剑英带到北京,送给国家文物奇迹管理局、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
很多专家熬夜读完了这本小册子,愉快不已,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评价说:“《明中都城考》实实在在比箫洵《故宫遗录》阐述元代宫室的贡献还要大,使一座已经埋没无闻的明代中都重新复活了。过去我一贯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的,现在才弄清楚原来连南京明故宫也是照凤阳明中都改建的。”
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国家文物奇迹管理局的重视。同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奇迹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高度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艺术、科学代价。1982年3月10日,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样平常而言,创造和研究一座城市遗址,是一项弘大的系统工程,从创造、勘察、宣扬、摄像、考证、绘图、撰写研究报告,直至争取国家认证,每每须要一个团队,数年功夫。而王剑英却在非常的历史期间,在没有研究经费,没有测绘工具和仪器,没有互助伙伴的情形下,赤手空拳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这本身便是个奇迹。
“冥冥之中,父亲之前积累的历史学、考古学、考据学、地理学、舆图学等多学科学养,彷佛都是为了探求、创造、研究明中都而积淀、准备的。”回忆父亲当年与明中都的相遇,王红感慨道,“这是不幸中的幸运”。
国家文物奇迹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剑英、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
03.
中都错失落帝都位
很多人都知道明代有北京、南京两座都城,但明中都却鲜为人知,连泰斗级专家单士元也对它“到底建成了没有,一贯模模糊糊,很不清楚”。这是何故呢?
原来,古代帝王实录“多书美而不书刺”,明代的实录、会典、纪传、碑铭等宫廷文籍,彷佛是故意隐讳,很少记载中都宫殿。景泰年间修《天地通志》,虽有“中都宫殿在(凤阳)府城万岁山南”的记载,但英宗复辟,《天地通志》亦废。
虽然史料少而分散,但《明中都城考》却旁征博引,将各种史料一扫而空。近年参与明中都遗址考古的故宫学者宁霄说,“很难想象,在没有电脑检索技能的年代,王师长西席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书本中找到这些资料的。近年虽然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明中都,但险些没创造新史料。”
明中都三重城
通过王剑英的《明中都城考》,这座被遗忘的城市找回了它的影象:
1367年9月,吴王新宫在金陵落成。第二年,朱元璋在新宫即天子位,国号大明。
此时天下已定,都城却悬而未决。朱元璋先给自己空想的定都地——开封(汴梁)一个“北京”的虚衔,并亲自勘察,准备建都。然而,那曾经繁华的汴梁城,久经战火,已是“人烟断绝、积骸骨成丘”。
开封被定为“北京”的第二天,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元朝灭亡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关中、洛阳、开封、北平、南京等地,都成了都城的可选项。朱元璋表面上与群臣切磋,内心却主张已定:抛弃已经培植得有模有样的南京,定都老家临濠(今凤阳)。
他的情由是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但究其根本,还是“圣心思故乡,欲久居凤阳”。朱元璋和他的乡党小伙伴们,大都是苦出身,现在有了富贵荣华,自然想要衣锦回籍。
中都是按照京师,也就都城的规格建造的,方案出发点自然非同一般:外郭城范围达到50平方公里,与元大都相称,而宫城达84万平方米,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大12万平方米。全城设104坊,各种衙署、坛庙、宅第一应俱全,布局建构可说是后来北京城的高配版。
众臣中排名第一的李善长是培植凤阳中都的总卖力。主持明中都考古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志说:“朱元璋常把李善长比作自己的萧何,李善长自然知道萧何建造未央宫的典故,在中都建造中一定会竭尽所能来谄媚朱元璋,这可能是明中都皇城穷奢极丽的主要缘故原由。”
在中都营建中,木材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附属国“求大木”;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根本,上面再垒砌大城砖;砌筑时则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浆,关键部位乃至“用生铁溶灌”;所有的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所有的石构建筑“华美奇巧”,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
明中都遗址出土的巨型蟠龙石础
营建中都的劳工,由全国征调而来。据王剑英考证,工匠近9万、军士7万、移民近20万、罪犯几万人、民夫45万,参与者总计近百万。
洪武八年,中都工程开工六年后,朱元璋第二次到工地察看,其间揭橥了祭告天地的祝文。祝文先是一大段忆往昔峥嵘岁月,然后又把自己的家乡夸了一顿,末了也感慨了一下工程“实劳民力”,好在“功将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鉴”,迁都意向已经非常明显了。
奇怪的是,就在朱元璋返回南京后不久,他溘然敕令“诏罢中都役作”。倾尽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在即将建成之际,戛然而止,这到底是为什么?史乘记载非常含混。
官方说法是,中都花费太多,不符合勤俭节约的治国方针。的确,朱元璋立国后,一贯标榜节俭,每天早饭,只是青菜加一碗豆腐,所睡的床铺,也和中等人家无异。可此时中都城已经修得差不多了,要花的钱差不多都花出去了,这时候说停建,不即是更大摧残浪费蹂躏吗?
王剑英从各种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认为,“压镇事宜”是中都歇工的导火索。
为了赶工期,民夫军士“病无所养,去世无所归”,作为反抗,他们在朱元璋察看时,用纸人木偶之类的东西,置于宫殿屋脊上进行谩骂。
此事让朱元璋蒙上一层厚厚的生理阴影,乃至两年之后,还“因工匠压镇,百端于心弗宁”。他在祭告天地时,特地后悔:“役重伤人,当该有司,叠生奸弊,愈觉尤甚,此臣之罪不可免者。”
还有一些明史学者认为,对淮西集团的戒备,才是中都歇工的真正缘故原由。
刘伯温是当初唯一反对建都凤阳的,他说“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缘故原由是“阵势曼衍”。用现在的眼力看,凤阳紧临淮河,随意马虎发生洪涝磨难,长期的水灾又导致地皮盐碱化,粮食产量低,且地处丘陵,非交通要道,确实不宜建都。
朱元璋起初听不进去忠言,但洪武八年,就在他从中都回南京后的第三天,退休老谋士刘伯温的去世讯传到了京城。他原来只是身有小恙,但吃了宰相胡惟庸的药后病情加重,撑了几个月就驾鹤西去了。刘的去世,让朱元璋对淮西集团加倍忌惮,假如到了老家,到处都是这些元勋们的亲朋好友,那还不彻底反了天?
罢建后,中都政治地位低落,经济冷落,被朱元璋迁徙来的大量人口,缺粮少食,只得唱着花鼓,逃荒求生。
关于“中都罢建”,王志认为,“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或许能供应新的视角。很多细节显示,中都皇城的完成度并没有想象的高,史料上对工程的记载,不用除是李善长虚报了进度。按照当时的工程标准和营建速率,要使中都成为成熟的都城,恐怕再用六年也无法完成。从这方面看,‘以劳费罢之’并非完备是托辞”。
明中都皇城外的护城河
04.
迁都北京弯曲多
明中都皇陵前的石像生
回籍建都失落败后,朱元璋耗时两年完成了对南京宫殿的改建。改建时,很多地方都沿用了中都规制,虽然较为朴素,仍颇有帝都气候。
本该安心当皇上的他,仍觉不称心。金陵虽虎踞龙盘,但国运不昌;吴王新宫“前昂后洼,形势不称”;填湖而建的宫殿随意马虎积水,这些缺陷都令老年的朱元璋不胜其烦。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意在稽核迁都西安的可能性,但又因朱标早逝终于作罢。痛失落爱子之后,朱元璋终极打消了迁都的动机。
至此,明朝建立已31年,都城在南京和凤阳间摇摆,汴梁和西安也是种子选手。但曾经繁盛的元大都、远在北方的北平,却从未纳入天子的视野,还成了民间传说里的“苦海幽州”。
朱棣迁都北京之前,这里只管是金元两朝的都城,但对付明朝廷来说,却并不是空想的建都之所。
谁乐意把都城放在离刁悍的蒙古部落很近的地方?谁乐意把都城放在一个已经被异族统治了四百多年,刚刚收回的城市?谁乐意把都城放在一个胡风文化深厚的城市?能做出这种选择的,除了朱棣,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
朱棣想迁都,缘故原由很多。有人说他的江山是抢来的,在南京做天子,内心难安。这恐怕有点鄙视永乐大帝了,多次北征蒙古,“天子守国门”对他而言,可不是一句俊秀话。大概,大元帝国缔造者忽必烈,才是他真正想要超越的目标。
他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从靖难之日起,就有了清晰的方案。登上皇位后,他知道迁都会引起很大的震撼和反抗,就用温水煮田鸡的模式,让反抗的力量逐渐平息。这种“只做不说”的做法,使得迁都北京和宫城改建问题,自明清以来就存在不少模糊不清,乃至相互冲突的说法。
作为建都的标志,紫禁城的营建始于何年?《明史》等史籍都说是“永乐四年”,300多年来,治史者对此笃信不疑。王剑英却在研究明中都的过程中,追根寻底,得出了“始于永乐十五年”的结论,并指出“永乐四年”只是“诏建北京”而未动工。他的《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令群儒折服,如今,这个结论已被史学界普遍接管和采取。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皇位还没坐稳,就把北平改为北京,称“行在”。同年,迁直隶、浙江等地的富户到北京,派工部尚书宋礼到南方准备大木,命工匠次年集结到北京。永乐四年,准备事情已就绪,为什么此时下了诏书,却未动工,反而又等了十年呢?
永乐五年,徐达之女、也便是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坚守北京城的徐皇后去世。借这个由头,朱棣巡狩北京,不到50岁的天子,出人意料的将陵寝选在北京昌平。
准备好的工匠和木料都投入到长陵的培植中,与此同时,北京增加了十个卫所,管理了大运河,修了城墙。这些,都是在为迁都做准备。
到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朱棣正式宣告迁都时,大臣们想反对,已经是有心无力了。朱棣这才开始建筑紫禁城,很多记录表明,元大内可能一贯保存到这一年,才“撤而新之”,彻底拆除。
永乐十五年,北京西宫建成。朱棣离开南京,坐镇西宫,亲自督建。十八年,紫禁城落成。十九年,各种礼制建筑也悉数竣工。
北京宫殿比南京更加轩敞、壮丽,虽然达不到中都标准,但也堪称建筑奇不雅观。永乐朝紫禁城的奉天殿,在本日太和殿位置,但好比今的太和殿大1.5倍,面阔达95米,如果保存至今,将是天下上最大的木制殿堂。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月朔,62岁的朱棣,在刚建成的奉天殿接管百官祝贺,北京由“行在”改为“京师”,进行了快二十年的迁都事宜,终告完成。
从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到1420年北京紫禁城落成,53年间,明帝国相继培植了中都、南京、北京三座都城,新建、改建了包含北京西宫在内的4座宫殿。近乎猖獗的都城培植,将微薄的社会财富耗尽,全体社会的怨气一触即发。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场神秘的大火点燃了建成不敷百日的紫禁城,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大殿化为灰烬。一向自傲的朱棣也十分惊惧,不得不像朱元璋一样为建都问题发布了罪己诏。
三年后,朱棣去世在北征蒙古的归途上,他的儿子朱高炽又把北京变成了“行在”,并方案“还都南京”。仅仅过了一个月,朱高炽就病逝了,他儿子、从小成长在北京的朱瞻基,碍于父亲的遗言,并没有规复北京的京师之名。
朱棣的重孙子朱祁镇登基时,北京作为都城的根本已很稳定了。于是朱祁镇因利乘便,进一步完善了北京的各项举动步伐,重修了“三殿二宫”。1441年玄月,北京的各种公函去掉“行在”二字,正式成为都城。至此,困扰明初统治者70多年的都城问题,才彻底办理。
我国历史上,迁都的事不少,但像明代这么能折腾的,仅此一例。明中都作为大明第一座表示帝王意志的都城,其城市方案和建筑设计,对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凤阳鼓楼
05.
北京与中都互为参照
明中都皇城出土的蟠龙石础
提起明代北京城的建筑,有无数民间传说,无论哪个版本,开头都要来一句“苦海幽州”。可见,元灭之后,这座曾经的国际化大都邑遭受了重创。
相传,朱棣派智囊刘伯温和姚广孝去建北京城,弹压恶龙。他俩暗自较劲,却不谋而合地听到“照着我画,照着我画”的童稚声音。两个人一想,这不是八臂哪吒么?结果,背靠背地画出了两张千篇一律的图,都是“八臂哪吒城”。
这个传说虽然流传很广,但北京城既不是刘伯温造的,也不是姚广孝造的,而因此元大都为雏形,在明代不断改造而成的。哪吒的三头八臂两脚,指的便是元大都的11座城门。
元大都的方案师是忽必烈部下的“和尚宰相”刘秉忠。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式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刘伯温、姚广孝的合体,民间传说大概由此而来。由他缔造的元大都,遵照《周礼·考工记》的王城制度,给北京留下了中轴线、胡同、大运河等宝贵财富。
占领大都后,朱元璋立即派工部尚书张允测绘了大都宫殿,编绘了《北平宫室图》。显然,这是在为兴建中都做准备。
“考古创造,朱元璋虽然提出‘驱逐胡虏,规复中华’的口号,并表示要复汉官之威仪,但明中都的城垣格局、皇城外T形广场、外金水河的布局、宫殿形制等,均与元大都有继续关系。”王志说,明中都承前启后,是介于宋元和明清之间,都城变迁中的过渡形态。
中都宫殿虽参照元大内,又存在大量创新。前朝部分除了主殿外,在东西两侧还设置了文华殿和武英殿两组院落,分别作为太子东宫和天子的便殿,以适应明朝的行政模式。
明中都皇城前朝宫殿出土石雕
最精彩的是,明中都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三朝五门”制度,转化为前导区,安排在宫殿之南。比较元大都,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间的间隔长了两倍,因此可以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摆下端门、承天门、大明门。同时,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移到了阙门之左;象征边陲版图的社稷坛,移到了阙门之右。这种布局,用一重重的墙与门,把中轴线上的皇威信严,推向顶峰。
城市考古专家徐苹芳特殊提醒人们把稳的是,在这条轴线的大明门位置,还涌现了一条宽阔的东西向大街,与南北轴线十字交叉,称为“云霁街”。这条街串联了中都城的钟楼、鼓楼、敬拜坛庙,俨然是本日北京长安街的雏形。
王剑英剖析,朱棣在少年时期,曾两次去凤阳敬拜皇陵,看到了营建中都的过程。青年时期,他又与兄弟一起到凤阳讲武练兵,在那里住了4年。因此,北京接管了不少明中都方案上的精华。
由朱棣亲自督建的紫禁城,叠合在元代的中轴线上,但向南移动,既避开了元故宫不大吉利的“地气”,也更趋近于改造后的北京城市中央。在单士元看来,紫禁城的布局和明中都类似,如午门、紫禁城四角楼、三大殿、东西六宫、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
永乐十七年,北京的南城墙自长安街的位置向南拓展到今前三门大街,这大大扩展了宫殿前的空间,中都宏伟的前导区也被移植过来,连洪武门、承天门这些名称都原样照搬。
中都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无山,则筑一土山,也名万岁山。这座山便是本日的景山,它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是平面上城市对角线的中央点。中都有日精峰,月华峰,北京紫禁城旁边,虽无山岭可命名,而宫殿之中则有日精门,月华门以象征。
元朝宫殿的南面,并无东西向的大道,中都的“云霁街”搬到北京后,改称“长安街”,这条路两端虽无钟鼓楼,但在相应的位置建了东单、西单牌楼,由此创造了城市的东西轴线。
嘉靖九年(1530年),规复明初天地分祀礼,建了天坛和地坛,其制度和方位都与凤阳明中都的圜丘、方丘相同。帝王庙虽然是在永乐营建北京之后100多年建的,但是从中仍能看到明初营建中都的影响。
明中都皇城中轴一线上的午门、承天门、外金水桥、洪武门遗址
06.
安徽与故宫联合考古
凤阳午门遗址
北京和明中都,是相互借鉴的两座城。在今日的凤阳城,还能找到北京城的源头。
凤阳城中,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洪武门、旁边千步廊、大明门、承天门、端门等位置依稀可辨,有些建筑已经复建。东西轴向的云霁街两端,钟楼、鼓楼相对而立。凤阳鼓楼建成600多年来,几经沧桑,屡废屡建,台基一贯保存无缺,基上柱础排列整洁,门洞上“万世根本”四个楷书大字,听说是朱元璋手书的。这座鼓楼基座长72米,宽34米多,是后来北京鼓楼规模的1.5倍,南京鼓楼的2.5倍,雄壮得令人震荡。
凤阳明鼓楼
明中都午门旁边,厚重的砖砌城墙尚余1100余米旁边;午门基台的白玉石须弥座上,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浮雕,总长达四五百米。这些浮雕高32厘米,深度达到3-5厘米。与之比较,南京明故宫的午门须弥座上只嵌有少量花饰,深度约1厘米,别的全是光面石块;北京的午门石雕,只有一个花饰,形象、尺寸险些与明中都一样。
明中都的别的地上建筑虽然都不复存在了,但留存的遗址格局基本保存完全,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宫殿、金水河、建筑、道路、水利举动步伐等。现在,为了保护这些遗址,凤阳城内建了十多处城市公园,随处是景、处处飘喷鼻香。
在明中都禁垣(相称于北京的皇城)地下,目前已勘探创造的夯土基址有137处,河道、水井、灰坑、道路、窑址等主要遗迹,勾勒出了建筑的基本布局。
随着明中都越来越有名,北京的一些地理历史爱好者,把去凤阳探求北京的“前世”,作为一种小众的玩法。长安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角楼等诸多称谓,让他们有种天然的亲切感。
明中都考古发掘现场
不过,就在几年前,明中都皇城遗址,还是一片“脏乱的旧城”。21世纪初,在房地产大潮的冲击下,明中都又到了泯没的危急关头:
太庙遗址、中都城隍庙遗址、开国元勋庙遗址、历代帝王庙遗址陆续被卖给开拓商;长春门遗址被铲平,建起了公路;洪武门遗址被革除一半,建起了公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雅观星台遗址所在的独山、明中都的主山凤凰山在数十年开山取石中,已是千疮百孔……
2013年是转机之年,那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获国家文物局立项,凤阳县政府也及时调度了《2010-2030年凤阳城市总体方案》,个中最大的亮点是,投入13.8亿元,将中都禁垣内的1308户居民、20个工厂、10个养殖场、4所学校全部迁出。
随着明中都的历史在城市培植中被展示出来,仅几年间,凤阳人对遗址的保护意识迅速提高:为了保护明中都的天涯线,政府调低了建筑的限定高度;一些已经卖给开拓商的遗址地皮又被赎了回来;各种遗址公园相继建立;从法律上保护明中都遗址的条例今年也将出台……这个城市正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灵魂。
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更可告慰王剑英的是,现存的明中都皇故城城墙,包括西墙、南墙的西半部,及较无缺的午门和西华门墩台,全长1350米,已经报告天下文化遗产项目,经专家现场稽核,初审通过,并列入《中国天下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明中都的全面保护和研究,正逐渐实现着师长西席遗嘱。”王志先容,王剑英在《明中都遗址稽核报告》中曾16次提到,须要勘探发掘来进行求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5年启动考古发掘,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2017年,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
明中都遗址发掘现场制作砖文拓片
最早的奉天殿什么样?明中都外金水桥到底有几座?天安门的雏形是几座门?很多问题都在发掘中得到理解答。
发掘确定,外金水河上为七座桥基,桥的宽度均大于南京、北京相应的金水桥,桥址的分布表示出井然的等级秩序。其余,桥基券石的卯榫结合部还创造多处有塞铁片或贯注铁水,证明史料所言非虚。不足为奇,北京故宫的外金水桥也是7座,除了天安门5个门洞对应5座之外,太庙和社稷坛还各对应一座桥。
承天门的城门布局非常独特,“三个门洞位于城台正中,城台两侧与禁垣墙连接,在城台两侧各开一偏门”。本日的北京天安门是5个门洞,王志认为,承天门“3+2”式门洞布局是唐代往后首次将5个门洞支配在都城第二道城的正门位置,或许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雏形。
在遗址公园内,前朝宫殿的发掘正在进行中。宫殿基址连续做了多年发掘,但形制却“越来越繁芜”,现已证明,宫殿台基绝非表面所见的“中”字形,而是更靠近元大都的“工”字形。不过,“要完备厘清宫殿及其附属建筑的形制,仍需进一步事情”。
从故宫到凤阳,宁霄以为“这里更能施展得开”。北京故宫考古慎之又慎,只能进行“微创”发掘,一样平常都是见“面”即停,也便是创造了主要的砖面、地面、活动面后就不再向下清理了。而且,考古发掘面积极为狭小且难有余地,一贯有“管中窥豹”“盲人摸象”的困窘 。而明中都考古,可以大开挖,这对付北京宫殿变迁、营建时序以及施工工艺、乃至哲学思想等都有启示。
对付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就评价道:“没想到这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全的根本布局,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根本布局、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明中都遗址发掘现场测绘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年夜众号 | 作者 孙文晔
编辑:曾佳佳 孙文晔
流程编辑 邰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