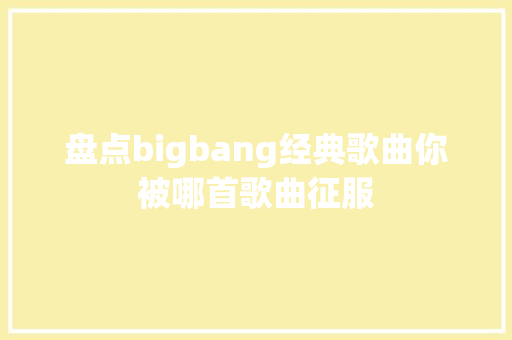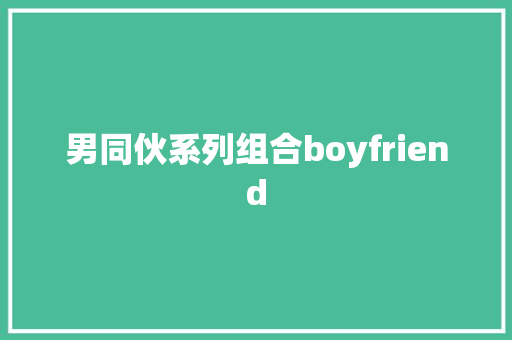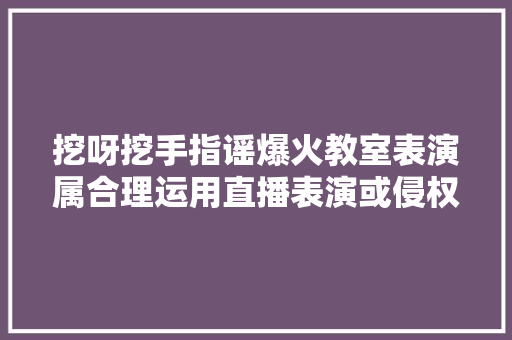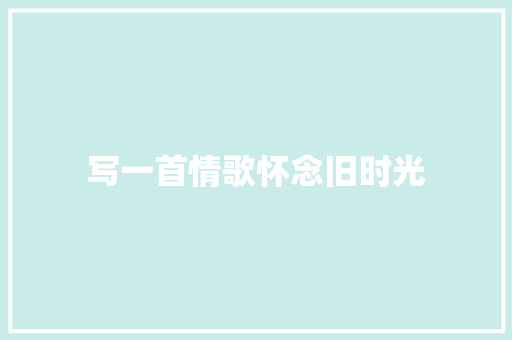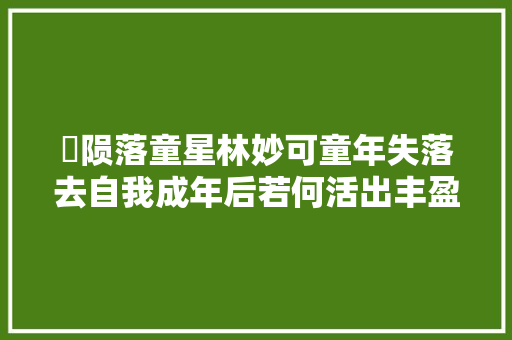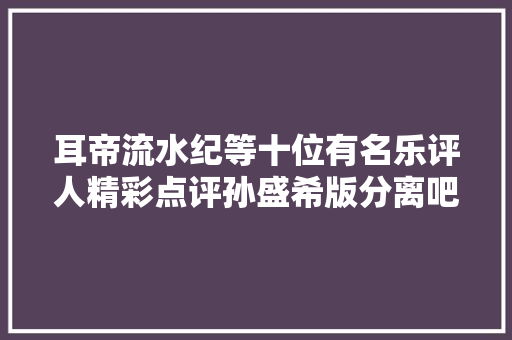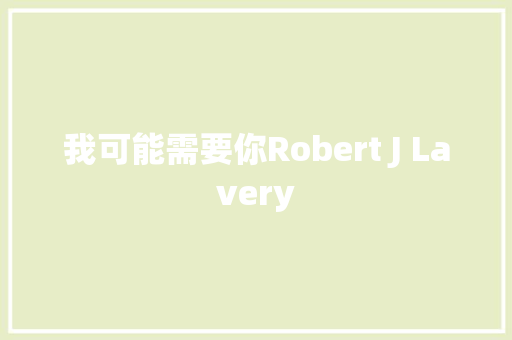继深圳宝安民工街舞队、山东济南农人工演出队等都邑民工演艺团体之后,“陕南旬阳花鼓演出队”在西安民间舞台的生动,日益受到农人工群体的关注。他们白天是工地上的打工一族、夜晚排练却是演员哀求,他们演出的地方小调,传承者家乡文化,也让更多的农人工朋友业余生活多彩起来,在融入城市生活时,在异域找到了归宿感,并把自己的风采展现在当代都邑面前。
街边民间大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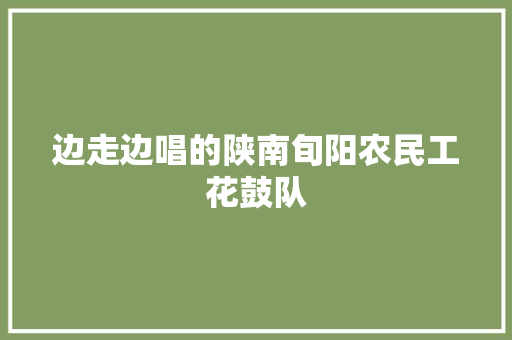
7月3日晚上七点半,西安市南郊三兆村落村落外的一处建筑工地边,照样又开始鼓噪热闹起来。刘世汉从他的那辆二手小面包上卸下响器和服装道具后,忙着将白底红花演出服妥善穿在身上。他是陕南旬阳花鼓演出队的队长,又是当晚演出的主持和男主唱之一,还兼负导演、道具和电工的重任。
沈固安和其他四位身着演出服的乐手,低头在车边一字摆开锣鼓,咚咚梆梆地调准定音;女演员张芳一边试着腰间绸带的松紧,一边当心地向四周放哨瞭望;用衣服掩蔽车窗的蒋思芳,嬉笑着催车内换戏装的女伴“快点,小心把身子走光了。”车内顿时传出尖叫和笑骂,惹得几位撑花纸伞,摇绸舞扇走场子的女演员也咯咯笑起来。
刘世汉将连接汽车电瓶的引线接上音响设备,举起发话器咳嗽了两声,算是给几位女演员重申了“队规”,接着面向不雅观众笑脸抱歉道:“我们条件是有点差,但演出不马虎。”然落后步嗓音宣告:“演员就位了,演出立时开始。”随即,热场锣鼓叮咚铿锵地敲响了他们的夜生活。
天色擦黑时分,路灯悉数亮起,灯光下的露天戏院已经围满了不雅观众,两边渣土堆上的草丛里,也散落着摇蒲扇赶蚊子的土著居民。马路两端不断有凌驾来携儿带女看戏的周边居民,人群外环形停满了带着安全帽晚归的农人工不雅观众骑来的电动摩托车,渭南白水籍农人工见告,再没这个演出队排练之前,自己和乡友们在这点,该当在饮酒吹牛或者打扑克、玩手机游戏。
戏院周边的工地随着夜色安静下来,耸立的高楼和伸向远方的塔吊在暮色中犹如给戏院挂起了背景,十米外往来在西康高速上的夜行车辆,也给戏院变换着舞台灯光。这个演出队队员都是清一色只会唱陕南花鼓子的进城农人工,他们白天从租住的城中村落民房内四散进入建筑工地上班,傍晚回家脱掉工服大略洗漱后,扒拉几口饭,再换上和城里人一样的鲜亮衣服,定时参加每晚的排练演出,直到晚上十一点闭幕。期间三四个小时是这些农人工演员一天最神圣的韶光段。
没有豪华的演出阵容,也没有强劲的演奏乐队,也没有深圳、山东等地农人工演出队的声誉,比较专业演员和剧团,这个根治都邑西安的陕南花鼓演出队还只是个“民间草场班子”,他们的演出全是免费的公益活动,演员们还要向工地请假,但由于拥有成百上千的粉丝不雅观众群,及每年十余场的外出演出,这个专唱陕南地方戏曲小调的演出队,在西安及周边市、县,依然小有名气。
演员都是农人工
去年尾月的一天,家住西安城墙脚下的陈昌文,在饭桌上碰着一位安康老家的熟人,便顺口问道:你该当会唱花鼓子吧,唱两句,我听听。熟人现场面对菜品和来宾编词,清唱了一段。“一听便是我小时候熟习的那个家乡小调味道。我40多年没听到了,眼泪当时唰地一下就流下来了。”
陈昌文祖籍安康旬阳县,5岁时随父辈移居西安周至县。此前他满耳朵都是家乡父老乡亲们传唱的陕南花鼓。在西安生活后,只有每年大年除夕夜百口吃团圆饭时,父母趁着兴致,才会相互合营清唱到大年初一的黎明到来。在60出头的陈昌文影象里,平时寡言的父母实在藏着一肚子的花鼓歌词。父亲呷一口白酒,严明的面庞在烟雾和歌声里逐渐松弛了下来,摇荡的油灯火苗映红了母亲的粗黑的皮肤,四肢随着身体的摇摆,像朱鹮掠过水面般轻盈。“我妈40年前去世后,我爸就再也不唱了。”
陈昌文还让这位熟人把唱得有名的小老乡刘世汉喊到家里做客,听了整整一个下午的陕南花鼓,并且建议把陕南花鼓戏在西安也唱起来,还专门为农人工写了一首花鼓新词。
刘世汉是安康旬阳人,在西安做拆迁工人,他从小到大便是在花鼓、山歌、孝歌、道情的曲调里终年夜的,耳闻目染和大人的教导,让他成了四邻八乡熟知的“好嗓子”。进城务工前,刘世汉就费钱置办了唱花鼓戏的锣鼓乐器,屈服陈世汉建议后,他首先在手机上为陕南花鼓爱好者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没想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只好升级改名为“陕南旬阳花鼓队”,成员一下子涨到上千人,不得不建立了第二群,而群友险些都是在西安打工的安康、商洛、汉中籍农人工。
岚皋县民主镇的张芳便是被“爱唱花鼓的网上朋友”拉进群的。开始大家在群里秀歌喉,得知刘世汉已经组织起十余个爱唱花鼓的在西安南郊搞起了排练,群友纷纭从网上走向线下,蜂拥汇聚在排练场展示自己的才艺,“陕南旬阳花鼓队”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刘世汉为此花了8000元置办了第二套乐器,在向妻子阐明自己的“败家”行为时,他不住强调:不吸烟、不饮酒都行,但不唱花鼓弗成。张芳为了排练每晚要从租住的西安东郊,化20元打出租车赶到南郊,她的丈夫对这种“发神经”到现在还是想不通。张芳则阐明,从小到大自己便是花鼓不离嘴,听到花鼓调,自己的魂魄都要飞起来了。
随工地迁徙的文艺部落
蒋思芳是刘世汉拉进群的,“便是想让她唱唱歌,心情能好起来。”陈思芳13年做了8次手术,现在还在靠药物坚持病情的稳定,身体虚弱的她常年闷在家里,既为自己的病情发愁,也为家庭窘迫的经济头疼不已。她常常失落眠、浑身乏力,腰疼腿麻。参加花鼓戏排练后,蒋思芳上述那些不舒畅,比过去少了许多,脸上的表情明显也快乐起来了。
花鼓队走出去演出多亏一位江苏老板的举荐。去年七月的一天下午,在西安南郊工地带工人垒墙的那位老板,向陈治柱等陕南工人提出可以提前放工,但是要听听他们平时干活时唱的地方小曲,直言为何对工人们能起到提神浸染,以至于陕南民工听了干劲足,连工程进度都加快了。
陈治柱和几位陕南民工相视一笑,他爬下脚手架,从行李袋里摸出一杆唢呐,其余几位民工也相继拿出钩锣、马锣等乐器,顿时在工地上奏乐演唱起陕南花鼓,引得正在干活的其他陕南籍民工们随声附和也唱了起来,这位安徽老板被民工们的“文艺范”震荡了。不久就推举陕南旬阳花鼓队到朋友在北郊的工地上去演出。
首场演出虽然有些小紧张,但还是演出队的“开门红”,在陕南籍民工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那往后,南郊三兆村落成了以旬阳人为主的陕南花鼓爱好者的俱乐部,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从北池头、岳家寨、月登阁、马腾空、茆家寨、新开门等西安的城中村落里,迁居到此。每晚的自娱自乐也逐步正规到专业排练,演员军队增加到60余人,经由筛选公认为有上舞台演出资格的有十余人。
55岁的田有柱是演出队最年长的演员,在老家他是远近有名的歌手,20年前到西安一贯干着抡大锤拆屋子的苦力活,他说每晚不唱花鼓浑身都不清闲,畅快淋漓边唱边跳两三个小时,晚上睡觉都比过去安稳多了。为了提高演技,他和老伴常常在屋子里切磋,有板有眼十分负责。
能够作为演员登台是每一个花鼓爱好者的最大声誉,三个月前,旬阳老家约请演员们还乡演出,“本来预定五位演员,没想到参演的坐满了四辆小车”。在县城一家酒店的舞台上,两组共32名演员们分太公、船客、邦船、丑娃、妖婆、掌灯角色在舞台上一站,台下不雅观众急速起身鼓掌,相互感慨,这么全班的花鼓戏阵容,现在春节时才不随意马虎能看到。
每个陕南人都要肩负传承重任
陕南花鼓是流传于民间的地方音乐,属歌舞型的小戏曲,腔调接管了南北戏曲艺术的诸多成分,唱词词格多为七言,亦有是非句的。演出与传唱多在举办灯会社火、迎神庙会、婚丧喜庆的时候。由于民性使然,从前间村落民走村落串户时,宗族之间、村落镇之间的演出军队时有相遇,两队之间以歌相会,以鼓乐相见,民间便兴起了即兴创作的“打对台”。歌词创作的越快,越及时、越辛辣、越能得到群众的叫好。歌手一张嘴就能串联起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风云,近年来花鼓歌词里还被歌手们加入了很多爱国利民、老实取信、孝敬父母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元素。至今仍有《薅黄瓜》、《十爱姐》、《十里停》、《新媳妇》、《找婆家》、《刘老六》、《盼红军》《绣荷包》 《放牛郎》等40多首花鼓代表曲目在爱好者中间口口相传。
谈及陕南花鼓的起源,民间人士长于搬出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有关富商之际,武王伐纣,巴庸派师参战。“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以此证明先民无不能歌善舞,所吟唱之曲韵久远流传至今,成为陕南花鼓主要一部分,可谓音乐活化石。
戏曲评论界认为,随着历史演化和当代艺术的冲击,陕南花鼓长期潜居村落庄劳动者之中,但是它演出方便,不局限场合,演员与不雅观念佛常融为一体,演到高潮时,不雅观众中也时时有人加入进去参加演唱。至今在陕南山区,年父老还有出门亮嗓唱花鼓的习气,一个有名的好歌手,便是村落组一宝。
“现在紧张是我们四五十岁这个年事段的中年人还在保留着这个喜好,年轻人彷佛更喜好盛行歌曲。”歌手张永武认为陕南花鼓措辞真切,贴近百姓生活,表现着山野人的朴实明朗气息,特殊是细腻的感情表达,有着婉约派诗词的风格。
“实在传统的花鼓演出军队还有骑竹马和狮子龙灯等,保留节目象滚绣球、上天梯、倒金塔、天下太平、全部上齐,没有130人就耍不开。”熟知陕南花鼓的旬阳籍人士杨厚根谈及花鼓队演出的主要性,他更认为“这会让更多的陕南人记住这乡音,把祖上传下来的这份文化遗产守住,不至于失落传,否则便是这辈人的失落职。”被评为“中国年夜大好人”后,他把一家企业褒奖给自己的3000元钱悉数捐给演出队,用于增长服装乐器,他说每个陕南人都要肩负起传承陕南花鼓的任务。
演员们见告,今年下半年他们作为舞台的那条培植中的马路就要通车,他们也该转移工地,演出园地又要探求新的地方,但陕南花鼓一定还会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