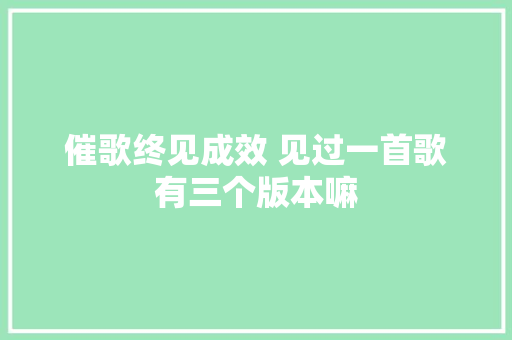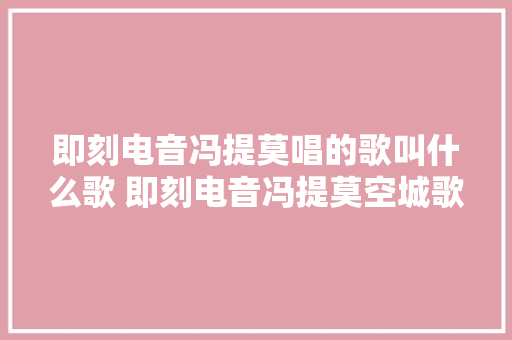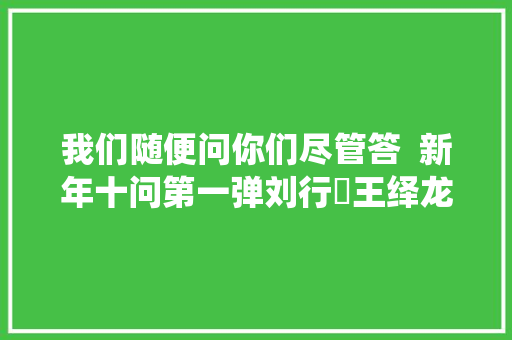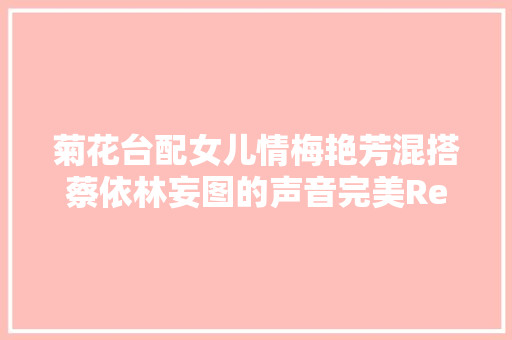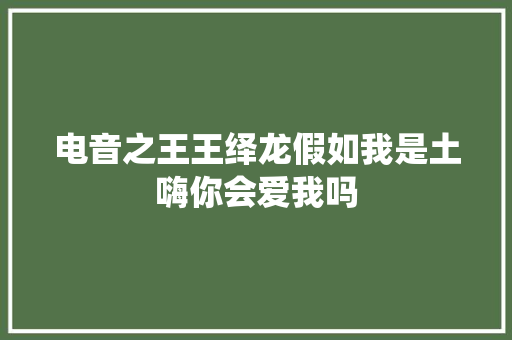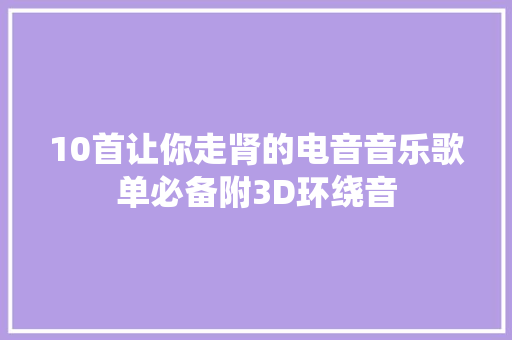5月,曾被称为“迪斯科女王”的张蔷,以她标识性的爆炸卷发涌如今了第三季《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连同那英都感叹“小时候听着你的歌终年夜”。在当下怀旧的集体感情中,她所代表的迪斯科的黄金年代彷佛昨日重现,为人们贡献了最为经典和古早的回顾。
作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启蒙,迪斯科曾经在1990年代旁边风靡一时,与之相伴的是舞蹈蹦迪这一娱乐形式及其衍生消费,逐渐进入大众生活。随着近三十年来的发展,迪斯科也经历了从地下到主流,从被淡忘到复古潮之后找到特定偏好消费者和消费场所的过程。

1980年代初,西方天下的新鲜事物一韶光涌入了中国,彼时的潮流年轻人与环球同步共享着一套盛行语法,个中就包含正在环球范围盛行的迪斯科。在此之前,中国依然是去性和去性别化的时期,迪斯科的涌现解放了身体规范,没有标准动作束缚、4/4拍“动次打次”的大略节奏,也使得舞蹈的门槛降落。
一韶光,承载人们伴随着迪斯科音乐舞蹈的的商业性舞厅也接连涌现,并成为都邑年轻人的一种主要娱乐办法。1980年由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布的一份关照显示,当时全国多个城市不断涌现以营利为目的的业务性舞会,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更是有达到上万人规模的舞蹈活动。
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迪斯科的盛行也惹出了一些争议。实际上,这份关照是一份“禁舞令”,迪斯科在当时被称为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迪斯科的观点不仅被官方误解,大众共享着相同而有限的文化资讯和资源,也曾一度稠浊迪斯科的界线。
“迪斯科最早进入大陆的时候,并不是纯洁的电子舞曲,而是一种类似于摇滚、盛行、city pop平分歧范畴的音乐杂糅体”,电子音乐乐评人电板鸭先容道。但无论如何,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能摇摆舞动起来的便是好音乐。
遭到官方封禁的同时,一些新的电子媒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着盛行文化的走向。越来越多人通过录音机和磁带、电台连续享受着全新的娱乐内容。《北京日报》曾宣布,对付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一台100多元的收音机须要花上两三个月的人为,一盘磁带则须要4、5元。但这并没有阻挡当时中国人拥抱娱乐生活的激情亲切。1979年景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仅一年就赚了800万。1984年,张国荣的一曲《monica》风靡喷鼻香港,很快这种迪斯科舞曲也开始通过无线电在大陆盛行开来。
在那之前,张蔷就已通过录音机收听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Billie Jean》,她曾形容“前奏一起来就想脱毛衣随着舞蹈”,并自此开启了对付节奏型音乐的审美和追逐。对付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人来说,张蔷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她代表了迪斯科乃至是内地盛行音乐的一段辉煌。
张蔷独特的嗓音被云南音像看中,1985年正式为她推出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公司支付了她1400元,而当时她母亲一个月人为才只有60元。《东京之夜》起初只制作了60万张专辑盒带,结果迅速卖到脱销,终极销量250万盒。而张蔷以翻唱为主的音乐生涯正式开始,凭借其音乐审美她所选择的翻唱歌曲每每也会受到大众的追捧。之后的两年里,张蔷发行了十六张专辑,累计销量超过两千万。1986年,十八岁的张蔷登上了美国的《时期》周刊,按销量评张蔷为环球最受欢迎女歌手第三位。
彼时,舞会也早已深入大众日常生活,成为主流的娱乐办法。而舞厅里播放的歌曲除了港台盛行乐之外,有不少有张蔷的翻唱。《千言万语口难开》便是当时的舞厅金曲之一,据张蔷所说,这首歌并非翻自喷鼻香港歌手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她听了英文原曲《More than I can say》后填词翻唱的。
那时候华语乐坛相对外洋市场还很匮乏,版权体系也未建立,很多时候借由国外的前辈生产力就能制造出传唱度极高的金曲。个中不乏一些“本土化”十分成功的案例。广州墨客黄蒲生将Modern Talking歌中的路易兄弟,转换为在中国城市与县城大街小巷的“路灯下的小女孩”,其迷惘而励志的形象乃至超过了原版。包括那首后来火遍全国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先由台湾歌手高凌风翻自欧洲舞曲组合The Nolans的《Sexy Music》,再有费翔在1987年带上春晚舞台的。
而无论来源何处,这种节奏轻快的音乐类型深受年轻人喜好,那个期间上映的电影中也时常有人们跳交谊舞与迪斯科舞的场景。贾樟柯年轻时也热爱迪斯科,被称为“夜店小王子”,后来他又在执导的电影中一次次重现舞蹈场景。
1987年,官方发布《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关照》,认可了社会办舞会的合法性。而这一年张蔷发行了一张名为《洒脱地走》的新专辑作为告别,她以为“当时自己能够翻唱的曲目都已经翻唱的差不多了,而原创的歌曲大多数都不是那么好听”,决定告别歌坛,出国看看。
到了1990年代,商业进一步参与了大众娱乐生活,大中城市里涌现越来越多的迪斯科舞厅,勾引着文化消费。仅在上海,商业性舞场的数目从1985年的52家增加到1990年的310家,1994年的1022家,1996年的1336家。个中1992年开在上海市中央一家名为“JJ”的大型迪斯科舞厅十分受欢迎,票价很贵,每天仍旧吸引了一千到两千名顾客。两年后,北京JJ迪斯科广场、莱特曼迪斯科广场、NASA迪斯科中央,这三个纯以跳迪斯科为经营项目的娱乐场所成为了都城年轻人的新去处。
盛行文化的回潮就在张蔷宣告远走澳大利亚的同时,崔健开始带领摇滚乐成为新的盛行风向标。张蔷曾在返国准备复出时听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她预先意识到,“崔健挡不住了,崔健的时期来临了”。之后摇滚乐确实开启了它的黄金十年。另一边,港台盛行音乐也凭借其成熟的唱片企划体系,向内地运送来大量的原创金曲,并打造了“四大天王”、小虎队等一众歌星,张蔷已不再是年轻人的心头好。
当迪斯科不再是主流音乐形式,舞厅作为一种老式的娱乐场所也逐渐被代替。在房地家昔时夜规模启动的21世纪初期,ktv和夜总会成为了新的娱乐消费空间。同一期间,以迪斯科为养分逐渐发展出的techno、house等电子音乐细分类型,分解出了更垂直小众的电子音乐俱乐部,以地下的形式延续着。
一如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迪斯科是一种潮流的地下文化,并未被主流所认可,如今在club舞蹈的年轻人也依然属于小众群体。然而,曾经不被主流所接管的张蔷如今已经成为了追忆八十年代和迪斯科的一种符号,站在最具流量的综艺上。地上与地下,当下与曾经形成了某种呼应。
作为电子音乐和派对文化发展都非常超前的城市,成都年轻人舞蹈的激情亲切并不亚于上海、北京。不同的俱乐部都有各自代表性的风格类型,身处个中的人也代表了不同的生活办法。比如.TAG是比较纯洁的techno俱乐部,2014年3月开业,与.TAG同期主导成都地下电音场景的,还有魔方大厦内的NASA、Here We Go。Nox是比较受欢迎的黑怕俱乐部,方糖和Axis相对综合,根据不同的活动主题划分音乐类型。圈子内DJ之间有一种隐形的晋升机制,都须要得到一定认可后才能登场这类老牌俱乐部。
但这类地下俱乐部的受众毕竟还是少数,纵然这天常运营都要花费不少心思。平时门票50-80元一张,纵然有豪华阵容,门票客单价也不过百元旁边。曾经一度,.TAG承接着大量外洋DJ艺人,最多的时候一个周有四个国际DJ出场,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本钱。现如今受到疫情影响,线了局景的经营更是如履薄冰,一旦碰上永劫光的封控,很有可能就由于无法承担房租而停业。
也有一些老牌俱乐部由于其他缘故原由末了消逝在了市场上。北京灯笼俱乐部是一家主打Techno风格的电子音乐俱乐部,2009年底在三里屯的3.3大厦开业,又在2010年搬到了工体西路。这家俱乐部承载着一代音乐人的生活,一贯推动着北京和海内Techno的发展。但随着工体迎来三年重修,灯笼等一批开在工体的club也在2020年集体撤离。值得光彩的是,今年6月7日,老牌techno club DDC正式回归,和去年十月重新业务的DADA一样,在日坛附近选址。
等到张蔷再度涌如今大众视野,已经是2008年。那一年,张蔷首次涌如今了央视这个主流媒体上,拍摄了欢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专题记录片《征象1980》,当时的编导陈晓卿为她安排了独立的一章,称作《风起张蔷》。同年,出道24年的张蔷在北展戏院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虽然不雅观众席饱满,但更多因此怀旧的标签吸引曾经的那些乐迷,彼时的张蔷还未有与当下对话的能力。
《吐槽大会3》上曾有一个段子,形容张蔷就像一种神秘的天文征象,每隔十五年降临一次娱乐圈。事实上复出五年之后,张蔷签约摩登天空,在发行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后又重获了一批年轻乐迷。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曾是张蔷在八十年代浩瀚的拥趸之一,他曾说“张蔷是我偶像,我该当为我偶像做点什么”,旗下的新裤子乐队担当张蔷的制作人。
新裤子曾在2006年发行过一张充满迪斯科元素的专辑《龙虎人丹》,个中收录了庞宽在九十年代写的《Bye Bye Disco》。为张蔷制作专辑时,这首歌又重新被张蔷翻唱并收录在《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中。
乐评人张晓舟称这张唱片是“中国盛行音乐史的一个经典企划”,“一次成功的复古式营销”和“启蒙时期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回潮(retro)”。而所谓回潮,是通过对旧时期亚文化和盛行文化的回收利用,再造新的潮流。他还提到,这张以怀旧为题材的专辑,与其说是张蔷在追忆八十年代,更像是新世纪的年轻人对八十年代的想像。
作为一位翻唱歌手,张蔷每每选择的是好听的音乐,并非局限于迪斯科曲风。其余,早期的迪斯科演出是乐队配置,并没有太多的合成器元素,键盘的占比也不大。直到后来,以迪斯科为养分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电子音乐细分类型,迪斯科才逐渐和电子舞曲画上等号。张蔷曾在接管采访时说过,“实在迪斯科是80年代的说法,迪斯科便是一个老爷爷,有子子孙孙,像电音啊全是迪斯科根基,迪斯科一贯没有离开。”
专辑中《别再问我什么是八十年代》的歌词所提到的一些意象与张蔷的真实生活关联并不大,但这并不妨碍张蔷在那之后,以“八十年代迪斯科女皇”的身份重新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同时形成了一股复古风潮。
电音节、互联网和综艺文化征象直接影响的便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当迪斯科被纳入电子音乐范畴之后,全体电音市场的发展同样值得关注。
不同于圈层化的club文化,电音节的场景能够承载更广泛的内容和成规模的消费者,人群的基数使得消费总量有所保障,极强的现场氛围也能够制造客单价更高的感情消费。2016年,全国共举办了34场电音节,一年后又增加了近20场,到了2018年,市场上已知举办的电子音乐节更是超过了150场。成本市场曾看好电音节的潜力,在2016年前后有过多起千万级的投融资事宜,很多大型电音节之后几年也陆续被引入海内。
麦爱文化2017年10月完成千万级公民币A+轮融资,亚洲星光娱乐则得到数千万元B轮投资。到了2018年,上海热波传媒还曾以主理方的身份,将环球三大电子音乐节之一的Electric Daisy Carnival(EDC)引入中国,并在当年举办了首场EDC雏菊电音嘉年华。
不同于国外发展成熟的电音节模式,海内电音节的票房收入远远不及资助收入。像EDC上海,以及三亚ISY音乐节,收受接管不雅观众都在5万旁边,与国外的Tomorrowland、EDC音乐节40万的不雅观众量级有很大差距。热波传媒CEO何诗杰曾在采访中表示,品牌资助大概占到收入四成,其他则是卡座酒水、以及票房收入,假如能担保票房收入在三成高下,音乐节就不会亏很多。
2018年的EDC音乐节,热波投入本钱在几千万旁边,个中艺人本钱大概霸占40%,而为了达到最佳视听效果,复刻国外现场艺术装置、娱乐举动步伐、舞台搭建等用度则是更高的投入。沈黎晖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电子音乐节的竞争特殊激烈,而外洋DJ霸占了紧张的市场份额。
除了演出公司之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凭借其上风开始布局电音业务,以音乐为触角链接更多消费者。2018年,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联合索尼音乐打造电音厂牌Liquid State,并与李宇春、谢霆锋、Alan Wlaker等达成了互助。
同一年,网易自创的电音品牌放刺FEVER宣告上线。放刺除了早期在网易云音乐上建立电音歌单、在B站上传教学视频以外,还在公众年夜众号上进行电音知识科普,低廉甜头电音文化记录片。去年一月,放刺在上海开设了其品牌下的首家电音文化体验空间9号俱乐部(No.9),意欲打造电音生态的闭环。但由于受到疫情等方面的影响,NO.9在去年十月又更名为“NO.9云音乐派对现场”,由放刺与网易云音乐共同经营。
据IFPI数据,2019年电音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排名第8位。《2019中国电音市场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环球电子音乐年产值估量将达89亿美元,中国电子音乐用户规模将达5.3亿人。然而,2020年爆发的疫情以及其持续的影响,对极度依赖线下消费的电音市场有很大打击。一个显著征象是,2020年之后海内大型电音节的数量锐减,更没有研究机构和干系报告将目光聚焦在电音市场了。
迪斯科和电子音乐干系的活动如今不再像八十年代时被剖断为造孽违禁,爱好者也可以在电音俱乐部、电音节等场景自由消费和穿梭,只不过,电音市场也并未能如此前所期许的那样真正爆发。或许电音还须要韶光找它的位置和受众,犹如张蔷十多年前复出时所经历的那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