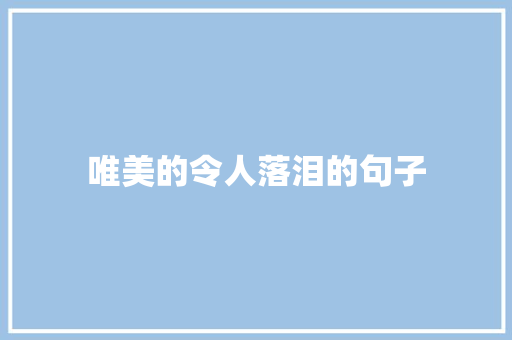远处彷佛传来汽笛声。
悲哀逆流成河46下午末了一节课是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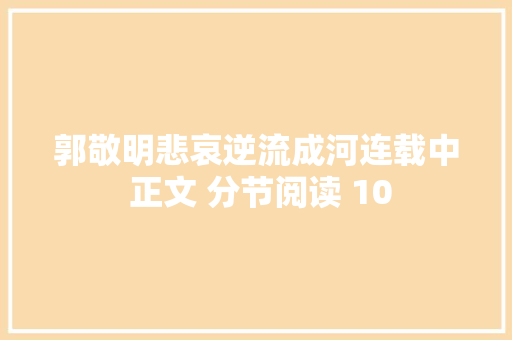
黑板上一张巨大的天下舆图。
穿得也像是一张天下舆图般斑斓的地理老师站在讲台上,把教鞭在空气里挥得唰唰响。
易遥乃至以为像是直接抽在第一排的学生脸上的觉得一样。
不过本日她并不关心这些。
右手边的口袋里是上次爸爸给自己的四百块钱。捏在手里,由于太用力,已经被汗水弄得有些发软。
而左手边的口袋里,是一张自己从电脑上抄下来的一个地址。
放学看到在学校门口等自己的齐铭时,易遥见告他自己有事情,丁宁他先回去了。
齐铭没说什么,站着望了她一下子,然后推着车走了。
背影在人群里特殊显眼,白色的羽绒服被风鼓起来,像是一团凝聚起来的光。
易遥看着齐铭走远了,然后骑车朝着与回家相反的方向骑过去。
也是在一个弄堂里面。
易遥放开手上的纸,照着上面的地址逐步找过去。
周围是各种店铺,卖生煎的,剪头的,卖杂货的,修自行车的,各种世井气息缠绕在一起,像是织成了一张网,甜腻的世俗味道浮动在空气里。
路边有很多脏脏的流浪猫。用异样的眼力望着易遥。偶尔有一两只溘然从路边的墙缝里冲出来,站在马路正中,定定地望向易遥。
终于看到了那块“私人妇科诊所”的牌子。白色的底,玄色的字,死板的字体,由于悬挂在外,已经被雨水日光冲刷去了大半的颜色,剩下灰灰的样子,漠然地支在窗外的墙面上。四周错乱的梧桐枝桠和交错凌乱的天线,将这块牌子险些要吞没了。
已经是弄堂底了。再走过去便是大马路。
实在该当从马路那一边过来的。白白穿了一整条弄堂。
逼仄的楼梯上去,越往上越看不到光。走到二层的时候只剩下一盏黄色的小灯泡挂在墙壁上,楼梯被照得像荒废已久般发出森然的气息来。
“还是回去吧”这样的动机在脑海里四下出没着,却又每次被母亲冰冷而毒辣的目光狠狠地逼回去。实在与母亲的目光同谋的还有那天站在李宛心背后一贯沉默的齐铭。每次想起来都会以为心脏溘然抽紧。
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和他怎么说话了吧。
白色羽绒服换成了一件玄色的羊毛大衣。裹在漂亮挺立的校服表面。
易遥低头看了看自己肥大的裤子,裤腰从皮带里跑出一小段,像一个口袋一样支在表面。副班长以及唐小米她们聚在一起又得意又彷佛怕易遥创造却又惟恐易遥没创造一样的笑声,像是浇在自己身上的胶水一样,粘腻得发痛。
易遥摇摇头,不去想这些。
抬开始,光芒彷佛亮了一些,一个烫着大卷的半老女人坐在楼道楼。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散放着一些发黄的病历卡,登记签之类的东西。
“叨教,”易遥声音低得险些只有自己听得见,“看……看妇科的……那个年夜夫在吗?”
大卷的女人抬开始,高下来回扫了她好多眼,没有表情地说:“我们这就一个年夜夫。”
一张纸丢过来掉在易遥面前的桌子上,“填好,然后直接进去最里面那间房间。”
悲哀逆流成河47天花板上像是蒙着一层什么东西。看不清楚。窗户关着,但没拉上窗帘,窗外的光芒照进来,冷冰冰地投射到周围的那些白色床单和挂帘上。
耳朵里是从阁下传过来的金属用具撞击的声音。易遥想起电视剧里那些会用的钳子,手术刀,乃至还有夹碎肉用的镊子之类的东西。不知道真实是不是也这样夸年夜。只管年夜夫已经对自己说过胎儿还没有成形,险些不会用到镊子去夹。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易遥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冰冷的白色床单从身体下面发出湿润的冰冷感。
“要逃走吗?”
侧过分去看到年夜夫在往针筒里吸进一管针药。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不是镇痛剂。如果用麻醉,须要再加两百块。没那么多钱。用年夜夫的话来说,是“不过忍一忍就过了。”
“裤子脱了啊,还等什么啊你。”年夜夫拿着一个托盘过来,易遥微微抬开始,看到一点点托盘里那些不锈刚的剪刀镊子之类的东西反射出的白光。
易遥以为身体里某根神经溘然绷紧了。
年夜夫转过分去,对护士说,你帮她把裤子脱了。
悲哀逆流成河48易遥险些是发疯一样地往下跑,书包提在手上,在楼梯的扶手上撞来撞去。
身后是护士追出来的大声喊叫的声音,唯一听清楚的一句是“你这样跑了钱我们不退的啊!
”
阴暗的楼梯里险些什么都看不见。易遥本能地往下跳着,恨不得就像是白烂的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摔一交,然后流产。
冲出楼道口的时候,剧烈的日光溘然从头笼罩下来。
险些要失落明一样的刺痛感。拉扯着视网膜,投下纷繁繁芜的各种白色的影子。
站立在鼓噪里。逐渐逐渐规复了心跳。
眼泪长长地挂在脸上。被风一吹就变得冰凉。
逐渐看清楚了周围的格局。三层的老旧阁楼。面前是一条彭湃人潮的大马路。头顶上是纷繁错乱的梧桐树的枝桠,零散一两片秋日没有掉下的叶子,在枝桠间勾留着,被冬天的凉气流风干成标本。弄堂口一个卖煮玉米的老太太抬起眼半眯着看向自己。凹陷的眼眶里看不入迷情,一点光也没有,像是黑洞般咝咝地吸纳着自己的生命力。
而这些都不主要。
主要的是视网膜上清晰投影出的三个穿着崭新校服的女生。
唐小米头发上的蝴蝶结在周围灰仆仆的建筑中发出刺目耀眼的红。像红灯一样,伴随着尖锐的警鸣。
唐小米望着从阁楼里冲下来的易遥,眼泪还挂在她脸上,一只手提着沉重的书包,另一只手去世去世地抓紧皮带,肥大的校服裤子被风吹得空空荡荡的。
她抬开始看看被无数电线交错着的那块“私人妇科诊所”的牌子,再看看面前像是失落去魂魄的易遥,脸上逐渐浮现出残酷的笑颜来。
易遥抬开始,和唐小米对看着。
目光绷紧,像弦一样纠缠拉扯,从一团乱麻到绷成直线。
谁都没有把目光收回去。
熟习的场景和对手戏。只是剧本上颠倒了角色。
直到易遥眼中的光亮溘然暗下去。唐小米轻轻上扬起嘴角。
没有说出来但是却一定可以听到的声音——
“我赢了。”
唐小米转过分,和身边两个女生对看着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开了,走的时候还不忘却对易遥招招手,说了一句含义繁芜的“保重”。
唐小米转过身,溘然以为自己的衣服下摆被人拉住了。
低下头回过去看,易遥的手去世去世地拉住自己的衣服下摆,苍白的手指太用力已经有点颤动了。
“求求你了。”易遥把头低下去,唐小米只能看到她头顶露出来的一小块苍白的头皮。
“你说什么?”唐小米转过身来,饶有兴趣地看着在自己面前低着头的易遥。
易遥没有说话,只是更加用力地捉住了唐小米的衣服。
被手抓紧的褶皱,顺着衣服材质往上沿出两三条更小的纹路,指向唐小米残酷的笑脸。
悲哀逆流成河49街道上的洒水车放着老旧的歌曲从她们身边开过去。
在旁人眼里,这一幕多像是好朋友的分别。几个穿着同样校服的青春少女,个中一个拉着另一个的衣服。
想象里天经地义的对白该当是,“你别走了。希望你留下来。”
可是——
齐秦的老歌从洒水着低劣的喇叭里传出来,“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曾经风行一时的歌曲,这个时候已经被路上俊秀光鲜的年轻人穿上了“后进”这件外衣。只能在这样的场合,或者ktv里有大人的时候,会被听见。
而没有听到的话,是那一句没有再重复的
——求求你了。
而没有看到的,是在一个路口之外,推着车停在斑马线上的黑发少年。
他远了望过来的目光,温顺而悲哀地笼罩在少女的身上。他扶在龙头上的手捏紧了又松开。他定定地站在斑马线上,红绿灯交错地换来换去。也没有改变他的静止。
悲哀逆流成河50被他从迢遥的地方望过来,被他从迢遥的地方喊过来一句漫长而温顺的对白,“喂,一贯看着你呢。”
一贯都在。
无限漫永劫间里的温顺。
无限温顺里的漫永劫间。
一贯都在。
悲哀逆流成河51闭起眼睛的时候,会瞥见那些缓慢游动的白光。拉动着模糊的光芒,密密麻麻地纵横在阴郁的视界里。
睁开眼睛来,窗外是凌晨三点的弄堂。
昏黄的灯光在阴郁里照出一个缺口,一些水槽和垃圾桶在缺口里显影出轮廓。偶尔会有被风吹起来的白色塑料袋,从窗口飘过去。
两三只猫悄悄地站在墙上,抬开始看向那个皎洁的玉轮。
偶尔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汽车的喇叭声,在寒气逼人的深夜里,由于太过寂静,已经听不出刺耳的觉得,只剩下那种悲哀的感情,在空旷的街道上被持续放大着。
易遥抬起手擦掉眼角残留的泪水。转身面向墙壁连续闭上眼睛睡觉。
已经是连续多少天做着这种悲哀的梦了?
有时候易遥从梦里哭着醒过来,还是停滞不了悲哀的感情,于是连续哭,自己也不知道由于什么而哭,但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被那种叫做悲哀的感情笼罩着,像是上海夏天那层厚厚的漂浮在半空中的梅雨时令,把全体城市笼罩得发了霉。
哭得累了,又重新睡过去。
而最新的那个悲哀的梦里,齐铭去世了。
悲哀逆流成河52易遥和齐铭顺着自行车的车流朝前面缓慢地提高着。
清晨时候上海的交通状况就像是一锅被煮烂了的粉条,三步一红灯,五步一堵车,时时有晨炼的老头老太太,踮着脚从他们身边一溜小跑过去。
每一条马路都像是一条瘫去世的蛇一样,缓慢地蠕动着。
“喂,昨天我梦见你去世了”,又是一个红灯,易遥单脚撑着地,回过分望向正在把围巾拉高想要遮住更多脸的部分的齐铭,“彷佛是你罹病了还是什么。”
齐铭冲她招招手,一副“不要胡说”的表情。
易遥呵呵笑了笑,“没事,林华凤跟我说过的,梦都是反的,别怕。我梦里面……”
“你就不能好好管你妈叫妈,非得连名带姓的叫吗?”齐铭打断她,回过分微微皱着眉毛。
易遥饶有兴趣地回过分望着齐铭,也没说话,反正便是一副看泰西把戏的样子看着齐铭的脸,犹如有人在他脸上打了台子在唱戏一样,到末了乃至看得笑起来。
齐铭被她看得发慌,回过分去看红灯,低低地自言自语。
易遥也转过去看红灯,倒数的赤色秒字还剩7。
“实在你该当有空来我家听听我妈管我叫什么。”
齐铭回过分,刚想说什么,周围的车流就涌动起来。
易遥朝前面用力地蹬了两下,就跑到前面去了。
所谓恋爱,只假如参加了便是故意义,纵然是没有结局,当你喜好上一个人的那一刹,是永久都不会消逝的,这都将会变成你活下去的勇气,而且会变成你在阴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