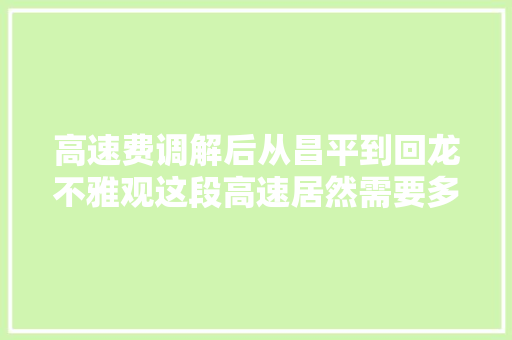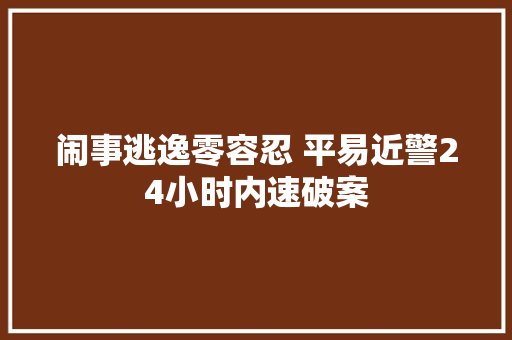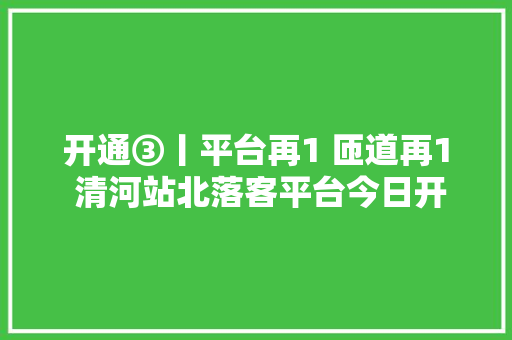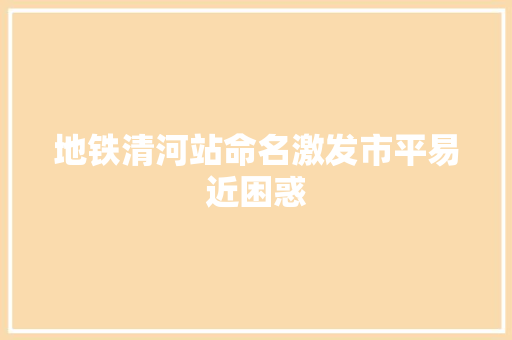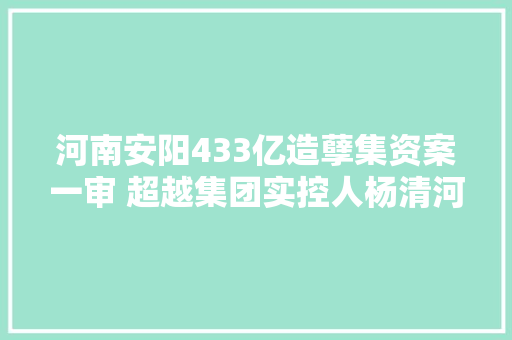一个身材高挑丰腴的美女,拎着蛋糕捧着鲜花进门。
洁白病床上,挂着呼吸机的陈清河,像去世鱼一样,伸开嘴大口喘息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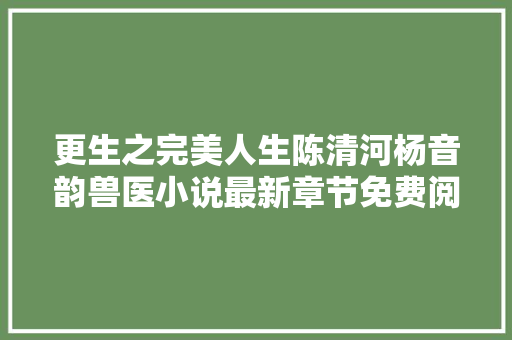
肺癌晚期,年夜夫说他只剩一两个月的活头。
瞥见女人,陈清河抬起挂着点滴的胳膊,困难扯起被角,羞愧的挡住脸。
女人叫杨音韵,是他的妻子,准确来说是二十三年前的妻子。
十八岁那年,生活在穷山恶水的陈清河,经由媒人先容,与女知青杨音韵结婚。
当年十月份,两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娃。
被家里宠坏的陈清河,根本不学无术,整天和村落里的混混们偷鸡摸狗,饮酒打牌。
喝醉了回家,就打老婆孩子。
每次陈清河撒酒疯,杨音韵就把两个孩子去世去世搂在怀里,任由拳打脚踢落在背上。
纵然这样,杨音韵也没有抛弃这个家,而是把所有的爱与希望,都倾注给了两个孩子。
直到有一次,喝醉酒的陈清河把烟头扔到被子里,点燃大火。
熊熊燃烧的茅草屋,烧去世了两个孩子,同样让陈清河患下了永久的肺病。
那晚过后,杨音韵消逝得无影无踪。
妻离子散的陈清河,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两个孩子悲惨的哭喊声。
他一夜发展,痛定思痛,悛改自新重新做人。
在二十世纪初年,陈清河拥有了上亿的身家,公司都开到了国外。
二十年里,他冒死的想要找到杨音韵。
陈清河知道,曾经的创伤与亏欠,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上,只能在有生之年,为她多做些事。
可是杨音韵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二十年了无音讯。
二十年后的本日,得了肺癌的杨音韵,自知道时日无多,已经裸捐所有家产,躺在病床上等去世。
杨音韵掀开陈清河挡住脸的被子,轻抚着他凌乱的发丝,神色繁芜而惆怅。
“我以为再见面时,我会恨你入骨。可是看到你这个样子,我恨不起来。”
陈清河痛楚的闭上眼,泪水顺着眼角流出,哽咽着说:“我对不住你们娘仨。”
杨音韵叹了口气,“二十年里,哪怕你找疯了,我也故意不涌现,便是为了让你的余生,在恶行的腼腆中度过,这是我唯一能对你的报复。”
“二十年的痛楚折磨,心里不好受吧。”
陈清河甘心杨音韵来源盖脸,年夜骂他一顿,把氧气管子拔了,也好比许平淡的温声细语,要来得更好受。
他再也掌握不住,捂着脸失落声痛哭,“为什么那把火烧去世的不是我!
”
杨音韵轻轻擦拭去眼角泪光,“二十年前,我被送到乡下做劳动改造。”
“由于身分问题,没人乐意吸收我,更没人给我一口饭吃。你娶了我,我才有活命。”
“二十年的良心折磨,你欠我的已经还清了。”
“你欠孩子的,下辈子逐步还吧。”
“本日是你的生日,我们不说丧气的,吹烛炬吧。”
杨音韵帮陈清河取下氧气罩,小心翼翼的吹灭了烛炬……
第二天,换了一身衣服,还特地画了淡妆的杨音韵,端着蛋糕涌如今病房门口。
“清河,四十二岁生日快乐。”
躺在病床上的陈清河愕然,“你这是什么意思?”
“往后的每一天,我都给你举办一次生日,畅想我们那一天可能经历的生活,也算陪你一辈子了。”
“谢……感激。”
第二十天。
“清河,生日快乐。”
“咱们都老了,腰也驼了,腿也挪不动步,该好好安歇。”
“如果你要先走,千万不症结怕,有我在阁下陪着呢。”
杨音韵坐在病床前,柔荑牢牢攥着他那只干枯瘦削的手。
陈清河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可喉咙不知被什么堵着,一个字也说不出。
年夜夫和护士在病床前围成一圈,大都红着眼,静静的抹眼泪。
燃着烛炬的蛋糕,就放在阁下,可是陈清河已经没有吹烛炬的力气。
阁下显示生命体征的仪器,正一个接着一个的发出警报。
杨音韵把蛋糕捧在病床前,替陈清河吹灭烛炬,含着泪说:“许个愿吧。”
陈清河困难的开口,“我……我去世往后,能不能……别,别火化,我害怕火……”
每次瞥见大火,陈清河都会想起自己双胞胎孩子被烧去世的一晚。
二十年里,哪怕他瞥见普通的篝火,都会忍不住浑身颤动。
哔——
心率检测仪响起警报声,代表人的心脏已经停滞跳动。
陈清河的双眼陷入阴郁,意识开始模糊,心底的那份恐怖逐渐扩展。
他想去世,同样也怕去世。
在末了病笃的时候,他唯一能感想熏染到的,便是手心被攥着的温暖,以及杨音韵温顺的声音。
“别怕,我在陪着你。”
“别怕,我在陪着你。”
“别怕……”
声音越来越模糊,陈清河被恐怖笼罩的心,逐渐变得安宁。
生前的景象,像走马灯一样开始回放。
他瞥见了十八岁时,喝醉了酒摇扭捏晃回家,扯着杨音韵头发撕打,把襁褓中双胞胎吓得嚎啕大哭的自己。
仇恨,自责,都没有用了。
陈清河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二十年后的影象里,用绝望的目光看着曾经胡作非为的自己。
等再回过神来,只剩下奄奄病躯,病笃末了的分秒。
陈清河依依不舍的用末了的力气,攥紧了杨音韵的手。
“如果能重来,那该有多好啊……”
第二章 放下屠刀 “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谁特么养鱼,谁不是人揍的。”
惯性的一杯白酒入喉,带来火烧一样的灼痛感,呛得陈清河直咳嗽。
缓过神时,陈清河擦掉咳出的眼泪,茫然望向四周。
熟习的村落口小饭店,三个年轻人坐在四方桌前,正吆五喝六的喝着酒。
桌上只摆着两盘菜,一盘土豆丝,另一盘是老母鸡炖土豆。
陈清河吓了一跳,仓皇站起身,把手腕放在嘴边,狠狠的咬了一口,血珠子都冒出来了。
疼,钻心的疼。
他跌跌撞撞跑到小饭铺的门口,对着洗手台上的小镜子,仔细看自己的一张脸。
清秀稚嫩的一张小白脸,身材瘦削,脑袋像是鸡窝一样蓬乱。
这……这是十九岁的我!
?
影象迅速回溯,陈清河恍然想起,这一幕和茅屋失落火的那天晚上,千篇一律!
那天,他捉走了家里下蛋的老母鸡,还拿走杨音韵藏在枕头底下的五毛钱,和自己的狐朋狗友饮酒。
一毛钱炒了个土豆丝,剩下四毛钱从供销社打了散酒,老母鸡让饭铺免费加工。
吃饱喝足,回家一头栽倒床上呼呼大睡,烟头引燃房间,自己醉醺醺的跑出,两个孩子被活活烧去世。
想到这里,便是一阵锥心刺痛。
“陈清河,这他妈酒还没喝呢,你发什么神经!
?”
陈清河转头看向三个歪瓜裂枣的小混混,呆滞的问了一句,“本日是什么日子?”
“七月十九啊。”
“哪年的七月十九?”
“七九年啊。你小子本日怎么神神叨叨的。”
一九七九年生日,便是失火当天,陈清河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天眷顾,他陈清河又重活了一世,回到了犯下罪孽前的三个小时!
霎光阴,无数繁芜晦涩的感情一股脑的涌上心头,泪水随之彭湃而出。
陈清河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镶嵌进肉里,心里暗暗立下誓言。
既然老天给了赎罪的机会,他这一辈子,绝不会再辜负杨音韵和孩子!
“陈清河,你特么磨叽什么呢,快来饮酒!
”
“滚过来,自罚三杯。”
正吆喝着的三个混混,是陈家的三兄弟。
哥仨爹妈去世的早,自己又不学无术,整天偷鸡摸狗,到三十五六岁还是王老五骗子汉一条。
想当初,十八九岁的陈清河,整天随着他们瞎混。
陈家哥仨却从来没把陈清河当朋友,只是把他当冤大头,随着蹭吃蹭喝,没钱了就撺掇他从家里偷钱、偷东西去卖。
重活一世,陈清河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再占了便宜。
一盘炖鸡和一盘土豆丝,还没来动几口。
一大桶散酒,才刚倒上一杯。
“老板,给我拿俩塑料袋。”
“好。”
从饭店老板手里接过塑料袋,陈清河沉着脸端起菜盘子,倒进塑料袋里打包,又拎起酒桶,转身就走。
陈老大傻了眼,“你特么要去哪?”
“回家,我老婆还饿着肚子呢。”
“那我们吃啥?”
“你们吃什么,关我屁事。”
撂下末了一句,陈清河不再管骂骂咧咧的陈家哥仨,出了饭铺往后,开始在林间小路开始狂奔。
狂奔了三里地,陈清河冲进虚掩着房门的破旧茅草屋,跪在床前,张大了嘴巴喘息,胸膛剧烈起伏,心脏都快要跳出来。
床上,两个粉嘟嘟的小奶娃,睡得格外酣甜。
陈清河双眼通红,喉头哽蠕,不敢相信这触手可及的幸福。
他几次伸脱手,想摸摸俩女儿的脸,可手指离嫩滑的小脸蛋咫尺时,他又犹豫了。
有不知多少个夜晚,他都梦见自己的两个女儿,每次想要伸手触碰,都在末了一秒被惊醒。
手掌抖动半天,就在陈清河终于鼓足勇气摸上去的时候,忽然一只柔荑拽着后脖颈,踉跄的拽着他出门。
含着泪的杨音韵,压低了嗓音怒骂:“陈清河,如果你敢打孩子的主张,我就先杀了你再自尽!
”
杨音韵看到陈清河举止怪异,跪在床前伸手摸孩子的样子,以为他是要把孩子给卖了。
毕竟像陈清河以前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干出什么丧尽天良事都不奇怪。
影象中熟习的人再次涌现,陈清河忍不住泪水再次涌出。
十九岁的杨音韵,俊秀且稚嫩,身子软弱俏脸苍白,一看便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
慌张了好一下子,他擦了把眼泪,咧咧嘴露出笑颜,哽蠕了半天才说:“我……我没有想卖孩子,便是看看他们。”
“你以前从来
陈清河低头回避她愤怒的目光,指了指屋子里桌上,挠了挠头讷讷的说:“菜还是热的,你吃。”
看着热腾腾的鸡肉,还有土豆丝,杨音韵有些发傻。
对付陈清河偷家里东西的事,她都见怪不怪了,可这些好吃的,自己什么时候轮到过一口!
杨音韵俏脸当心,“你是不是在里面下了药,想把我们娘仨一起卖了!
?”
陈清河拿起筷子,挨个吃了一口,憨憨一笑,“没毒。你太瘦了,得多吃肉。”
杨音韵泪水涌出眼眶,“还吃肉呢!
咱家都快没米了,如果不是我每天钓点鱼炖汤,都没有奶喂孩子!
”
“现在下蛋的鸡也没了,我们娘仨早晚饿去世。”
陈清河这才创造,杨音韵脚边放着一个蚯蚓罐,竹子和缝衣针大略单纯做的鱼竿,该当是准备要去钓鱼。
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钓鱼补贴口粮,还带着两个襁褓中的孩子,辛劳程度可见一斑。
当初的自己,可真够忘八的!
陈清河捡起地上的鱼竿和蚯蚓罐,“往后有我在,担保你们娘仨谁也饿不着。”
想要让杨音韵对自己有改不雅观,单凭一句话是绝对不足的。
陈清河没有多阐明,拿了工具就出了家门。
月光下,杨音韵望着陈清河踽踽拜别的背影,不由得有些发呆。
难道……他转性了?
第三章 影象中的大火很快,杨音韵就打消了自己稚子的动机。
哪怕狗改了吃屎,像陈清河这种人渣,也绝对不会痛改前非。
杨音韵永久忘不了,陈清河喝醉酒时,像发了疯一样打人的样子。
如果不是自己拦着,双胞胎孩子肯定被他摔去世了。
一定是他本日喝醉了酒抽风,才做出奇怪的举动……
六月三伏,蝉鸣蛙声鼓噪,陈清河走了二十分钟的山间小路,来到河边扔下鱼饵,忍着肚饿等鱼儿中计。
他原来想和杨音韵一起吃顿饭再出门,可买土豆丝的一毛钱,是偷她攒下的,母鸡是用来下蛋给孩子炖蛋羹的。
这两样东西,陈清河没脸吃。
陈清河给鱼竿做了个小机关,自己爬上树,摘还没怎么成熟的野桑葚。
吃了一堆桑葚勉强充饥,过了一个小时旁边,陈清河又钓起两条寸许长的小鲫鱼。
这两条小鱼,没啥吃的还满是刺。
哎,如果手头有点本金就好了。
在百废待兴,同样各处黄金的年代,想要赢利切实其实再随意马虎不过。
上辈子的陈清河,花了二十年,成了资产上亿的企业家。
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凭借四十岁的知识储备量,他绝对可以达到上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不过再大的年夜志壮志,也不如钓上来的两条鱼主要。
回去把鲫鱼煎一煎,猛火炖煮,能弄上一碗奶白的鱼汤。
杨音韵太瘦了,得好好补一补。
一起蝉鸣蛙声,陈清河拎着鱼篓慢悠悠的回家,心里计算着,该怎么才能弄到第一桶金……
“着火了!
”
“救火啊!
”
来到村落口时,陈清河瞥见好多人端着水盆拿着水桶,一边喊一边往杨树林里跑。
杨树林阵势不好,除了自己一家,根本没有人住。
陈清河短暂愣神,忽然错愕的扔掉鱼竿,拔腿就朝着家里跑。
等离近了,就能瞥见火光冲天与浓烟滚滚的茅草屋。
房屋的木质构造完备燃烧,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在看到大火的霎时,陈清河浑身抽搐,恶心干呕,剧烈的生理反应让他下意识想要逃跑。
上一世,陈清河在失火中差点烧去世,并落下永久性的肺病。
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也葬身火海。
火焰给陈清河带来的阴影,远远强过大水猛兽。
“孩子,我的孩子!
”杨音韵跪在地上,嘶喊着要往前冲。
两个村落里的大婶,去世去世的架住杨音韵的胳膊,“姑娘,这么大的火,别说是娃娃,哪怕是成年人也烧去世了。”
“便是要去世,我也要和她们去世在一起!
”
火势越来越大,再往里冲已经没故意义。
带着绝望与仇恨的杨音韵,狠狠的给了自己一巴掌。
“是我没看好孩子,怎么不把我烧去世啊!
”
她为了赚点油盐钱,喂奶后把孩子哄睡,帮着前村落李婶子做点针线活赢利。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大火燃烧,群人救火的一幕。
哗啦——
陈清河抢过一盆水,把自己浇得透心凉。
端盆的同族叔伯吓了一大跳,“这是救火的水,老远端来的,你小子犯什么混呢!
”
陈清河没有回答,而是撕下一截上衣,捂着口鼻突入了熊熊燃烧大火的茅草屋。
看到这一幕,声嘶力竭着哭喊的杨音韵,呆滞跪在原地,切实其实不敢相信面前发生的统统。
冲进火场的……是陈清河!
?
理智见告她,突入像这样的火场,无论是谁都得丧命。
猛然反过神来的杨音韵,再度无力的嘶喊:“回来!
你想去世吗!
!
”
表面的呼喊声,陈清河已经听不见了,入耳的只有哔哔啵啵燃烧声,木头房梁咯咯吱吱不堪重负的声。
大火与浓烟,会让人的眼睛堕泪失落明,以是陈清河在冲进门往后,直接闭上了眼。
进门五步,左拐向前猛撞!
砰——
熊熊燃烧的主卧门被撞开,陈清河往前跨出一步,左转连续朝着前方猛撞!
次卧的门板,再次被撞开。
陈清河睁开眼睛,瞥见俩娃娃小脸憋得通红,正挣扎着在床上嚎啕大哭。
谢天谢地,孩子没事。
原来茅草屋只有一个客厅,一个寝室。
杨音韵有身往后,她怕陈清河夜里发酒疯打人,伤了肚子里的孩子,就在寝室中心,用砖头砌了一堵墙。
这一堵隔热的砖墙,救了俩孩子一命!
在陈清河把俩孩子去世去世搂在怀里时,才觉得到后怕和紧张。
本日这场大火,是他二十年里的无数噩梦中,都想要阻挡的。
他在梦里,把茅草屋的布局已经记得清清楚楚。
哪怕闭着眼睛,也能撞开房门,清晰的找到俩孩子的位置。
忽然,表面传来一声惊叫,“屋子要塌了!
”
房梁变形,嘎嘣嘎嘣的木头断裂声响起,陈清河下意识跪在地上,竭力弯着腰,把孩子去世去世护在怀里。
轰然一声巨响,木质构造的茅草屋完备倒塌,直接成了平地。
一把大火,把杨音韵的心烧成了灰。
她眼珠翻白,急火攻心背过气去。
不知谁喊了一声,“快看,陈清河没去世!
”
浑浑噩噩中的杨音韵听到声音,竭力的掀开眼帘,瞥见在倒塌的废墟中,陈清河踉跄着步伐,怀里抱着两个孩子,朝她走来。
“我的孩子!
”
杨音韵凭空生出一股力气,从地上站起,冲到陈清河身前,把两个孩子接过。
大女儿白白净净的,身上没沾着灰,闹腾的正厉害。
阁下有个婶子,帮杨音韵把孩子接过。
可身体更弱一些的小女儿,皮肤黢黑,小脸铁青,已经没了动静。
杨音韵含泪抬开始,用抖动的声音问:“她……她怎么不哭了?”
“不可能!
”
陈清河一把抢过孩子,“我刚才救她的时候还好好的,哭得可起劲了,这怎么会……”
被这么一折腾,十个月的小女儿迷迷瞪瞪的睁开睡眼,看到阁下一大堆人,吓得瘪了瘪嘴,哇的哭出声。
“看,她哭了,没事了。”
陈清河咧嘴一笑,把孩子塞到杨音韵的怀里,随后向后踉跄一步,重重跌倒在地昏去世过去。
“清河!
”
意识晕厥的末了一秒,陈清河仿佛听到了杨音韵发急的呼喊声……
浑浑噩噩中不知过去多久,陈清河猛然睁开眼睛,大汗淋淋的从床上坐起身。
“女儿!
”
陈清河一声惊喊,愕然打量四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你终于醒了。”
耳畔传来杨音韵怠倦的声音,她掀开被子,披着睡衣点燃床头烛炬,眼球通红可见血丝。
大木床靠墙的位置,俩双胞胎奶娃甜睡的正喷鼻香,砸吧着小嘴彷佛做了什么美梦。
陈清河大松了一口气,这才借着烛光,茫然看向四周。
土坯墙,青瓦顶木头房梁,床头贴着泛黄的年画,屋子里唯一算家具的,就只有手打刷枣红漆的红木柜子。
屋子的装饰,哪怕放在八零年初,也寒酸的厉害。
“这是……爸妈家!
?”
“你晕厥之后,就被爸用排车拉回去了,我们也只能住在爸妈家。”
杨音韵缩了缩脖子,带着抖动的哭腔,畏惧说:“对不起,我也不知茅草屋是怎么烧起来的,是我没照看好家和孩子!
”
“你……你想打就打吧。”
以往的时候,她把饭做咸一点,就可能挨一顿毒打,更何况是轻忽失落火,把屋子烧了。
陈清河翻身从床上坐起,检讨了一遍身子,创造并没有伤势,大概只是吸入一氧化碳过多,才昏倒的。
“音韵,以前是我忘八,我不是人。”
“往后不管发生什么,我往后再也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
“我要赢利,让你们娘仨吃饱穿暖,再盖一栋大屋子,过最好的生活。”
杨音韵美眸空洞麻木,对他的话丝毫不为所动,乃至不屑理会。
对此,陈清河只能苦笑。
以前他想要钱饮酒赌钱,都耍这种花招,说好话从杨音韵兜里骗安胎的钱。
一次、两次,三次……谎话说多了,真话也会变成谎话。
想要让杨音韵改不雅观,只能通过长久的实际行动。
他迅速穿上衣服,拿上手电筒,又从柴房取了两口蛇皮口袋,摸着黑出门。
站在院门口,望着他夜幕中踽踽行走的背影,杨音韵动了动嘴唇,想要问他去哪,终极把话停在喉头。
陈清河一起穿过树林,来到河边。
夜里十二点,蝉鸣蛙声正响亮。
陈清河一起穿过树林,来到河边,开始捉蝉和田鸡。
在后世,麻辣蛙肉、油炸蚕蛹都是炙手可热的美食,可在八零年初,这些东西还只有嘴馋的小孩抓来吃。
如果能把这玩意加工好卖出去,便是一本万利。
之以是要晚上抓,是由于这俩东西白天瞥见人会跑,晚上用手电筒一照,由于强光反应,就趴在那儿不动了。
不到一个小时,陈清河就抓了整整两袋子,费劲巴拉的扛回家。
路途经过被烧塌的废墟,陈清河扒拉着灰烬,从里面扒拉出一个炒锅,一个炖锅,还有一个炉子。
天一亮,陈清河就要去镇上卖小吃,这些厨具刚好用得上。
看着面前烧塌了的废墟,陈清河的脑筋里一直的琢磨一个问题——那场大火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上一世,陈清河一贯以为是自己的烟头引燃棉絮,才烧起熊熊大火。
这一世,自己没有吸烟,杨音韵去村落头给人做针线活,俩孩子躺在床上安睡,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是天干物燥,哪里飘来的火星子,还是……有人在蓄意纵火!
?
周围没有居民,飘来火星不现实。
被人蓄意纵火很有可能,上辈子陈清河偷鸡摸狗,斗殴打斗,险些把村落里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个遍。
八零年代可没有监控,想调查清楚险些不可能。
到底是谁干的呢……
陈清河拿动手电筒,在附近寻摸一圈,忽然从屋后的草丛里,创造了一个打火机。
打火机上,印着穿着暴露,时髦的红发女郎,还有红浪漫洗头房的牌号。
看到打火机的瞬间,陈清河顿时神色阴沉,“妈的,是这三个忘八!
”
打火机是县城洗头房赠予的,陈清河以前常常和陈家哥仨一起去那里鬼混,身上也有同样的打火机。
全体石龙村落,只有他们四个人身上有打火机!
昨天早高下过雨,打火机没有沾泥,可见是一天内落下的。
救火的时候,陈家三兄弟不在,那么他们必定是纵火的!
上一世,也是这三个人,纵火烧去世了自己两个孩子!
陈清河怒攥着拳头,恨不得现在就去找三个人冒死!
可是……还不是时候。
第一:就凭一个打火机,还定不了他们的罪。
第二:杨音韵和自己的俩孩子,还饿着肚子,居无定所。在报仇之前,得先让他们娘仨吃饱穿暖。
第五章 小吃摊之前陈家兄弟敢动手,是由于自己住的偏僻。
现在,杨音韵和孩子住在父母家,左邻右舍有很多人,哪怕陈家三兄弟狗胆包天,也绝对不敢再动手。
有了父母保护,陈清河可以放心的出门去摆小摊。
天将蒙蒙亮,陈清河扛着俩蛇皮口袋,困难走到家门口。
父亲正在院里洗脸,母亲蹲在露天灶台前,柴火哔哔啵啵燃烧着,映红了她苍老的面颊。
陈清河站在门口,想进去打呼唤,心中又胆怯。
按照韶光推算,就在一个月前,他和陈家三兄弟偷偷溜进家,把父亲的棺材折价一半,卖给了寿材铺。
拿到了十五块钱,当天就去了红浪漫洗头房。
屯子老人在上了年纪往后,会自己买木板,钉棺材。
做好了棺材,每隔一两个月,给棺材刷一遍漆。
一来是为了省钱,二来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棺材,心里痛快酣畅,能肃清对去世亡的恐怖。
家里唯一值钱的这么一口棺材,被陈清河偷出来给半价卖了,老两口赶到寿材铺,都没钱把棺材赎回。
父亲陈大栓气得大病一场,从此和陈清河断绝关系。
想到当初的所作所为,陈清河恨不得掐去世自己。
不过,是错总要承担。
他挪步走进门,硬着头皮站在院里喊了一声,“爸,妈,我回来了。”
“你给我滚!
”
穿着被汗渍染黄的破洞白短袖,解放库和黄胶鞋的矮瘦老头,端着搪瓷盆,就朝着陈清河身上泼。
陈清河退却撤退一步,洗脸水被泼在脚边。
“老头目,大早上你发哪门子邪疯!
”
张桂花去世去世拽住陈大栓的胳膊,“儿啊,别管你这倔爸,到屋里坐着去,面糊立时烧好了。”
陈清河咬着牙,半天憋出一句,“爸,我错了。”
“我不是你爸,你是我爸!
”
陈大栓气得满脸通红,“早知道养出你这么个活爹,出生那天就该把你摔去世在墙上!
”
陈清河低着头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您看在俩孙女的份上,收留杨音韵在这里住一段韶光。”
“我很快会赚到钱,在废墟上再盖一栋屋子。”
“你赚个屁!
”
陈大栓哼了一声,自顾自的抓起笠衫擦了把脸,算是默许他在这里用饭。
张桂花亲密的拉着儿子的手,“你爸便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这段韶光一贯惦记着你呢。”
“转头你好好道歉,等今年秋收了麦子,就再给你盖一栋新居子。”
今年,母亲也才四十出头。
看着她发丝斑白,手掌粗糙的像老树皮,陈清河心里不是滋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妈,饭就不吃了,我想管家里借点东西。”
张桂花有些惶恐的说:“儿啊,咱家可没有钱,也没什么能卖的东西!
”
陈清河有些无奈,看来想要让身边人印象改不雅观,道阻且艰啊。
“妈,我啥也不卖,便是想用咱家的排车,再借点油盐酱醋,拉点东西去县城卖。”
“行,车子好久不用了,妈给你整顿整顿。”
“不用,我自己来。”
屯子的排车,俩轮上头架着个长木板,由于长得像木排,以是叫排车。
前头车把很长,有点像黄包车的布局,常日农忙时用来在田间地头运粮食。
陈清河拿了块破毛巾,把排车抽打干净,又将俩蛇皮袋以及炉子和厨具放上去。
弄好了东西,陈清河把拉车绳抗在肩上,闷着头要出门。
陈大栓扯着嗓子喊,“你小子敢把家里排车卖了,我打断你的腿!
”
“知道了爸。”
陈清河闷着头正往前走,忽然胳膊被柔荑拽住。
愕然转头,杨音韵拿着个软乎乎的布包,塞进他的怀里。
“昨天妈烙的玉米饼子,我没舍得吃,你拿着路上吃。”
陈清河愕然愣在原地,“这……”
“你别误会,昨天你救了俩孩子还受了伤,我不能让病人饿肚子。”
“感激。”
攥着带有体温的布包,陈清河喉头有些哽咽,咬上一口玉米饼子,嚼着甜丝丝的。
有这样的家人,再没本事让他们吃饱饭,自己就太忘八了!
陈清河一鼓作气,拖着排车走了十五里地,饿了啃一口玉米饼子,渴了喝一口绿皮水壶里的山泉水。
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他总算在早上八点钟,来到石龙县城。
八十年代,百废待兴。
冒着蒸汽的工厂,骑二八大杠,统一穿蓝靛布和解放鞋的年轻人,街边鸡毛换糖的货郎,锵剪子磨菜刀的声音此起彼伏。
陈清河到附近水渠,娴熟的给田鸡剥皮清理内脏,挨个的洗濯干净,重新放进蛇皮袋里。
一大袋子田鸡,还有蝉蛹,陈清河整整清理了两个小时,才把所有食材处理干净。
八十年代初,城里人还不怎么吃这些玩意儿,能不能卖出去,陈清河心里也没谱。
但愿买卖能好一些,赚的钱不说买鸡鸭肉蛋,至少够买点猪蹄和大棒骨回去。
杨音韵的身子骨太弱,父母也年纪大了,得吃点东西,好好补一补。
十一点半,陈清河把板车停在兴盛机器厂门口,燃炉生火,准备做饭。
蝉蛹比较好处理,直接下锅油炸,出锅时洒了五喷鼻香粉,放在竹筐沥油。
等晾凉一些,陈清河伸手抓了一个塞进嘴里,入口酥脆,满嘴的生喷鼻香。
嗯,不错。
田鸡擦干水分,下锅文火慢炸,等把骨头都炸酥了,这才捞上来控干油水。
十二点整,等工人放工时,陈清河扯着嗓子喊:“特色小吃,解馋管饱,免费品尝!
”
在洗濯食材时,陈清河在河边捡到一块白布,又折了一根竹竿绑在排车上。
白布上写有四个大字——免费品尝!
八零年代,是好随意马虎摆脱饥饿的年代。
一粒米、一枚生锈的钉子、一块碎布头,对这个年代的人来说,都是宝贝。
人穷了,难免就会贪小便宜。
陈清河摊位上“免费”两个字,直接让一大批人聚拢过来。
“小伙子,你这儿真让免费尝?”
陈清河直接拿起筷子,夹了一个蚕蛹放在报纸上,“大爷,尝尝。”
老头尝了一个,嚼得满嘴生喷鼻香,不由得伸出大拇指,“好吃,再给我尝一个!
”
陈清河呵呵一笑,“这可弗成。大爷,我这招牌上写了,免费品尝,廉价管饱。”
“再想吃,您得花点钱了。”
“多少钱?”
“一毛钱一大碗。”
陈清河晃了晃手里的瓷碗,“一毛钱一大碗,您自己舀,多少都算您的。”
老大爷面前一亮,立即取出一毛钱放在钱箱里。
“把碗给我!
”
老大爷撸起袖子,把碗插入盛放蝉蛹的竹筐中,舀了满满一大碗。
就在想往报纸上倒的时候,不留神一抖动,洒在竹筐里不少。
“哎,年纪大了,这手便是不听使唤。”
就在老大爷惋惜时,陈清河又铲了一碗底的蝉蛹装进报纸,“大爷,您吃好常来,最近我都在这里摆摊。”
“呵呵,小伙子厚道啊。”
放工时人流特殊多,许多人尝了蝉蛹往后,纷纭表示要购买。
在八零年代初,一毛钱的购买力,相称于后世的二三十元。
哪怕把瓷碗装满,也就不到半斤蚕蛹,根本不算便宜。
可陈清河精准的捉住了人们贪便宜的生理,把一毛钱半斤,换成一毛钱一碗,就吸引了大批顾客。
一毛,两毛,三毛……统共十斤多的蝉蛹,在二十几分钟内被一扫而空,卖了整整三块多钱!
卖光了蝉蛹,陈清河又拿刀把田鸡肉剁成块,锅烧薄油,葱姜蒜炒喷鼻香,大火爆炒蛙肉和干辣椒段。
炒好的蛙肉倒入簸箕,仍旧是一毛钱一碗。
蛙肉被炸得骨头都酥了,肌肉嫩滑,配上麻辣鲜喷鼻香的口感,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人们捧着报纸,吧唧着嘴吃得满头大汗,喷鼻香味四溢,又吸引了更多人购买。
下午一点半,所有东西都卖光了。
陈清河清点了一下钱箱,里面统共八块六毛钱!
要知道,在八十年代,一个普通的工人,人为只有十几二十块。
一天的韶光,赚了旁人半个月的人为!
上辈子,陈清河身价过亿,却从来不以为金钱有什么意义。
本日,陈清河攥着一沓毛票的手,都忍不住激动得淌汗。
先花一块二,割上二斤上好的五花肉,又买了一袋米和一袋白面,统共花了两块钱。
剩下的钱,陈清河小心翼翼的揣进兜里,急匆匆推着板车回家。
下午五点半,吭哧吭哧走了十五里地的陈清河,总算挪步到家门口。
还没等进门,就听见里头传来争吵声。
“陈大栓,你们两口子还要不要点逼脸!
”
“春耕时候借我们家一块二买粮种,到现在还不还!
”
“当初借钱的时候,你腆着个老脸来求我,说是自己一家没有粮种,下半年就只能饿去世。”
“你说收了粮食往后准还,现在钱呢!
?”
陈清河进门就瞥见,膀大腰圆的苗秀芬,正单手叉腰,指着陈大栓的鼻子破口大骂。
陈大栓是个诚笃木讷的庄稼汉,神色憋得通红,低着头不肯吭声。
张桂花也一脸的窘态,“大妹子,我们家的确不宽绰,如果能拿得出钱,我们是那赖账的人么。”
“再说了,现在才六月份,下个月才秋收,到时候我们卖了麦子一定还钱行不?”
堂屋门口,杨音韵抱着两个被吓哭的孩子,俏脸上尽是无奈。
“晚一分钟就弗成!
我家没钱了,等着米下锅呢!
”
苗秀芬格外蛮横的堵着门,“你们本日不还钱,我就堵在门口,骂到你们还钱为止!
”
如果被堵在家门口骂街,陈大栓老两口,往后休想在村落庄里抬开始。
陈大栓咬着牙,黑沉着脸说:“最迟八月初,我还你一块三行不?”
“门都没有,现在我就要钱!
如果没钱,就把村落西头的地划给我们!
”
现在正青黄不接,苗秀芬知道陈大栓拿不出钱来。
她本日讨债是假,想要趁机讹一块地才是真的。
俩孩子已经到了睡觉的时候,被苗秀芬大嗓门一吵吵,哭得格外撕心裂肺。
孩子身体弱,很随意马虎哭岔了气。
陈大栓心疼孙女,紧攥着拳头近乎哀求的说:“大妹子,你想要我让多少利,咱们出去聊,别吓着孩子。”
“呸!
”
苗秀芬绷紧了一脸的肥肉,夜叉似的凶神恶煞说:“你们家没钱,便是陈清河那败家子,还有姓杨的娘仨给害的!
”
“生了这么个儿子,活该你一辈子受穷!
”
“你也别把那俩女娃,当宝贝疙瘩似的供着。”
“陈清河整天出去鬼混,留着杨音韵一个人在家里,她长得一副狐狸精相,俩孩子的亲爹,指不定是谁呢!
”
杨音韵被骂得神色发白,她性情孱弱不敢开口,想进屋躲避,又怕公公婆婆和苗秀芬打起来。
陈大栓攥紧了拳头,咬牙黑沉着神色说:“苗秀芬,干啥事都别把人往绝路上逼!
”
苗秀芬一脸不忿,“逼你又怎么样。陈大栓没有那根公鸡翎子,就不要装老鹰。”
“你是个带把的,就动手打我。来啊,来啊!
”
苗秀芬梗着肥腻腻的脖子,把脸一个劲的往前凑,陈大栓面红耳赤的一个劲退却撤退。
在屯子,谁的儿子多,钱多亲戚多,谁的势力就越大。
苗秀芬的丈夫在镇上当钳工,人为一个月有近三十块,剩下三个儿子,便是常常和陈清河一起鬼混的陈家哥仨。
陈大栓如果敢先动手,恐怕家都会被苗秀芬带人给砸了。
就在陈大栓进退两难的时候,陈清河的一只手,已经搭在苗秀芬的后背……
阅读全文地址重生之完美人生(陈清河杨音韵)兽医小说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乐逍遥小说网阅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