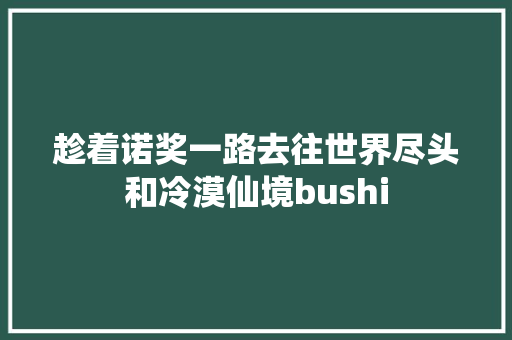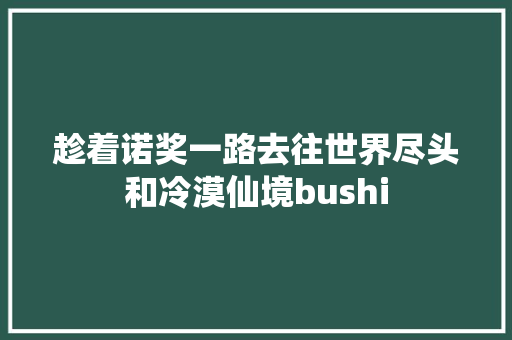前天的推文“新晋诺奖得主约恩·福瑟:在过去的10年里,我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谨慎的准备”里,译者李澍波已经大致带我们领略了挪威的一些风土人情,本日,文景君想约请各位读者随着“他者others”联合创立人及实行主编、《在驯鹿聚拢的地方,吟唱》作者吴一凡一起去往挪威的邻居——芬兰。
出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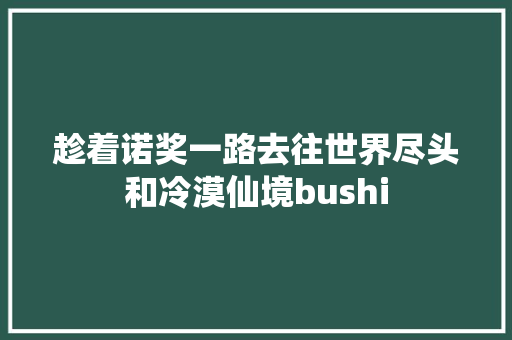
我在不同年份的不同时令数次深入北极圈,前往迢遥的芬兰拉普兰地区拜访萨米人。头一次是一个秋末,我和萨米人在那儿等待初雪。和我同行的还故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美学博士乔雅(Gioia)。从前旅居欧洲时,我和她在柏林一个废弃厂房改造的临时艺术中央相识,逐渐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她认为这种奔赴北方的艰辛旅途并不适宜我独自完成,只管我向她阐明自己有可靠的引导,但她的回应是:“能有我知心吗?”事后证明,她的坚持或许也是某种神秘力量的组成部分,没有她我会错过神圣的极光及其蕴含的能量。如今在芬兰的萨米人仅有6500人旁边,不过这个数据并不可靠。“数据没办法真的可靠,”我的引导塔尼娅(Tarja)说,“在这里我们并不以血统点认人数,这样阐明吧:一个与萨米人一起生活的赫尔辛基人,他理解萨米习气与文化,能够用他们的措辞,那他便是个萨米人。相反,如果一个萨米人到城里忘却了自己的传统,那他也就被这片地皮驱逐了。”关于萨米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他不是驯鹿牧人,便是猎人或捕鱼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一定和大自然有关,有时他们可能既是牧人又是捕鱼人,随不同时令转换。驯鹿冬天会去南边一点的地方生活,夏天则回到北部。从前萨米人就随着它们迁徙,在途中搭帐篷过游牧生活;现在他们在森林里的木屋定居。自从有了雪橇车,每年冬天驯鹿开始迁徙时,他们会开车去森林里照看它们,晚上回家,只有几天韶光生活在野外。他们天生就有极好的方向感,在阴郁的荒原中绝不会迷路。按当地人的说法,大自然总会为你指明方向。他们的这句话并不具有比喻义,这些原住民懂得如何读懂大自然给予他们的“路标”,在脑海里建立起影象舆图。英国生理学家、行为学家迈克尔·邦德(Michael Bond)认为当代人是置天生就有的巡航能力和空间感于不顾,至少在GPS指错路前,不会有人答理这份天赋。当代生活中的人们早就忘却了千百年来,探索便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寻路则是由此进化而来的,也是人类之以是成功的关键。本日依然以佃猎—采集过活的部族很少了,萨米人也大多过上了定居生活,但他们仍旧要深入极北原野中追寻自己的驯鹿,活动范围非常大,依赖的便是惊人的巡航本领、敏锐的空间感和方向感,还可以在脑筋里记住这统统。他们的头脑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磨炼下变得加倍长于不雅观察、探求方向。在原野中,萨米人看似形单影只,但他们始终知道朋友、亲人、家所在的方向,也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此他们绝不孤独,从未迷失落。事实上险些所有萨米人都喜好独自深入荒野或航行于大海,全体旅途中,我无数次听到萨米人评论辩论形单影只面对无人之境的神奇体验。“只要拥有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遵照自然法则,大自然就会以它的办法照顾你。”他们无不这样见告我。实际履历则让我体会到和这些人深入荒野的安全感。我们本能地须要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从而判断在这个环境中是否安全,一个出色的寻路者还会对周围环境保持警觉,能在精确的韶光做出精确的决议确定,能从不同的视角认出曾到过的地方,有出色的影象力,并长于利用自己的旅行经历。我们在临近挪威的芬兰边疆小镇努奥尔加姆过夜,这也是芬兰最北方的镇子。塔纳河(Deatnu)将小镇与挪威隔开。“Deatnu”在萨米语中的意思是“伟大的河流”,是萨米民气目中的圣河。这里是全欧洲最适宜捕三文鱼的地方,大自然源源不断的给予使当地人满怀戴德。塔纳河正值枯水期,浅滩犹如河中岛屿,冷风中站在河岸,夏季充足的雨水使之奔驰的景象不难想象,它的威慑力和巨大能量与广袤森林旗鼓相当。即便是枯水期也危急四伏,只有最理解地皮和蔼象的萨米人才能在这里驾船捕鱼。萨米人对景象管窥蠡测,他们总是举头看看便能准确预测气候。在拉普兰不能得到萨米人帮助的话,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片地皮。雷默(Raimo)在努奥尔加姆生活了大半辈子,决定给我上第一节野外生存课。他是个野外引导,萨米人和芬兰人的混血。我们在他河岸边的家中见面,这附近也有几栋木屋,供夏季到这里来捕鱼或者家庭游的游客利用。此时除了我们之外就没有别的客人了,我环顾不大的就餐室,墙上挂动手绘的萨米语北冰洋舆图,已经有些掉色,上面除了清晰地标注着北冰洋的位置外,还有驯鹿群的分布以及逆流而上的鱼群,其他的都是概括性的勾勒。见面时雷默一身短打,看了看我的呢外套和皮靴说:“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见告你山上的景象,云层挺厚,风有点大,而且我们得在野外用饭。大概你会再须要一件外套和一双真正温暖的鞋?我会在T恤外再穿件风衣的。”我默不作声地穿上两件外套和登山鞋,随着他在薄暮时向远山出发。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管山叫山丘,认为那里根本就不高,但这只是萨米人的意见。市价秋末,雷鸟的羽毛还未完备变白,它们从头顶飞过,提醒我们在向森林深处进发。我们到这儿来徒步,让我首次领略了北极风光。天空泛白,远处云层裂开一道口子,夕阳把那条线状的天空染成淡淡的橙赤色,和地平线保持平行,在它们之间的是绵延不绝的山(丘),形成一条又一条不断推进的平顺曲线,没有赛谁高的意味,看起来颇为柔和。我们走进一片枯树林,天光变化多端,逐渐转黑。雷默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他在山上建了个木屋,今晚要带我们去见识他的手艺。“冬天,我常带滑雪爱好者到那儿等待极光。”木屋已隐约可见,我以为再爬过一道坡便是胜利,但事实绝非如此。“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在森林里该怎么办,于是我们许多人都成了野外引导。冬天忙完驯鹿便是滑雪季,做事行业也是这里的收入来源之一。”萨米人知道如何保护森林,也知道旅行者同样是来自森林的当代礼物之一。他们始终懂得如何收成。我们在枯树林里不知走了多久,天色愈发暗下来,不过当你真正相信一位萨米引导时,这统统绝不会显得胆怯,反倒宁静安然得很。归巢的鸟鸣、风穿过树枝的声响、不远处的溪流、脚下的苔藓被我们挤出水分……这些声音在森林中被逐一辨认。面前,萨米人正如穿过自家厨房去取咖啡一样在荒野中开路。此刻所有人都能相信,他们独清闲荒野中的时候,便是与大自然领悟为一之时。这片枯树林有一种荒凉的美。树木枝干低矮发黑,没有一片叶子,它们一棵棵兀自站在那里,仿佛是由于见证过太多,于是决定沉默,任由岁月见告它们命运。雷默在森林里生活了40多年,见过这些树每年冒绿芽的光阴,“后来由于鸟太多,吃光了树叶,树干终极因接管过多水分而去世去”。他边走边见告我,这是36年前开始的生态圈,现在则须要比这长得多的韶光来让新树代替这些枯枝。“这便是大自然,无须欢畅也无须悲哀,你对此无能为力。”让人意外的是,我们都彷佛能在这片荒漠的去世亡之林找到一颗与自然不分彼此的纯净之心,能停下所有动机和思维。“知道对统统无能为力,把自己交给宇宙万物,成为生态圈的一部分。”我应和雷默,他点点头,认为我说了一句像是“太阳从东边升起”这样不过是常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