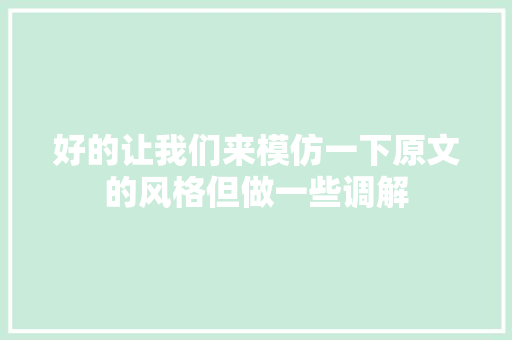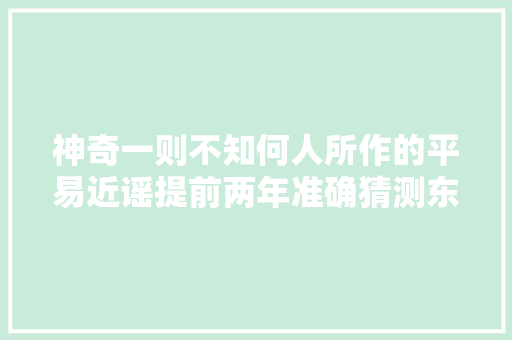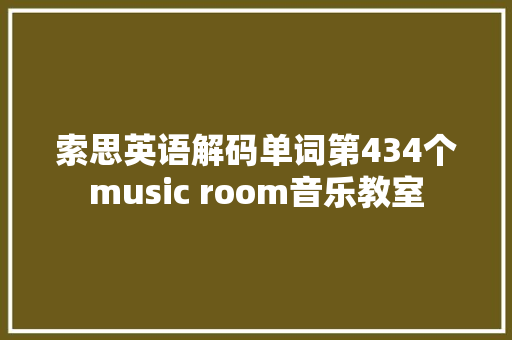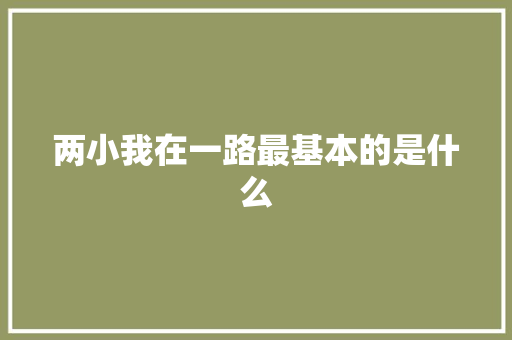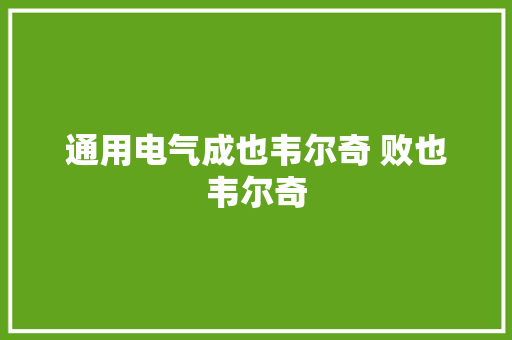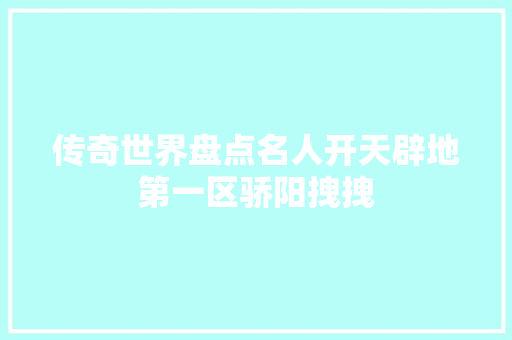理查德·詹金斯

威廉·燕卜荪(1)认为,牧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在近代企图从美学或者社会功能方面对牧歌进行阐明的过程中,这句话可能是最著名的。但本章的稽核工具将集中在一个更加呆板的任务上:弄清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并稽核牧歌为什么会存在,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变革的。对其独特而有时的历史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能越好地理解它为什么如此多样和不可捉摸。
\r\r牧歌的独特性之一便是它纯粹是欧洲(或者说西方)的文学类型。对大多数文学类型来说,都不存在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愉快地谈到中国的小说,评论辩论中国的史诗或者讽刺诗肯定也不存在什么大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把某一首中国古典诗歌或故事说成是牧歌(除非是在和欧洲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时,涌现比喻性的说法),会被人们认为是胡言乱语。由于牧歌艺术的本色在于它归属于一种传统,它实质上、而且必须是自觉的行为。如果读者没有能够看出一首牧歌是牧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还没有理解它。中国的墨客,由于他们不归属于这一传统,以是不可能写过牧歌,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没有牧歌的位置。当然,他可以描写村落庄的俏丽,牧人的生活,但这些还不敷以使他的诗歌被称为牧歌,由于牧歌并不仅仅是关于村落庄生活的,它是一种分外的处理这个题材的办法。当弥尔顿写下如下诗句:
\r\r女仙和牧人们不再在\r 多沙的、长满了百合花的拉顿河堤上舞蹈了。
\r\r我们知道,只管它们并非《阿卡德斯》的组成部分,但仍是牧歌。当蒲柏写出如下诗句:
\r\r牧童(他不想得到更好的名字)\r 赶着羊群沿银色的泰晤士河前行,\r 点点阳光洒在水面上,\r 嫩绿的赤扬形成了颤动的树荫。\r 当他轻轻哀悼时,河水彷佛都为之停步,\r 围着他的羊群也以安静表示同情……
\r\r我们关于这一传统的知识见告我们,只管这首诗的背景是英国,而且没有明确提到古典的典故,但它仍是牧歌。可是,当霍普金斯(2)写下这样的诗句时:
\r\r天下的斑斓归于造物主,\r 他创造了犹如斑纹奶牛的天空,\r 还有所有在水中游动的点画般的鲑鱼……
\r\r我们看得出,这是一首描写自然景致的诗,根本不是牧歌。
\r\r总之,牧歌有、或至少默认某些规范。这并不虞味着这些规范是固定不变的,但它确实意味着,牧歌的历史和起源,对付把它理解成一个文学类型具有分外的主要性。对大多数牧歌作者来说,维吉尔的《牧歌》既是典范,又是源泉。这部短诗集大概是欧洲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品,但维吉尔本人承认,他是在模拟那个出生于西西里的、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墨客忒俄克里托斯。在忒俄克里托斯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后来在维吉尔的牧歌中涌现的特点:牧人们吹着乐器,相互对歌,用韵律幽美的六音步诗句评论辩论着爱情和村落庄。因此,牧歌起源于一个人的创造。对大多数文学类型来说,其发轫的历史要么沉入历史的迷雾之中,要么是逐渐定型的,使我们无法确定其出发点,以是,牧歌的起源是够奇怪的。忒俄克里托斯发明了牧歌这种文学形式,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不是他。如前所述,牧歌归属于一种传统,但忒俄克里托斯显然无传统可追寻,他也没故意识到他正在确立一系列老例,这些老例竟会延续了两千年之久。他的作品Idylls(田园诗)中,有些是牧歌式的,有些则不是(Idyll的本意是提要或小的绘画,近代给Idyll授予的田园诗观点,虽然来自牧歌传统,却有些曲解)。后人把他的牧歌与其他的作品截然分离开来,假设它们都遵照一套明确的规则。由于生活在一个讲究创意的时期,他大概只是想表现出新意和分外,如果他知道后人把他的诗作为一种规范,他很可能会感到震荡。传世的还有一些墨客模拟他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不过,如果我们因此认定希腊有一种牧歌传统,那不免犯下时期缺点。那些名气不那么大的墨客不过是模拟忒俄克里托斯,并非牧歌流派。
\r\r罗马的牧歌传统与希腊颇为相似。维吉尔声称,他是第一个模拟忒俄克里托斯的拉丁语墨客,而我们没有情由疑惑他这个说法。他也有几个追随者,他们是卡尔普尼乌斯·西库路斯(可能是公元1世纪的人),涅麦西阿努斯(约3世纪),还有一个佚名作者,因其作品的残篇创造于瑞士的一座修道院中,被人们称为隐居者。如果我们说这些墨客最多不过是维吉尔能干的模拟者的话,这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很不公道。因此,在罗马的诗歌中,除了维吉尔和他的一两个模拟者外,彷佛也不存在牧歌传统。如果我们转向古代的文学批评,会创造我们的结论惊人地得到了他们的证明。古代的评论家们常日把文学作品划分身分歧的类型,如史诗、哀歌、教喻诗、讽刺诗,等等,可是他们彷佛没故意识到有牧歌这种文体存在。贺拉斯、昆体良和朗基努斯都对此保持沉默。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没有创造他们把牧歌作为一种类型来谈论的内容。至少在公元4世纪以前,在有关维吉尔的评论中,也没有这样的提法。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评论家们继续了古典评论中对作品进行分类的做法,而且我们创造急速涌现了差异:在诗歌分类中,牧歌的档次最低,史诗最高。西塞罗和昆体良曾经鼓励人们这样看待文学,但他们并未谈论牧歌。如我们下面将揭示的那样,文艺复兴时期评论家们的不雅观念确实有古代的渊源,但它来自古典古代后期,并非古典时期的拉丁语文学。
\r\r我们应该提及的古典牧歌的末了一个代表人物,是希腊人龙古斯和他的小说《达菲尼斯与克洛厄》。这本小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它提出了这样一种不雅观念:牧歌可以用散文的形式表现。由于维吉尔的影响,龙古斯不可能被人们忽略,由于从15世纪末起,维吉尔传统就和这一个来源的牧歌传统开始领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相信,古代已经涌现固定的牧歌类型,并遵照一套明确而得体的规则,结果使他们对不同的作家不加差异,并进一步模糊了不同风格的牧歌之间的界线。龙古斯幽美的田园诗实际上更靠近常日人们所说的阿卡狄亚式的或者德雷斯顿式的牧歌类型,而不是忒俄克里托斯或者维吉尔式的。
\r\r维吉尔的《牧歌》竟然成为全体一种诗歌类型的典范,实在是文学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很少有作品是那么非自然地服从其目的的。年轻的维吉尔是新派墨客的崇拜者。这些墨客是一个疏松的团体,成员大多是行省的贵族。他们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用一种造作的、怪异的诗句规避高尚的严明性和预见性。卡图鲁斯的《帕琉斯与特提斯》(3)是这种风格现存的代表作。《牧歌》正应以此来理解。他们追求的不是规则,而是奇特、即兴和诡辩。维吉尔在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上发展了忒俄克里托斯的风格。一方面,他更加富有文采,也更加虚假(精心挑选一个希腊人为榜样便是个例证);另一方面,在用诗歌表现意大利屯子的苦难方面,他又更富有现实性。当时,农人的地皮被没收,并被移交给那些退役的士兵。诗歌内容本身并非田园风光,但他们在处理更痛楚的题材时多采取间接办法。诗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只有在背景或者视觉的边缘才能看到。我们听到了远处战役的鼓噪,可是并无士兵走到前台;我们听说了牧人们的女伴,可她们谁也没有讲话或者加入到牧人中来;我们听说了下雨和冬天,但我们享受到的却是更好的景象;科律登(4)看到远处的收割者,但他本人却和自己的羊群清闲地呆在一起。诗中也有一些事情要做,科律登在《牧歌》第2首中、麦里波乌斯在第7首中很快将动手做这些事情,但诗中的他们仍没有做。诗中对城乡关系的紧张有所暗示,但仅此而已。所有这些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那里得到了发展。《牧歌》内容是如此丰富,成了他们最好的矿源。但是,牧歌实质上是风雅和暗示性的。当后人企图把维吉尔诗中那些简短、暗昧的东西变得更加直白时,维吉尔的特点也就不可避免地损失了。
\r\r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没故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是4世纪关于维吉尔的不雅观念。它来自塞尔维乌斯对维吉尔的注疏。维吉尔的初版出版于1469年,两年后就出了塞尔维乌斯的注疏。很快,人们就把维吉尔的正文和塞尔维乌斯的注疏稠浊出版且成了老例。16世编年夜多数维吉尔的版本都属此类。当时,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受过教诲的人会只读维吉尔的正文而不读塞尔维乌斯的注疏,要创造塞尔维乌斯给人们描述的维吉尔曲直解的或者不完美的就更难了。塞尔维乌斯声称,维吉尔走过了一个墨客应该遵照的道路,先从创作档次较低的牧歌开始,接着创作中间层次的《农事诗》,末了在《埃涅阿斯纪》的史诗中达到了其创作的顶峰。正是这种不雅观念被塞尔维乌斯嫁接到对维吉尔文风的剖析上了,而这些对西塞罗和昆体良以来的人们都是非常熟习的,结果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牧歌在古代已经是一种完备成熟的文学类型,而且被置于诗歌的最底层。我们可以肯定,维吉尔并没有按照这种镇静、秩序井然的办法安排他的写作生涯,由于他重新派墨客的追随者变成了讴歌帝国的史诗吟游墨客是分外而又不可预见的,但这种不雅观念确实影响了后世的墨客。由于斯宾塞和蒲柏都想模拟维吉尔这个完美的墨客,而他的经历又遵照了完美的办法,以是他们都从创作牧歌开始他们的诗歌创作。
\r\r塞尔维乌斯对《牧歌》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既与我们对维吉尔的理解不同,也与今日盛行的牧歌有别。我们为维吉尔的高雅和精细所倾倒,塞尔维乌斯强调的则是该文体的低下和牧人的无知。他的偏差在于将《牧歌》视为寓言。纵然在这里,只管他险些错了,但我们却不能说他完备错了。麦纳科斯是《牧歌》第5首和第9首中涌现的一个墨客,与维吉尔有某些相似的特色。考虑到这些诗篇不可捉摸的特点,我们最多能说他既是维吉尔,又不是维吉尔。在《牧歌》第5首中,那已经去世去且已仙游的达菲尼斯,虽然实际上不可能是恺撒,但给人的觉得是他便是朱利亚斯·恺撒。这便是维吉尔式的象征方法,模糊而又不稳定。塞尔维乌斯走得更远,他见告人们,在《牧歌》第一首中涌现的提图路斯的女人加拉特娅和阿玛莉里斯,分别代表曼图亚和罗马。罗马的另一个象征是松树;泉水代表元老院的议员,灌木象征语法学家,诸如此类的还可以列出许多。这类说法显系胡说八道,但却很有影响。把牧歌当作道德寓言的文艺复兴传统均发轫于对维吉尔的这种误读。
\r\r《牧歌》第1首以提图路斯躺在山毛榉树荫下开头。塞尔维乌斯见告我们,提图路斯代表着维吉尔,这个说法乃至在本日的书中还在被人重复。但它是缺点的,由于诗中没有一个字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塞尔维乌斯(或者是他的资料来源)已经把稳到,在《牧歌》第6首中,阿波罗称提图路斯为墨客。由于误解了维吉尔的方法,人们把《牧歌》第1首中的提图路斯和第6首中的同名者混成一个人了。塞尔维乌斯的不雅观念产生了奇特的结果:由于他(有情由)希望麦纳科斯也代表墨客,以是在《牧歌》中,我们就有两个维吉尔。更糟糕的是,提图路斯和墨客太不相像了。他是一个年长的、头发花白的被解放奴隶,而维吉尔是个年轻的、生来自由的人。可是,维吉尔的荣誉,使得这些讹误也为后来的作家模拟。斯宾塞的《牧人历书》出版于1579年,完成时我们只通过注释中一个人名的字头E和K知道他。第一首诗为《一月》,引入了科林·克劳特这个人物,如E. K所说:“在这个名字下面,隐蔽着墨客本人的影子,由于维吉尔有时就藏在提图路斯这个名字后面。”可是在末了一首诗《十仲春》中,科林已经年迈,头发花白了(斯宾塞当时只有20来岁)。只管创造出了科林这个人物,《十月》中的库狄彷佛也代表着墨客。这些做法看似奇特,但如果是遵照维吉尔,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塞尔维乌斯的维吉尔的方法,则是完备可以理解的。
\r\r到16世纪,人们已经广泛地认同这样一种说法:自维吉尔以来,牧歌基本是一种风格低下、内容富有道德寓意的文学形式。锡德尼在《为诗歌辩解》中这样写道:
\r\r人们喜好牧歌难道错了吗?(大概由于它们处在诗歌的最低档,它们该当尽快被超越)。难道那可怜的乐器应该受到鄙视吗?它曾经放在麦里波乌斯的嘴里,吹出了那遭到严厉的主人和劫掠的士兵蹂躏下的公民的苦难。还有,透过提图路斯,我们看到,正是公民的善良,才使那些身居高位者得到嘉护。有时候,在狼与羊群的幽美故事中,我们可以创造所有关于恶行和耐心的思考;有时候,它见告我们,为小事争执,得到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胜利……
\r\r以比喻阐明牧歌的习气在这里不仅得到鼓励,而且被授予了更严明的色彩。在牧歌的传统中,这一类的有时实在发生得太常常了。维吉尔《牧歌》的第4首(如塞尔维乌斯已经指出的那样,它根本不是常日意义上的牧歌)说到一个孩子的出生,而这个孩子将把人类带回黄金时期。后来,它被阐明成是对耶稣基督出身的预言。这一步一旦迈出,人们就可以很随意马虎把更多基督教的内容与牧歌领悟起来了。人们把稳到,牧人是最早得到基督降生的人,以是他们的生活大概是一种特殊优秀的生活办法。福音书提到了绵羊和山羊,也提到耶稣曾经把自己比喻成牧人的事。两者合一,牧歌墨客就会把节制的牧人与那些傲慢的、野心十足的牧羊人进行比拟,斯宾塞《牧人历书》的《七月》便是这样做的。在《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中,人们还创造了这种说法的根据,在那里,牧人亚伯献上的捐躯蒙上帝悦纳,他那妒忌心十足的兄弟、农夫该隐就行刺了他。
\r\r维吉尔传统的寓言化和基督教养,在曼图安的拉丁文牧歌中有所表现。此人是15世纪卡迈尔派的修羽士(以是,他也提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以及耶稣基督出身时牧人在场的事情)。曼图安的措辞尽可能模拟维吉尔,但其精神截然不同。维吉尔的作品中有时会提到精明的女性,但绝没有曼图安牧歌第4首中那种长篇谩骂女性的东西,那里的内容更多地来自玉外纳;维吉尔的诗中间接提到过寒冷的景象,但绝无曼图安第6首中那种滴水成冰的冬天;维吉尔的牧人多少有点现实感,乃至粗俗(塞尔维乌斯指出了这一点,但有时强调得过分),但曼图安则谈到了牲口粪、阉割和清理下水道,乃至让他的一个牧人在栅栏后面大便(为了虔诚于被他误置的导师,曼图安让牧人为他的行为找了个借口,但其借用的那些语句实质上出自完备不同的背景)。曼图安的寓意化方向非常严重,其末了的4首诗中塞满了寓意式的语句。在《屈服的和不屈服的修羽士之间的辩论》中,这种做法达到了极致,那里所有的话都来自牧人生活和事情中的语句。
\r\r这些不那么精彩的诗篇在16世纪享有很高的荣誉。J. C.斯卡利泽鞭笞这些诗短缺男子汉气概、疏松而不切题,构造不佳,末端还补上一句:由于有些学校的校长更喜好曼图安而不是维吉尔,以是有必要鞭笞他(《诗学》,第6卷第1章)。可并不仅是校长们。亚历山大·巴克莱在为他自己的牧歌写的媒介中,夸奖了维吉尔,但给了曼图安棕榈叶(5)。熟习并不总是导致鄙薄,曼图安以是得到推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名气,他的作品在学校里用得多,其拉丁文的古典风格和劝人向善的内容受人青睐。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他的诗常常是孩子们在学校中学的第一首拉丁文诗。托马斯·洛杰在《为诗辩解》中问道:“有学问者能忍受失落去荷马,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失落去曼图安吗?”德拉顿回顾他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师时,环境是这样的:
\r\r他很快就开始上课了,\r 先给我读了一段老实的曼图安,\r 然后是维吉尔的《牧歌》……
\r\r在《爱的徒劳》中,莎士比亚让那个迂腐的校长霍罗福尼斯一出场就背诵了曼图安第一首诗的第一行:“Fauste precor gelida quando pecus omne sub umbra Ruminat(那头鹿,你知道,刚才还沐浴在血泊之中……)啊,善良的老曼图安!
……老曼图安!
老曼图安!
谁不理解你,又有谁不爱你。”这些话的可笑之处在于,霍罗福尼斯虚假的学问,不过是每个上学的孩子都会的拉丁文基本功。当加布里埃尔·哈维嘲笑罗伯特·格林缺知少识时,他说的是“他找遍了他上学时用的语法书”。(由于在他的书的边缝上写着同样“博学的”Fauste precor gelida)其手腕也可以归于这一类。这些事实的意义在于,人们可能在学生的童蒙期间就向他们先容了曼图安和维吉尔,而且韶光上非常靠近,当时他们还不能对两者作出细致的区分,他们有可能对拉丁语牧歌不加区分,将其作为一个类型,即维吉尔—曼图安型。普吞汉姆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一个比较精明的批评家,他意识到是曼图安把道德的内容注入到牧歌中的。谈论过维吉尔之后,他接着说:“这些牧歌中包含着一些道德原则,以改进人类的行为,如曼图安和近代其他墨客的作品那样。”可是,威廉·韦伯把维吉尔、卡尔普尼乌斯和曼图安等同起来,说他们:
虽然他们所写的事情看起来都是粗鲁和丑陋的,犹如那些淳厚的乡下人,可是他们也确实说出了不少同样令人高兴和有益的东西。由于这些人虽然外表淳厚,可是他们却能赞赏其朋友而无溜须之嫌,严厉地鞭笞对手而无尖刻之词。
\r\r这些大概并非精到之论,但它们有助于解释,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经由塞尔维乌斯的改造,维吉尔逐渐和曼图安混在了一起。其后果我们在《牧人历书》中已经看到了。斯宾塞公开模拟的是两个墨客,有时用粗俗、村落庄的措辞,有时用的是讽刺措辞。
\r\r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牧歌把两种看似对立的特点——约定性与多样性——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规则是如何强化的,多样性之以是可能,是由于在牧歌的背后,有古典文献本身存在。维吉尔的《牧歌》是如此多变,如此让人浮想联翩,又是如此的不拘一格,以是,它们和塞尔维乌斯、曼图安给我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另一种不同的不雅观点肯定会产生。文艺复兴时期,牧歌传统有两个紧张流派,让我们将其称为硬牧歌和软牧歌。关于硬牧歌,我们已经谈了一些,至于软牧歌,虽然它终极会取得支配地位,但时至今日,它对我们来说还是可以用“阿卡狄亚”这个词来概括。在阿卡狄亚,到处一片翠绿,仙女和乡下情郎们徜徉在汩汩流淌着的小河边和多彩的草地上,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纵然他们不足幸福,大概因单恋而伤心,终极也会融化为一种幽美的高雅情调。人们对这种已经损失的知足的追求,通过那句非常有名的话“Et in Arcadia ego”(纵然在阿卡狄亚也有我)表现出来。瓦格《再访布里斯海德》的第一部分取的便是这个标题。诗中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人对他年轻时期生活的回顾。
\r\r如果进行更深入的稽核,我们会创造,阿卡狄亚的故事是另一个系列有时势宜凑合的结果。“纵然在阿卡狄亚也有我”彷佛带有浓厚的古典味,但实际上它的产生不会早于17世纪。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革。我们第一次碰着这句话是在古厄西诺的画上,画面上有两个牧人,正看着一个骷髅,画的名字便是《纵然在阿卡狄亚也有我》。画面的意思显然是说,去世神无所不在,“纵然在阿卡狄亚,也有我的存在”。可是,这句话的出名,是由于普桑的那幅画。画中,牧人们正在刻着这句话的宅兆旁,那个去世去的牧人现在成了发言人,他的意思是“我也曾经到过阿卡狄亚”(这句话的拉丁译文应该是“Et ego in Arcadia”)。至此,去世神狰狞的警告变成了高雅的思乡情调,一个新的传统从此形成。它显然源于古典,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r\r全体有关阿卡狄亚的不雅观念实在是一个缺点。长期以来,人们都相信,是维吉尔将阿卡狄亚作为一种沉着的田园生活的象征创造出来的,但他实际上没有这样做。除了一处例外,他的牧歌背景不是阿卡狄亚,个中六首从未提到这个地方,另有三首只是顺便提到阿卡狄亚或者阿卡狄亚人。只有第十首牧歌因此阿卡狄亚为背景的。诗中说的是维吉尔的朋友、墨客加卢斯,由于追求浪漫的爱情正在去世去。这首诗的含义比较模糊,可能要根据已经失落传的诗才能明白个中的意义。可是无论是哪种情形,维吉尔所描述的阿卡狄亚和后来牧歌中涌现的阿卡狄亚完备不同。那是一个寒冷、荒漠、孤独而迢遥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它与维吉尔其他诗篇所描写的景致完备不同。没有一个古代和中世纪的墨客、评论家或者注释家提到维吉尔曾经把阿卡狄亚作为牧人生活象征创造出来,由于他确实没有创造出它来。
\r\r相反,近代有关阿卡狄亚的不雅观念应归功于尼亚波里斯的人文主义者雅可波·山纳扎罗(1458—1530)。他的《阿卡狄亚》(1504年出版)是一个牧歌诗与散文阐述的稠浊物,讲述了一个叫山纳扎罗(代表山纳扎罗本人)的名流,为爱情所苦,隐退到一个俏丽而宜人的村落庄的故事。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山纳扎罗缺点地阐明了维吉尔的作品,而且这是一个天才的缺点。他的新阿卡狄亚是从维吉尔的《牧歌》中发展而来的,但也包含了《埃涅阿斯纪》第8卷中的某些内容。在该卷中,埃涅阿斯访问了未来将成为罗马城的地区,创造那里有一个小城市。城市是由来自希腊阿卡狄亚地区的流亡者建立的,由一个叫厄凡德尔的国王统治。在罗马旧址上曾经有阿卡狄亚人居住的传统,比维吉尔要古老得多,但可以肯定,它和牧歌的不雅观念没有任何联系。可是,维吉尔对它的处理,使人们可能将其接管到一种新的牧歌版本中。他把厄凡德尔描述成一个富有王者气候和某种村落庄名流谦和品质的稠浊物。在某些方面,这是与近代版本的乡绅最靠近的古典资料来源。山纳扎罗之后,它成了牧歌故事中的紧张题材。
\r\r不过山纳扎罗的不雅观念也可以算作是从维吉尔的《牧歌》本身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维吉尔的同代人加卢斯因此他本人的名字涌如今牧歌中的;麦纳卡斯是个近似于墨客本人的人物;达菲尼斯暗示着朱利亚斯·恺撒。所有这些都与那种贵族因某种缘故原由(如躲避仇敌之类)遮盖真实身份,把自己伪装成乡下人的故事很不相同。但从一个主题可以随意马虎地转到其余一个,特殊是在对《埃涅阿斯纪》产生缺点理解的情形下。从另一个角度看,山纳扎罗可以说把实际上由龙古斯创造的、柔柔而散漫的牧歌,授予了轻微的维吉尔色彩。达菲尼斯和克洛厄过着卑微的牧人生活,但结果证明,他们是崇高人家的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就被抛弃,在农夫的抚养下终年夜。这个主题很受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欢迎。到16世纪末,牧歌式的浪漫便是根据希腊的小说阐明的,从此使龙古斯也变成了维吉尔传统的一部分。
\r\r山纳扎罗的《阿卡狄亚》在欧洲广受欢迎,并且引出一系列模拟者。在西班牙,蒙特迈耶写了《狄安娜》(1559年),并成为创作堂吉诃德浩瀚灵感的来源之一。在英国,《阿卡狄亚》也受到敬仰,由巴托罗缪·容格译成英语出版(1598年)。英国的两部浪漫小说:托马斯·洛杰的《罗萨林德》(1590年出版)和罗伯特·格林的《潘多斯托》(1588年出版)也是受其启示而作,并成为莎士比亚《皆大欢畅》和《冬天的故事》情节的来源。锡德尼的《阿卡狄亚》有些不同。在其早期的形态上,即《旧阿卡狄亚》中,它追随的是传统的浪漫牧歌的套路,《新阿卡狄亚》到他去世时仍未完成,故事要长得多,而且把战斗和宫廷冒险与牧歌式的规整领悟在了一起。锡德尼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原谅了牧歌的伪装题材:主角是出身崇高的男女,但穿的却是乡下人的服装,颇像《皆大欢畅》中的人物。但牧人腓力西德斯是锡德尼创造出来的人物,其风格更靠近维吉尔。这样,从繁芜到大略有了两种不同的办法。
\r\r塔索《亚明塔》的上演(1573年),使牧歌戏剧在意大利盛行开来。在他的继续者中,瓜里尼因其《忠实的牧人》(Il Pastor Fido)(1589年上演)享有特殊高的声誉,它的成功勉励弗莱彻创作了《忠实的牧人》(约1610年)。《亚明塔》还鼓励了那种把软牧歌与黄金时期传说领悟起来的方向。黄金时期的传说起源于希腊,最初见于赫西奥德的作品。神话说,宙斯最初创造了黄金种族的人类,然后将其毁灭,以白银种族取代。衰落的系列在连续,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先后产生,末了是黑铁时期,即我们生活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理解黄金时期神话的最好来源可能是奥维德《变形记》的第1卷以及维吉尔《牧歌》的第4首。在这首诗中,墨客想象赫西奥德的序列被颠倒过来,黄金时期因此再度归来。在维吉尔的《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中,黄金时期的传说也以某种不同的形式存在。这是一个关于天国的传说,是伊甸园传说的古典版本。那时,葡萄挂在树枝上;树分泌出蜂蜜;由于大自然自动供应了统统,因此人们不用劳动;在一些版本里,还有当时无私有财产的说法,由于人们都合乎道德而无私地生活着,共享所有的财富。因此,有关黄金时期的传说和田园诗或者阿卡狄亚式的牧歌实质上相称不同。但塔索通过在个中插入了一句“O bella età de l’oro”(意思是:啊,可爱的黄金时期!
)的咏叹调,使二者的界线开始模糊。《亚明塔》弥漫着淡淡的哀愁,咏叹调所期待的,是那个与剧本本身所处的不同的天下。但由于许多田园诗式的牧歌都带有思乡情调,以是人们随意马虎把对阿卡狄亚的神往转变成对失落去的黄金时期的期盼。在锡德尼的幸福乐土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牧人的孩子在吹笛子,就彷佛他永久不会朽迈似的”(《新阿卡狄亚》,第1卷第2节)。人们想描述的不是乐园,而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短暂地得到这样的幻觉:严厉的韶光和变革法则暂时停滞了。这是范例的阿卡狄亚特色。可是有时候,锡德尼的阿卡狄亚彷佛又完备变成了乐园(第1卷第9节):
你难道没有瞥见那比翡翠还要绿的青草吗……你是否瞥见了其他那些俊秀的花呢?它们每一朵都须要我们去理解,用生命去表现。这些崇高的大树虽已届老龄,但仍旧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由于这里任何美的东西都不应当消退。……这些清亮、愉快的小溪流淌得多么缓慢,彷佛不愿离开这结合如此完美的地方。它们发出的抱怨声是多么的甜美,由于它们不愿拜别。
\r\r锡德尼在这里实践的,是他在《为诗歌辩解》中所倡导的原则:文学可以高于现实,描述出一个比我们居住的天下更可爱的天下。“大自然所供应给我们的画面,远不像墨客们所描述的那样丰富多彩,它既没有快乐的河流、自动结果的果树、芬芳甜美的花朵,也没有那些足以使我们这个天下变得更加可爱的东西。它供应的是青铜的天下,而墨客们描述的是黄金时期。”在他伟大的作品中,锡德尼为我们表现的,便是这个天下。
\r\r塔索的牧歌剧还给黄金时期的神话增长了一个内容,那便是曾经有过一个爱情自由的时期,性活动完备自由。那里没有犯罪,唯一的规则是,你可以做任何你乐意做的事情(S’ei piace, ei lice)。这项内容在古典时期大多数有关黄金时期的神话中是没有的。只管提布鲁斯曾经触及,但在任何版本中,这一点都不突出。黄金时期神话的这个新内容,是对基督教严苛道德哀求的反应,因此是后古典时期对古典神话的利用。牧歌因此也随意马虎成为人们躲避的一种方法,一种与现实对照的参照系统。可是,它也可以做事于普通的目标,成为一个人们根据公认的规则对道德责任的苦乐进行稽核的场所。锡德尼笔下的莫西多罗斯就把他周围的动物的性开放与他本人必须忍受的对帕梅拉激情的克制进行了比拟:
\r\r当我主人的牲口到这个新地方来吃草料的时候,我有许多次看到那些年轻的公牛可以证明它们的爱情。但如何证明?看它们那自满而高兴的神色。于是我自言自语地说,啊,可怜的人类,那本应主宰他幸福的聪慧,如今却变成了他幸福的叛徒。这些动物,就像天性未泯的孩童一样,悄悄地继续了这份福泽。而我们,倒像私生子似的,只能躺在表面,受痛楚和悲哀的煎熬。他们不妒忌肉体的快乐,也勿需遏制感官的享受。我们却得受名誉的阻碍以及良心的折磨。
\r\r这种思想的种子在忒俄克里托斯那里就有,但实质上是公元往后才发展起来的。当人将自己置于大自然中,才创造自己和自然界的别的部分存在无法超出的鸿沟。后来的牧歌作者还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的。
\r\r到16世纪后半期,硬牧歌已经比古典牧歌变得更硬,软牧歌则比古典牧歌变得更软。在维吉尔的牧歌中,软、硬两种成分都有,但是后来,他精心稠浊的成分又被人们分解出来,变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牧歌实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类型,作家们又很自然地试图把这两种成分稠浊起来,或者说把各种不同样式的牧歌并列,让它们相互揶揄对方。锡德尼的《阿卡狄亚》从某种程度上便是一个综合各种流派的例证,现实的、浪漫的、道德的、寓言的、田园诗的、哀伤的,搜罗万象。塞尔维乌斯和曼图安的影响仍在连续,以是人们从维吉尔那里取用的名字多是粗俗之辈,如达麦塔斯、毛普萨等,而那些比较高雅的牧人的名字,或者取自其他资料来源,或者是新创造的带古典色彩的名字。《冬天的故事》表现了这种方向:比较高尚的女牧人被称为潘狄塔,虽然这个词很可能是拉丁语的,但意大利味十足,她是个“遗失落的女孩”。但毛大姐便是个普通的屯子姑娘,只适宜乡野村落夫向他求亲“叫毛大姐做你的情人吧;好,别忘却嘴里含个大蒜儿,接起吻来味道好一些。”(第4幕,第4场,第164行)。这个名字本身在维吉尔的作品中没有涌现过,而是“mopsus”一词的阴性形式,在这样的高下文中,它无疑是非常恰当的,由于“mops”和“mopsy”的意思都是“姑娘”,“mopsy”同时也是一个针言,用以描述一个衣衫不整或者邋遢的女人。值得把稳的是,人们认为,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有利用代价。人们以为,这样一个粗俗的英国乡下村落妇形象与维吉尔笔下的人物比较靠近。
\r\r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类型,牧歌可以成为它自身的批评者,有时,我们乃至可以在牧歌入耳到反对牧歌的声音。在《冬天的故事》中,有这方面的暗示,不过仅仅是暗示而已。格林把他的《潘多斯托》划分为波希米亚和西西里两部分,非常自然的是,村落庄场景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由于每一个维吉尔的读者都知道,由于忒俄克里图斯的缘故,这块地皮与牧歌有着分外的关系。莎士比亚则不可理喻地颠倒了格林的做法,把宫廷戏放在西西里,村落庄戏放在波希米亚,因此导致他犯了个尽人皆知的缺点,给波希米亚划定了海岸线。纵然只学过小拉丁语,他肯定也知道牧场在西西里。或许他是故意揶揄牧歌的一些规则?弗罗利泽王子已经遮盖了他的身份,他是带着一种空想化色彩和合宜的阿卡狄亚式的忠实崇拜潘狄塔的。可是,莎士比亚让他的主人公的浪漫做事于一种精心营造的讽刺。与弗罗利泽比较,潘狄塔的话语有时就像一个真正的乡下姑娘那样直白(第4幕,第4场,第154行):
\r\r弗罗利泽:把你的手给我,我的潘狄塔,就像一对斑鸠那样,永不分开。
\r\r潘狄塔:我誓愿如此。
\r\r她意识到,纵然是最富有诗意的激情,也仍旧因此现实的肉体为根本的(同上,第101行以下):
\r\r我不愿用我的小锹在地上种下一枝,正如假如我满脸涂脂抹粉,我不愿这位少年夸奖它很好,只由于那副假像才想娶我为妻。
\r\r可是,莎士比亚并不打算抛弃阿卡狄亚的俏丽,潘狄塔被故意识地置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维吉尔的牧人曾经也是如此),末了证明她曾经出身崇高,虽然从刚出生起就由牧人抚养,不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她天然的高雅与本色仍表现了她崇高的出身。在维吉尔《牧歌》的第2首中,有一段关于花的经典描写。借助潘狄塔之口,莎士比亚对维吉尔想象力中高雅的一壁作出了回应(参看本书第7章)。潘狄塔既是、又不是一个村落姑。她坦直而又浪漫,这种模棱两可的环境来自相称不同的希腊爱情描写传统,倒与维吉尔的精神相去不远。
\r\r17世纪,大概还要早些,牧歌中温软的一壁逐渐霸占支配地位。斯宾塞晚年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型。诗歌《科林·克劳特再度归来记》、《仙女王》第6卷中插入的牧歌仍是寓言式的,但变得更加柔和。德拉顿早期的牧歌深受《牧人历书》影响,但他的末了一个牧歌集子《缪斯的伊丽齐乌姆》(1630年出版)更加富有韵律美和田园诗色彩。至此,牧歌的天下同时也是黄金的天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伊丽齐乌姆)便是“现实的乐园”(Elysium)(6),拥有“永久不会消逝的快乐”和“常绿的橄榄枝”,橄榄枝的叶子永久不会落下,夜莺一年四季都在歌唱。可是,那常常刺激阿卡狄亚模式的哀愁在这里也涌现了,那便是:这个幸福的天下已经损失了,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硬派牧歌作者曾经认为,描写他们熟知的那类村落民是忠实于维吉尔的精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精确的。软派的牧歌作者则转变了他们的做法。他们用浪漫的笔调描述那种熟习的、令人喜好的乡间景致。德拉顿的“伊丽齐乌姆”既是英国,又是抱负的国度。威廉·布朗尼在《不列颠牧歌》(1613年出版)中变得更加温和,把他的家乡德文郡神话化了。稍早些,斯宾塞在《科林·克劳特再度归来记》(1595年出版)中,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对爱尔兰的描写。如果再向前追寻一些,可以看到蒙特迈耶的《狄安娜》,它把牧歌式的爱情融进了来昂的风景中。在大多数作品中,古典作品的影响是微弱而渺远的。可是,它们与维吉尔的《牧歌》又有真实的亲缘关系。在《牧歌》中,维吉尔曾经把希腊的牧人放在意大利的风景中,并且通过现实和非现实的领悟授予他们以生命。
\r\r通过稽核当代人对维吉尔作品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教养的阶层有关牧歌的不雅观念正在发生变革。亚伯拉罕·弗莱明在其1589年的《牧歌》导言中,曾经为《牧歌》的“粗俗”和“村落庄风格”辩解,他那沉闷的节奏和韵律也与他的辩解贴切。下面是他翻译的维吉尔《牧歌》的卷首语,是用无韵的十四行诗体翻译的:
\r\r提图路斯舒适地躺在山毛榉树荫下,\r 用一支细细的牧笛演奏山野歌曲,\r 我们将离开美妙的村落庄和甜美的草地,\r 我们将离开故土,而你提图路斯在树荫下清闲,\r 山林中回荡着你赞颂仙颜的阿玛莉里斯的歌声。
\r\r1628年,威廉·李斯勒以斯宾塞为典范,重新翻译了维吉尔的作品。不过他所追随的斯宾塞不是《牧人历书》中那个单调乏味的斯宾塞,而是《仙女王》中金色的斯宾塞。他用不同的韵律,以7行一节的斯宾塞办法,翻译了维吉尔的第一首诗:
\r\r你躺在山毛榉树下宽大的阴影中,\r 提图路斯啊,你清闲地躺在那里,\r 手持牧笛——你银色的缪斯,\r 可我们将离开美妙的地皮,逃离可爱的家园,\r 你却能悄悄地躺在树荫里,\r 让山林回响着你\r 对阿玛莉里斯的颂赞。
\r\r李斯勒曾以“甜美的金色”形容“这些幽美的牧歌”,他虽然相信个中存有寓意,但对其道德意义却不予采信。寓意现在变成了甜美的果汁,诗歌的表面意义则成了闪光的外表,“当人们把眼力只盯在这些幽美诗歌的外表上时,他们很可能会为其甜美的滋味而愉快”。在约翰·比德勒轻松、流畅的双行押韵的译作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内涵(1634年出版):
\r\r提图路斯啊,你在山毛榉的亭盖下高卧,\r 用那纤纤芦管试奏着山野的清歌;\r 而我就要离开故乡和\r 可爱的田园,亡命他国,\r 你则在树荫下清闲,\r 让山林回响你对仙颜的阿玛莉里斯的夸奖。(7)
\r\r在李斯勒和比德勒的译文中,我们看到,维吉尔与布朗尼、德拉顿以及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其他牧歌墨客更加靠近。维吉尔仍旧是牧歌创作的宗师,但这位宗师是用富有张力的材料制造的。
\r\r从这个背景看,弥尔顿在《黎西达斯》中对教士腐败的鞭笞所采取的严格寓意手腕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一种向《牧人历书》(弥尔顿曾有几处模拟了《牧人历书》)乃至曼图安风格的回归。如《失落乐园》一样,《黎西达斯》表明,弥尔顿将是一个像巴赫那样的天才,一个大器晚成的天才。可是,阴郁只是该诗风格的一部分,由于《黎西达斯》是所有把牧歌诗体化考试测验中最成功的。其他作家们只是把文艺复兴以来涌现的各种牧歌凑集在一起,弥尔顿对各种成分的领悟则是在维吉尔本人的鼓励和辅导下进行的。
\r\r阿瑞图萨圣泉,你曾经给泛滥\r 而奔流的敏吉河名誉,让它的河岸布满芦苇\r 我曾听到用苇管演奏的高雅曲调,\r 但如今我的牧笛要开始演奏了……
\r\r阿瑞图萨出自《牧歌》第10首,敏吉河出自第7首,牧笛从最开始便是牧歌的标志之一。然而上引第3行以及整首诗的不雅观念则是维吉尔《牧歌》第4首的开头那句:“西西里的缪斯,让我们唱雄壮些的歌调。”弥尔顿从维吉尔那里接过了这样一种不雅观念:在牧歌范围内,可以对语调和程度进行调度。乃至在某人评论辩论一种半是半非的牧歌时,他也向这一诗体的前辈们乞助。在向“西西里的缪斯”乞助时,维吉尔想到的是忒俄克里图斯。弥尔顿则既向维吉尔(其家乡曼图亚就在敏吉河边),通过维吉尔,又向忒俄克里图斯乞助(阿瑞图萨是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的泉水)。因此,他将自己汇入了牧歌的伟大传统之中。
\r\r《黎西达斯》不仅是英语中最伟大的牧歌,而且也是最富有维吉尔特色的牧歌。这不仅是由于他利用了大量《牧歌》中的典故,而且是由于弥尔顿对维吉尔的意图有深刻的把握和理解。诗中有对《牧歌》细节上的模拟。例如,在维吉尔诗歌中确实很严明的地方,弥尔顿就鞭笞它(第123行以下):
\r\r在他们开列花的清单的时候,他们那些干瘪无味的歌曲\r 连可怜的稻草秆发出的尖叫都比它们好听……
\r\r那刺耳的叫声,连同讽刺性的内容,都是直接从维吉尔《牧歌》的第3首第27行搬过来的(这一行曾经让德莱顿认为,如果维吉尔乐意的话,他可以成为罗马最精良的讽刺墨客)。在诗的末端,那段非常幽美的对各种花的特性的描述,同样也取自维吉尔传统(第142行以下)。更故意义的是,弥尔顿创造了维吉尔的方法,这种方法使维吉尔能够用动人的笔调,描述那些因这种或那种缘故原由不易直接处理的东西。在描写黎西达斯被收受接管到天国时,弥尔顿模拟的是《牧歌》第5首中有关达菲尼斯到达奥林匹斯山的部分。基督教的再生与异教的神话是非常不同的,不过也正是这一点给弥尔顿供应了机会。除非借助于某些比喻或者修辞手腕,否则人们是无法想象天国的景象的,维吉尔的诗给他供应了所须要的比喻,使他能够创造出一个纯洁而极乐、但又不会单调的虚幻天下(第174行以下):
\r\r在那快乐而友爱的幸福王国里。\r 除了橄榄树和沉着的小溪外,\r 还可以用纯净的神液洗去发辫上的污渍,\r 听到那难以言传的婚礼歌曲。\r 所有的天使都欢迎他,\r 在神圣的行列和甜蜜的社会里,\r 人们唱着盛赞其光荣的歌曲,\r 从他的眼里永久地抹去了悲哀。
\r\r弥尔顿大概从《埃涅阿斯纪》的第6卷中也借鉴了某些内容。在那里,维吉尔用一种靠近英雄牧歌的笔调,描述了极乐世界的环境。那里阳光残酷、四季常青,轻松的自由活动成为极乐境界的核心部分。
\r\r有时候,维吉尔也对牧歌加给他的限定表示不满。在《牧歌》的末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第10首第70和75行以下):“这些就够了,女神,让你们的墨客拿去唱,当他闲坐着,用纤细的芦管编着篮筐……让我们起来走吧,暮气对唱歌的嗓子不利,杜松的阴影是很坏的,连对庄稼都无益,山羊们吃够了,回家去吧,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某种讽刺的意味,那一贯让牧人们喜好的树荫,如今成了麻烦。牧歌诗适度的俏丽,通过那小小的篮筐和它材料的卑微表现出来,这时彷佛也不足了。但“让我们起来走吧”一句,有些模棱两可,是我们起来回家,仍旧勾留在牧人生活的圈子里,还是彻底躲避这种生活?在他自己的诗的结尾处,弥尔顿利用了牧歌最常常性的象征——树木,捉住了这种不愿定的东西:
\r\r陌生的乡下年轻人就这样对着橡树和小溪唱着……\r 太阳长长的影子曾经笼罩了山冈,\r 如今已沉入了西山,\r 末了他站了起来,用力挥舞着他蓝色的年夜氅;\r 来日诰日将会有新的树木,新的草地。
\r\r末了一行第一个短语中,墨客韵律里重视的是“树木”,而在第二个短语中,强调的是“新”,两者间有细微的差异。我们无法确定的是:来日诰日带来的,将是更多的牧歌,还是从牧歌转向其他类型诗歌的躲避?在这里,牧歌再次显示出它对自身的反思,既不乏批驳精神,又深受喜好。
\r\r18世纪的人们虽然创作了大量牧歌,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并不多。安布罗斯·腓力普斯的牧歌《拿泊·潘泊》只是在里手的圈子内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并刺激约翰·盖伊写出了他的讽刺诗《牧人的一星期》(1714年出版)。这部作品再次提醒我们:只管盖伊本人并未讥讽过分,甚至影响他对屯子题材的热爱,但讽刺从来便是牧歌的一个类型。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我对我的祖国不列颠的热爱,匆匆使我站出来,直白地描写我们那些勤恳而老实的农人,无论如何,他们像西西里和阿卡狄亚的农人一样,须要一个不列颠墨客模拟那里的墨客描写他们。我当然清楚,最近一些年轻人曾经用精心拼凑的无聊文辞,批评农人的卑微和卑下,我不清楚的是,他们限定牧歌描写的那个黄金时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的诗中所涌现的一些人物名字古怪,如布肯内特、格鲁比诺尔、布鲁兹林达(8)等,当他像腓力普斯那样描述其他人的时候,他直接取材于《牧人历书》,这是斯宾塞在近代仍拥有影响的一个例证,由于他的诗中也塞满了维吉尔的典故。
\r\r也是在18世纪,牧歌的影响从文学扩大到其他艺术形式领域。在园林方案中(斯托海德复活了克劳狄的意大利牧歌景致,舒格波鲁的公园中有一牧人雕像,上刻铭文为“我也曾到过阿卡狄亚”);在德累斯顿的瓷雕女像中,有《塞维里斯》和《切尔西》;在凡尔赛,宫廷贵妇们把她们自己打扮成乡下牧人的样子容貌住在伪饰的村落落里。乃至在音乐中,牧歌也产生了影响。在18世纪所有的牧歌剧中,大概汉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特娅》(脚本为盖伊创作)最成功地展示了间隔、传统、外在美、乃至诙谐如何能够实际上加深、而不是减弱痛楚感。乃至器乐曲也带上了牧歌色彩: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名字是他的出版商给取的,紧张是由于末了一个乐意的田园气息;但《田园交响曲》的思想则是他本人的。他那伟大的弥撒曲的末了一个乐章与那些更早的作品有许多同等之处:都采取六—八韵律、长持续音、旋律简洁、强烈的全音阶协奏乃至关键的D大调,都是与奏鸣曲同等的。当迢遥的战役的声音——军号和战鼓——侵入到和平的祈祷声中时,那被打断的祈祷声却带着牧歌情调的天真与谦恭,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可是,不管它多么富有维吉尔色彩,人们当然仍可以说,音乐和古典没有任何联系。古典传统所供应的,乃是牧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觉得,它确实与以前的传统有某种关系。牧歌的规则可以变革、发展,乃至末了它起源时的那些特色消逝殆尽,但保存下来的,是规则这一观点本身。
\r\r18世纪是牧歌的硬派特点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逝的期间。1717年,蒲柏在《论牧歌》中明白无误地流传宣传:“牧歌是那种他们称之为黄金时期的景象。”乃至雅各宾派的雅克–路易·大卫在1798年打算给《牧歌》绘插图时,也选择了保留某种洛可可风格的相对温软的新古典主义手腕。只管他们谁也没有把稳,革命派实际上与另一个牧歌派的人物——玛丽·安东内特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文学领域中,18世纪是牧歌衰落的期间。在这方面,萨缪耳·约翰生对《黎西达斯》的批评具有主要意义(见其《墨客列传》之《弥尔顿》):“它的形式是牧歌体,夷易、粗俗,因此让人恶心。”如果有谁认为《黎西达斯》夷易或者粗俗,那倒有些奇怪,不过约翰生的批评对他本人所处时期的很多牧歌来说,倒是非常恰当的。“我们不能认为它是感情的真实表露,由于真情不可能跟在过去的典故和模糊不清的评论后面。真情不会从桃金娘和百合枝上摘果子,也不会去拜访阿瑞图萨泉和敏吉河,更不会讲粗鲁的羊人或者长着怪脚的动物。人们只要有韶光抱负,就不会有痛楚。”这里具有启迪意义的不是他对弥尔顿成功的判断,而是他谢绝用牧歌本身的措辞来评判它。约翰生精确地指出,《黎西达斯》并非真情痛楚的流露,但它本非此意。除非人们规定,所有抒怀诗必须表达强烈的个人情绪,否则这一类的批评只能是无的放矢。维吉尔已经见告我们如何通过间接和模糊手腕,把公共与私人、个人与客不雅观的东西领悟在一起,典故和对情绪的克制,可以取得新奇的表达痛楚的效果。弥尔顿很好地把握了维吉尔的这种方法,可约翰生没有。随着后来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知识阶层逐渐失落去了他们古老的利用规则的直觉。
\r\r从18世纪末起,牧歌的历史就不连贯了。华兹华斯的《迈克尔》太短缺文学典故,以是它的副标题《一首牧歌》看起来是把这个术语作为一种比喻或者比较利用的,他彷佛是说,“这是一个未经润色的威斯特摩兰牧人的故事。如果处在其余一个时期,人们大概就用牧歌的形式阐述它了。”在雪莱哀悼济慈的《阿多尼斯》(1821年揭橥)中,对牧歌的利用不过是标题中的一个词而已。可是,这就把我们带到牧歌的另一半,这另一半标志着牧歌传统的进步。自中世纪以来,维吉尔的《牧歌》第5首一贯是人们创作哀歌诗的样板,在一首佚名的、标题为《哀悼比奥尼斯》的希腊诗篇中,人们创造了用牧歌哀悼已故墨客的古典先例。可是,一贯在英国盛行的用牧歌哀悼墨客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的文学中没有对应的传统,而且险些是有时涌现的。锡德尼的英年早逝及其英雄业绩,曾经鼓励不同的墨客向他表示敬意,个中最突出的是斯宾塞的《阿斯特罗菲尔》。《黎西达斯》纪念的是爱德华·金,不管是多么不可能,弥尔顿仍旧把他刻画成一个墨客(第10行以下):“谁会不为黎西达斯歌唱?他本人就唱得非常美妙,并创造了旋律。”雪莱给济慈创造了一个希腊的假名,从而把自己也置于这一传统中。他的问句模拟的是弥尔顿:
\r\r当他,你的儿子,躺在这里,\r 被那阴郁中飞行的利箭撕碎的时候,\r 伟大的母亲,你在哪里?\r 当阿多尼斯去世去时,\r 孤单的乌拉尼娅,你在哪里?
\r\r弥尔顿的原诗是(第50行以下):
\r\r当无情的深渊淹没你们热爱的黎西达斯时,\r 仙女们,你们在哪里?
\r\r弥尔顿在这里模拟的是维吉尔《牧歌》的第10首。同样是在这首诗里,一些神秘的人物前来安慰干瘪的加卢斯(第19行以下):“牧人来了,那迟缓的赶猪人也来了,麦纳科斯来了……阿波罗来了……阿卡狄亚的神潘来了……”在自己的诗中,雪莱把这些神秘人物变成了抽象的圣灵(第109行以下):
\r\r其他的神也来了……希望与崇拜之神\r 有翼飞行的说服之神和罩着面纱的命运之神\r 光辉之神和惨淡之神……
\r\r虽然雪莱向牧歌寻求灵感,但他寻求的并非牧歌中的牧歌成分,那里既没有《阿多尼斯》中曾经涌现的绵羊,也没有牧人。
\r\r牧歌体哀歌墨客中的末了一位是马修·阿诺德和他为纪念克劳而写的《图尔西斯》(1866年揭橥)。让人抵牾的是,这首诗彷佛恰好证明了牧歌正在消亡的事实,由于只管它取得了非常的成功,但它就像他的希腊悲剧《麦罗帕》一样,故意地显得非常古奥。值得把稳的是,虽然诗中偶尔参考《黎西达斯》和《牧歌》,但利用的紧张典故不是来自以维吉尔为核心的欧洲传统,而是希腊的田园诗。常常萦绕在阿诺德脑海中的,是人类生命的短暂和历久的自然界之间强烈的比拟。图尔西斯去世了,布谷鸟却总是会来的(第71行以下):
\r\r它听不见,它悄悄地来,轻轻地飞!
\r 有什么关系?明年它还会回来的,\r 在甜美的春天里,我们又会听到它的叫声,\r 还有那些葱翠的灌木、挺立的蕨类\r 以及森林道路边蓝色的铃花\r 新割的干草的喷鼻香味。\r 可是我们的乡下情郎图尔西斯再也看不到这些了……
阿诺德模拟的是《吊唁比奥尼斯》(第99行以下):“啊,锦葵,当它们在园中枯萎的时候,那些葱绿的欧芹和卷曲的大茴喷鼻香又茂盛起来,明年它们还会再长的。可是我们这些高大、强壮、聪明的人,一旦去世去……就会长长地休眠,永无休止,再也不会醒来。”在《阿多尼斯》中,雪莱已经接管了希腊墨客的这种思想(第153行以下):
\r\r唉,我是多么不幸!
冬天周而复始,\r 痛楚随着年轮的循环又来;\r 空气与溪流总能不断更新它们的快乐,\r 蚂蚁、蜜蜂、燕子每年归来;\r 鲜嫩的枝叶和花草点缀着去世者的棺材,\r 热恋的鸟儿在林间出双入对……
雪莱末了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认知者,去世也。”可是,一旦去世去,“他再也不会醒来,啊,永久不会了!
”丁尼生所写的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哀歌,听起来也是如此(《怀念》,第2首):
时令让花再度开放,\r 把初产的幼畜送到羊群中……\r ……\r 可这些花不是为你开放……
\r\r奥斯卡·王尔德无疑是理解阿诺德和他的希腊样板的,因此,在《道林·格雷的画像》(第2章)中,让他的亨利·沃顿勋爵再度表达了这一思想:“由于对你来说,青春如此短暂,山花会凋落,但它们会再开。到明年6月,金链花又会像现在一样金黄残酷,一个月后,铁线莲会犹如紫色繁星。年复一年,它绿色的枝叶上同样会挂满紫色的花萼。但我们的青春从此一去不回。”可是我们不能确定所有这些是否便是受了《哀悼比奥尼斯》的影响。后来,它还不断会涌现,成为表达那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已经存在的一种情绪的模式。阿诺德确实给希腊的思想增长了一点新的东西:自然界对人的漠不关心(“它没有听见”)。他的布谷鸟彷佛也不是来自希腊的田园诗,而是济慈的夜莺,那不朽的、不是为去世而生的鸟,数千年来,它一贯唱着同样的歌。还在更早的时候,牧歌墨客——借用弥尔顿的话说——已经喜好“玩弄那些虚假的想象”了,抱负着大自然会同情牧人,绵羊、树木、河流都曾经为达菲尼斯或者黎西达斯的去世哀悼。现在,维吉尔的传统已经被抛在了一边,另一种牧歌为人们表达相反的情绪供应了样板,这种情绪看重的是我们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之间的间隔。
\r\r深邃的蓝天成为19世纪的作家们表达人类孤苦无助时孤独的另一个象征。以是,盖斯凯尔夫人《北方与南方》(第5章)的女主人公,在感情低沉的时候,瞩目着那“深邃无垠的蓝天深处……那永了望不到尽头的天空深处,它悄悄地……将地球上发出的痛楚的叫嚣,接管到那无限巨大的光芒中去”。蓝天和自然界春天的历久更新两个主题,在马勒的《大地之歌》中被领悟到了一起,它最初表现为绝望的愤怒,末了是泛神论式的接管。Das Firmament blaut ewig——“苍天是永恒的蓝色,大地在春天总是在固定的节令着花。可是你呢,人类,你能活多久?……可爱的大地春天里繁花如海,苍翠葱绿。蓝天永久笼罩!
永久……永久……”。我们听到的是浪漫主义后期“maladie du siècle”(癫狂的世纪)的声音,但其利用的词汇来自汉斯·比特对中国抒怀诗的阐释。不管是古代希腊,还是古代的中国,两者彷佛都不主要。创造性的心灵现在乞助于这些古老的思想来源,不是把它们当做老师,而是将它们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
在牧歌的早期历史中,环境是多么不同,那时作家们都模拟维吉尔曾经做过的、或者是他们认为维吉尔曾经做过的统统,而且是带着崇敬与感激进行的。这种对传统的尊敬并不排斥变革与创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维吉尔的误解和歪曲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忠于传统竟成为形成牧歌古怪而独特历史的紧张缘故原由之一。纵然我们把牧歌的观点稍加扩大,在20世纪还能找到那么一两个此类墨客,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牧歌已经消亡。像图尔西斯一样,它一旦去世去,就会永久消逝,但它是否还会像达菲尼斯、黎西达斯那样,或者如春天的大地那样,得到新的生命呢?当代盛行的“文献交叉”,纵然不会在作家中,也会在评论家中鼓励人们复兴这种文学类型,由于它实质上也是依赖先例和规则的。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就预言,人们很快会再度听到牧笛的声音,不免失落之浮躁,由于如果牧歌未曾存在过的话,那也不会有必要去发明它了。
\r\r Further Reading\r\rThere is a commentary on Virgil’s Eclogues by R. Coleman (Cambridge, 1977). On Arcadia: B. Snell,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r. T. G. Rosenmeyer (Cambridge, Mass., 1953), ch. 13 (‘Arcadia: The Discovery of a Spiritual Landscape’—a famous and suggestive essay, though wrong in some respets); D. Kennedy, ‘Arcades ambo: Virgil, Gallus and Arcadia’, Hermathena, 143(1987), 47–59; R. Jenkyns, ‘Virgil and Arcad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9(1989), 26–39. The story of ‘Et in Arcadia ego’ was revealed by E. Panofsky in R. Klibansky and H. J. Paton (eds. ), Philosophy and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Ernest Cassirer (Oxford, 1936), 223–254, reprinted in Panofsky, Meaning and the Visual Arts (1955), 295—320.
\r\rVarious works study pastoral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iterary critic: W.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London, 1935) (some fine aperçus, though little of the book is actually concerned with pastoral, despite the title); R. Poggioli, The Oaten Flute: Essays on Pastoral Poetr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Cambridge, Mass., 1975); P. V. Marinelli, Pastoral (London, 1971) (a brief survey).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pastoral theory is J. E. Congleton, Theories of Pastoral Poetry in England 1684—1798 (Gainsville, 1952).
\r\rAmong studie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classical basis of pastoral are G. 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 1949), ch. 9; E. R.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 W. Trask (New York, 1953), ch. 10; W. Leonard Grant, Neo-Latin Literature and the Pastoral (Chapel Hill, 1965); T. G. Rosenmeyer, The Green Cabinet: Theocritus and the Eropean Pastoral Lyr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9), which has a good deal to say about Virgil also. Editions of later poets which pay attention to classical sources include The Ecolgues of Baptista Mantuanus, ed. W. P. Mustard (Baltimore, 1911), and the Longmans Annotated Texts of Milton’s Complete Shorter Poems, ed. J. Carey (London, 1971;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art of a complete edition of Milton in one volume, ed. J. Carey and A. Fowler, 1968), and of Matthew Arnold (ed. K. Allott, 1965).
\r\rW. W. Greg, Pastoral Poetry and Pastoral Drama: A Literary Inqui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e-Restoration Stage in England (London, 1906), remains a stylish survey. For medieval pastoral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Renaissance, see H. Cooper, Pastoral: Medieval into Renaissance (Ipswich, 1977). Pastoral eleg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after is the theme of E. Z. Lambert, Placing Sorrow: A Study of the Pastoral Elegy Convention from Theocritus to Milton (Chapel Hill, 1976); see also J. H. Hanford, ‘The Pastoral Elegy and Milton’s Lycidas’, Proceedings of the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5 (1910), 403—447. For the Golden Age see A. B. Giamatti, The Earthly Paradise and the Renaissance Epic (Princeton, 1966) and H. Levin, The Myth of the Golden Age in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70).
\r\r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Pastoral Verse, ed. J. Barrell and J. Bull (Harmondsworth, 1974), contains a number of poems that are not pastoral at all, but makes a pleasing anthology.
\r \r\r(1) 燕卜荪(1906—1984),英国墨客与评论家,对20世纪的文学评论影响甚巨,1937年至第二次天下大战爆发,1947—1952年两度在北京大学任教。
\r\r(2)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1844—1889),英国墨客,其作品1918年后才被搜集出版,但影响过20世纪的许多墨客。
\r\r(3) 帕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曾与海洋女神特提斯成婚,生子阿克琉斯,即远征特洛伊的希腊军队中最著名的英雄。
\r\r(4) 像后面提到的麦里波乌斯一样,科律登是维吉尔《牧歌》中涌现的人物。
\r\r(5) 棕榈叶象征胜利,这里显然是说巴克莱对曼图安的评价更高。
\r\r(6) 伊丽齐乌姆(Elizium)是把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的字头和英国拉丁文写法的字尾结合起来组成的。该词和拉丁文的瑶池、福地(Elysium)读音一样。墨客奥妙地利用了两个词之间的谐音。
\r\r(7) 对这首诗的翻译,基本采取杨宪益的译文,仅根据不同情形作了一些小的变动,见《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杨宪益卷·奥德修纪》,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r\r(8) 布肯内特来自bumkin(乡下佬、粗人),格鲁比诺尔来自grubber(做苦力的人),布鲁兹林达可能来自blouse(女式宽松罩衫),三个名字都与屯子有关。
\r\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