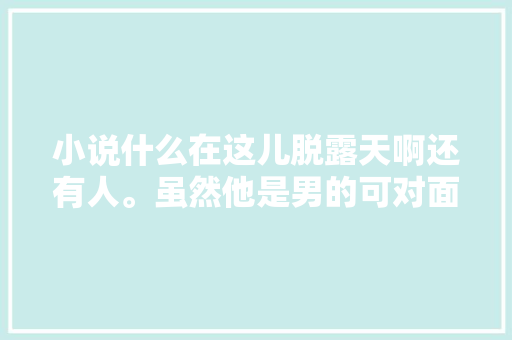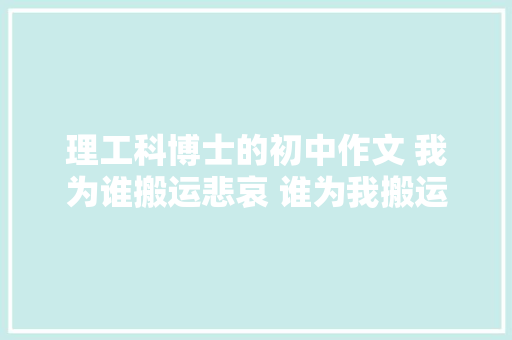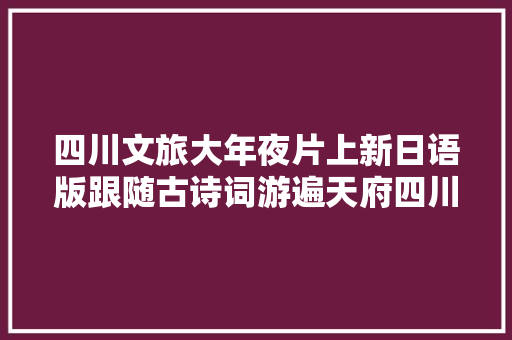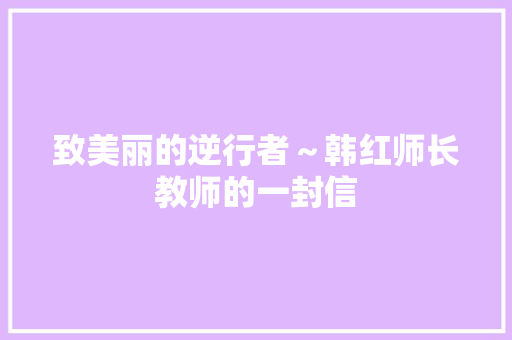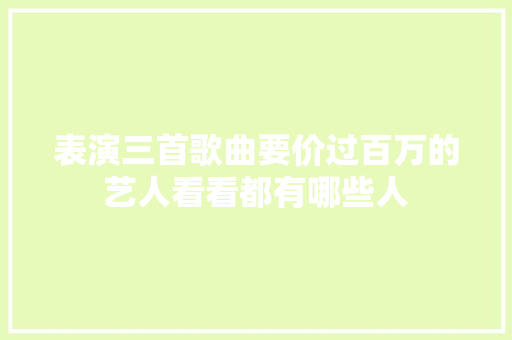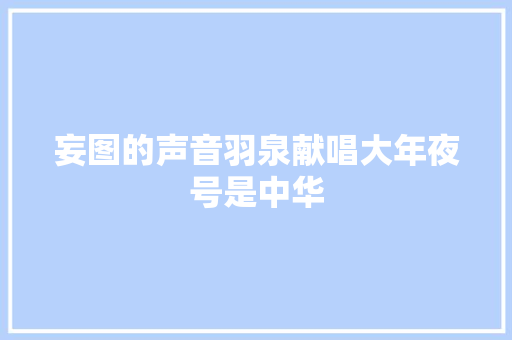编者按:随着罗诉韦德案被最高法院推翻,这一决定可能立即导致堕胎行为在美国22个州被剖断为造孽,估量将有数以百万计女性失落去接管堕胎做事的路子。本文收录了5位作者在阿利托大法官见地草案透露后,对付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评论。作者们从女性失落去生殖自由和堕胎自主权;大法官如何推动了这一进程与最高法院的政治化;爱尔兰女性失落去堕胎权惨痛历史背后的启迪;共和党如何压制少数族裔女性选民的投票权,进一步掩护和巩固其做出的政治决定;共和党如何与福音派组成同盟,利用了女性的身体换取政治权力这五个方面核阅了罗诉韦德案的闭幕带来的影响。这一决定带来的痛楚将对女性造成真实的侵害,而更令人绝望的是,推翻罗诉韦德案很可能并不是守旧派的终极目标。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中译略有删减。
当地韶光2022年5月1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当地举行守卫保护女性堕胎权法案的游行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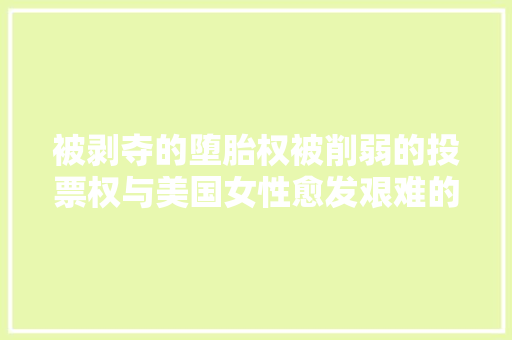
抽吸手术(aspiration)
作者:克里斯汀·亨内博格(Christine Henneberg),一位从事妇女康健和操持生养事情的作家和年夜夫。
我事情的诊所没有窗户,走廊上有一排方形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桌子、一个电脑屏幕、一盒纸巾、两把椅子,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这里是诊所顾问会见前来堕胎的病人的地方。
这些小房间里的大部分事情都不须要我的参与。咨询师们有一套须要讯问每个病人的问题,但对话每每不会按剧本进行。一个女人开始评论辩论她的生活:与伴侣的争吵,小儿子的哮喘,姐姐下周的婚礼,母亲的酗酒。只要她以为这些事情与手术有关,那这统统就都是有关的。咨询师以专注的沉默,同情的目光,偶尔的“嗯,啊,我明白了”给出肯定回应。终极,她们会商到最主要的详细问题——病人是否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并准备好接管本日的手术?
终极,大多数病人会穿过大厅,来到一个更大的手术室,那里有更临床的氛围。手术室配备有检讨台、脚蹬、电动抽吸装置、无菌手术设备和一台超声波机。我每天大部分韶光都待在这些房间里,进行抽吸手术。
抽吸术是一种高效且相对温和的清空子宫的办法。手术设备包括一个医用小管。年夜夫利用手动或电动抽吸,通过手和手腕循环运动来完成手术。本日,险些每个年夜夫都采纳这种方法进行早期流产;该方法也被用于处理永劫光或繁芜流产的情形。
每天有一两个病人会感到迟疑,这就像诊所中小插曲。在她进行手术之前,我会被叫到一个咨询室,查看她的病例并与她交谈。
和多数病人一样,她来诊所是为了堕胎,或至少是为了知道她是否符合堕胎的条件而来。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大概她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她可能是由于一些症状而来:她在流血,可能会流产;她想知道我能见告她什么,她有什么选择。也可能是护士在做超声波检讨时创造子宫里没有有身迹象,这就增加了宫外孕的可能。
在谈论了详细情形后,假设她们没有涌现紧急情形(无法掌握的出血或宫外孕的症状),我会见告她,我们如何进行手术将取决于她的目标和想法。她是确定要终止受孕,还是须要更多韶光来考虑?如果她已经流产了,她是希望让身体自行排出组织,还是想要用药物或抽吸手术来加速这一过程?她是否操持与伴侣或爱人谈论这统统,还是打算独自决定?
许多女性常常对我们花这么多韶光谈论这些个人的、非临床的成分感到惊异。在她问我:“你有什么建议”的时候,我会见告她:“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真正的医学建议依据。我提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安全合理的。这是个人的决定。这完备取决于你自己。”
我看到她的眼神,像是在说:你在开玩笑吧,由我决定?有时那是一种恐怖的眼神,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它终极将不可避免地转化成其他的东西,一种探究的瞩目。她在我面前,进入了内心非常私密的地方。我无法进入个中一探究竟,但我给予了她鼓励,让她谛听自己的声音——让她暂时阔别年夜夫、阔别朋友和家人的判断和偏见、阔别停车场里抗议者的喊叫声。这是我在事情中最喜好的部分之一:看着她走进内心深处,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一个完备属于她的决定。
她是来堕胎的,而她得到的,或者说她首先得到的,是对“堕胎自主权”的理解,以及她对自己未来的设想。随着罗诉韦德案的推翻,这些权利将不复存在。那些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的私人发言与抽吸手术都将消逝不见。
当地韶光2022年6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名事情职员在听到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后感到不可置信, 阿拉莫妇女生殖做事中央关闭了堕胎做事。
无所顾忌的多数派
作者:大卫·科尔(David Cole),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的国家法律主任;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央,乔治·米切尔(George J. Mitchell)法律与公共政策教授。
传统的不雅观点认为,人们不能通过最高法院法官在最初几年的表现来评判他或她,由于他们尚未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恐怖的权力和任务。新上任的大法官常日须要一段韶光来适应自己的位置,并在适应过程中谨慎行事。
然而,对付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来说,情形并非如此,他们已经在最高法院分别事情了一年、三年和五年。如果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大法官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康健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透露的见地草案成立,那么这三位大法官将共同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正是这一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决定,保护了妇女掌握自己身体和命运的基本权利。
新任的大法官有许多情由去暂缓支持这一激进的决定。五十年来,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都申请并重申了罗诉韦德案。30年前,最高法院谢绝了推翻该案件讯断的明确哀求,强调遵守先例的特殊主要性,以及得到堕胎机会对妇女平等地位的核心意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承诺任命能够推翻罗诉韦德案件讯断的法官的做法也值得反思。这种试金石式的测试将最高法院变得政治化,而法院的合法性则取决于它能否超越特朗普所青睐的,赤裸裸的政治手段。
这些只是法理上的问题。人们还认为,法官该当慎重考虑这个“将给海内一半的公民带来灾害性后果”的决定,由于女性将失落去个人可以做出的最主要决定之一,即是否要孩子的权利(事实上,男性同样会由于能够和伴侣操持是否以及何时生孩子而受益)。虽然所有女性都将失落去宪法授予的权利,但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没有经济来源的年轻女性,家庭状况困难的女性,以及有色人种女性将立即感想熏染到这种侵害。
阿利托大法官的草案坚持认为,推翻宪法先例没有什么错,由于最高法院一些最著名的见地都是这样做的。布朗诉教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推翻了58年前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宣告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阿利托统共引用了约30项法院推翻先例的裁决。但最引人瞩目的是,绝大多数的决定都扩大了权利。少数裁决淡化了对权利的保护,但没有任何一项裁决完备取消了一项权利。终极,阿利托的冗长清单只能证明如果最高法院肃清一个长期公认的权利,将会是多么“亘古未有”。
此外,阿利托推剃头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堕胎。他坚持认为,只有当这些权利“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时,法院才该当保护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但事实上,我们本日享有的“险些所有宪法权利”都超出了“历史和传统”所承认的范围。事实上,制宪者利用了诸如“自由”、“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这样的开放式术语来许可乃至鼓励这种演化。
如果我们把权利缩减到1791年通过《权利法案》时人们享有的权利,乃至缩减到19世纪末增加《内战改动案》时人们享有的权利,许多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平等保护条款》在1868年被批准时并没有禁止性别歧视或种族隔离。受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也不包括“利用避孕方法”或“不受性别或种族的限定,自由选择性伴侣或配偶”的权利。
阿利托说,堕胎不同于其他的“自由”,由于它“摧毁了……‘潜在的生命’”。但这种差异与他的推理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他宣告的规则是,宪法中没有特殊提到的权利,只有在根植于历史和传统的情形下才会得到承认,而不是只有“阻碍潜在生命的权利”才会受到限定。
末了,阿利托轻率地评估了裁决对女性产生的影响。他否认了废除堕胎法将违反平等保护的说法,指出并非所有女性都有身了。但根据这一理论,一部规定不适用于患有镰状细胞血虚症(该病多发生在黑人群体中)病人的法律也不会构成种族歧视。他还表示,我们无法知道女性是否依赖罗诉韦德案件中宣告的权利来方案她们的生活、家庭和奇迹,而这一事实显然是不可否认的。
该决定不是终极决定。但如果法院坚持这一结果,这将是真正激进的多数派所为,无异于粗暴地行使权力,从一半的民众手中夺走她们最主要的权利之一。
爱尔兰的痛楚经历
作者:安·恩莱特(Anne Enright),都柏林大学创意写作教授。
2018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当爱尔兰的堕胎禁令终极被废除时,爱尔兰女性在都柏林城堡的园地上舞蹈、唱歌、欢呼。我不在那里,我没有舞蹈,我呆在家里,对着我的电脑键盘堕泪,考虑着我的孩子们的未来。争取身体自主权的斗争韶光太长,带来的侵害太大,而我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足。
1983年,爱尔兰全民公投通过了《爱尔兰宪法第八改动案》,该改动案承认“承认未出生的胎儿生命同样拥有权利。在适当考虑有身母亲平等生命权利并在可行的状况下,法律将担保和守卫这些权利”。终极,所有须要堕胎的爱尔兰妇女,无论出于什么缘故原由,包括医疗缘故原由,都必须前往英格兰接管手术。
许多年后,我才对“母亲”一词是否该当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提出质疑。“母亲”不便是一种关系吗?那么“有身的人”呢?大概我们可以从利用这个词开始,而非选择“母亲”,这个在英语中最具约束力的词。
在1983年投票之后的许多辩论中,人们评论辩论强奸的受害者,乱伦强奸的受害者,法定强奸的受害者;关于有学习困难的妇女、晕厥中的妇女、患有可治疗癌症的妇女、怀有致命畸形胎儿的妇女、流产时伴有去世亡危险的妇女。这些妇女都被爱尔兰宪法和天主教会称为“母亲”,而她们的痛楚处境不是重点。“生命权”条款与社会环境无关,它与关于医疗的实际情形无关。它乃至与个人的赞许无关,由于生理学是无关紧要的。有身是对自我的一种抹杀。通过有身,一个人竟能同时被视为“奇迹”和“毫无权利的肉体”。
然而,辩论是必要的,也仍在连续:生命权是一种理念,但人体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1992年,爱尔兰举行了又一次公投,以澄清“母亲的平等生命权利”。当时,一个被强奸后有身的14岁女孩在国家的照顾下产生了自尽方向,一项将她带到英国进行堕胎的操持被提交到爱尔兰最高法院。爱尔兰最高法院许可她进行旅行,但在讯断后不久,她流产了。然而这个案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爱尔兰公民终极直面了这些问题。“自我毁灭的风险”能否被算作许可堕胎的情由?爱尔兰公民看到了该问题的残酷性,65%的人投票表示可以。
你能想象在一张纸选票上留下你的标记,哀求你梳理出被强奸的孩子难以结束自己生命背后存在的问题,那是什么觉得吗?我感到非常恶心,我的手在抖动。我感到被完备打败了,虽然我投了票,但我没有去游行、辩论、发言或抗议。在1992年,我无法从这场辩论中找到出路,部分缘故原由是这个由另一方制订的辩论是没有出路的。
为什么要辩论呢?中产阶级妇女都会选择通过旅行来得到堕胎做事。2001年,事后避孕药涌现了,只管女性不得不付钱给年夜夫,并让经历尴尬才能买到它。只管如此,女性仍旧默默地承受着痛楚,乃至无人知晓她们的姓名。一些女性去世去了,法院审理了一些棘手的案件,但她们的姓名被A、C、X所取代,并附上干系的法律证词。
2012年,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Savita Halappanavar)去世在戈尔韦(Galway)的一家医院里,当时她因流产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护士,由于院方关心的只有注定无法存活的胎儿。她的丈夫普拉文(Praveen)问:“他们为什么不把目光投向成人的生命?”这个问题是如此正常,如此不证自明,以至于使得“未出生者”的平等权利看起来像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抽象观点。对付在印度终年夜的普拉文而言,他难以理解的事实是——天主教的爱尔兰对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认识”,他的妻子为此捐躯了。
爱尔兰的堕胎禁令在医学上和实践上都是失落败的。这一禁令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但是,导致该法案被废除的公众舆论转变并非来自于法律、道德或宗教辩论;转变的发生是由于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的名字为人所知,她的照片涌如今新闻以及标语牌上——愿她安息。之后,活着的妇女把她们的名字写进了关于堕胎的故事里,一个强有力的禁忌被冲破了。2018年,超过四分之三的爱尔兰选民表示,媒体或熟人讲述的关于堕胎的个人故事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然而,当爱尔兰公民终极投票附和许可堕胎时,我的感想熏染并不大略,这统统都太有毒了。我须要对那些困难的岁月表示哀悼。我18岁的女儿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对她来说,这些问题再清晰不过了。她很愉快,由于她可以投票,而且她的第一次投票就投给了胜利的一方。
当地韶光2022年6月25日,美国华盛顿,堕胎权利活动家在最高法院外抗议。美国最高法院许可各州监管堕胎的裁决,在全美引发了一场猖獗的旅行热潮,人们纷纭将患者勾引到仍许可堕胎的州。
窃取皇冠上的明珠
作者:雪莉琳·伊菲尔(Sherrilyn Ifill),民权状师和学者。
对美国妇女而言,罗诉韦德案和操持生养协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的闭幕是灾害性的。然而,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康健组织一案中,阿利托法官在其见地草案的结尾处,对裁决的潜在影响做出了看似乐不雅观,实则冷漠无情的预测。他没有直接论述法院的裁决将造成的痛楚,而是将其作为对各州女性选民的“仁慈”恩赐。他表示这将“把堕胎问题交还给立法机构”,并许可“对付堕胎问题持不同态度的妇女去影响立法进程”。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提醒我们,“女性并非没有选举权或政治权力。”
两党中的许多人会方向于赞许这一宣言,而且确实有一些州的妇女能够调集她们的选举力量来保护堕胎权利。但在许多州,尤其是在南方,情形并非如此:那里仍旧居住着大量黑人女性。因此,在阅读该见地草案时,我们必须考虑最高法院具有毁坏性的投票权判例及其对黑人女性选举权带来的影响。
最高法院在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的裁决取消了《投票权法案》中第4条规定的关键保护方法,并推翻了该法案第5条规定的预先批准公式,该公式规定有投票歧视历史的法律统领区必须在颁布之前,将拟议的选举变革提交联邦当局批准。这一条款使《投票权法案》成为民权立法的皇冠上的明珠,由于它建立了一个制度,阻挡了歧视性行为成为法律的可能。在谢尔比案中,法院驳回了预先批准公式的利用,此举可能是试图通过强调黑人选民在歧视性选举法颁布后仍可自由寻衅这些法律,他们可以根据《投票权法案》的第2条规定,对削弱或剥夺少数族裔投票权的选举法和歧视性做法提出申说,从而将危害降至最低。
从那时起,黑人妇女不得不战胜一系列不断加速且日益繁芜的选民压制操持,这些操持以惊人的速率激增。纵然在多布斯草案流传的同时,由于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通过了压制选民的法律,黑人和拉丁裔妇女的投票能力(以及她们的选票能否被打算在内)都面临威胁。这些法律在诉讼中受到了民权组织的寻衅,但是这些问题在今年的国会和州中期选举之前不太可能得到完备办理。
黑人女性选民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在2020年总统选举和2021年乔治亚州特殊选举中,她们在民主党的选民中达成了创记录的投票率。在2020年总统初选期间,黑人选民在佐治亚州富尔顿县排了9个小时的队投票,当时正值大盛行情形最严重的期间。这些选民的爱国主义行为和决心得到了佐治亚州共和党的“重点褒奖”,共和党制订了一套新的选民压制法,个中一个条款规定,“向排队的选民供应水或茶点”将被定为犯罪。
人们可以根据《投票权法案》第2条对这条法律和新颁布的压制选民法律中的其他内容提起诉讼。但是,这些诉讼将不会采取过去40多年来,“根据第2条提出的申说的审查标准”进行评估。由于在2021年夏天,在布尔诺维奇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Brnovich v.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一案中,阿利托大法官亲自宣告了一个新的、限定性更强的测试,以评估根据第2条提出的申说,它忽略了国会明确提出的、下级法院几十年来利用的有效标准。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反对见地中写道,阿利托的多数见地切实其实是“无法地带”。但后者彷佛并不在意。就在一个月前,法院许可一个公然的种族主义选区(Gerrymander,美国的政治术语,指以不公正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参加今年的中期选举,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联邦审判法院在一份长达 234 页的决定中挖空心思地详细阐明了这一选区的种族主义特色。法院宣告了关于“影子裁决”(shadow docket)的决定,指不经由完全审理程序,短缺最高法院充分见地以及当事各方充分通报或口头辩论的情形下,针对紧迫事宜迅速做出的讯断。
这些决定都使得黑人女性更难以行使选举权,而按照阿利托的说法,选举权是女性得到堕胎权的手段。但是,当阿利托声称将堕胎的未来节制在女性选民手中时,他却否认了法院助长的对黑人和拉丁裔妇女的政治剥夺。那么,他口中节制选举权的女性究竟指谁?该见地草案的成立,意味着法院将限定黑人妇女的基本隐私权,同时将拆除我们保护自己政治权力的工具。
在堕落之前
作者:苏·哈尔珀恩(Sue Halpern),《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纽约评论》定期撰稿人。美国明德学院常驻学者。
在塞缪尔·阿利托那份“倒退式”的最高法院草案见地遭到透露的前一天,我恰巧在飞机上看《塔米·费伊的眼睛》(The Eyes of Tammy Faye),这部2021年的电影虚构了美国最主要的福音派基督教夫妇之一塔米·费伊和吉姆·巴克(Jim Bakker)的起起落落。
在一个1985年的场景中,杰里·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一位年长的、更成熟的、政治上更精明的电视布道者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的米尔堡,吉姆·巴克正在那里建造一个基督教主题公园。当他们坐着吉普车一起颠簸时,法尔维尔对巴克说:“布什副总统指望我们在1988年像过去帮助里根那样帮助他。没有我们,共和党就赢不了。你须要明白,在这场为我们国家的灵魂而战的战斗中,我们是多么强大。”
在影片中,法尔维尔口中的“为国家灵魂而战”指的是反对同性恋和艾滋病。他坚称“这种‘同性恋癌症’正在影响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庭”。事实上,这场斗争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法尔维尔被说服利用堕胎来为共和党运送白人福音派教徒。
当时,福音派基本上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也不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来投票。宗传授教化者兰德尔·巴尔默(Randall ballmer)指出,纵然到了1976年,也便是罗诉韦德案通过的三年后,南方浸信会也重申了1971岁首年月次通过的一项决议,敦促其成员争取立法,许可在涌现强奸、乱伦、有明显的胎儿畸形证据、在确认有可能危害母亲的情绪、精神和身体康健的证据等情形下堕胎。
但共和党计策家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明白,只要牢牢攥住福音派,就可以把总统宝座交给罗纳德·里根,并巩固共和党的未来。
到20世纪70年代末,正如我所记录的那样:法尔维尔担心民主党人会取消白人专属学院的免税地位,个中包括他自己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学院。这些白人专属学院是20世纪60和70年代为相应联邦政府逼迫废除种族隔离而在南方建立的福音派学院。正如巴尔默以是为的那样:韦里奇知道,共和党人须要呼吁一些比种族主义更随意马虎被社会接管的东西。环绕“杀去世婴儿”的辩论,成为了吸引选民和延续种族歧视的狡猾伎俩。
在共和党与福音派组成同盟之前,共和党人总体上并不反对堕胎。1967年,作为州长,里根签署了《加州治疗性堕胎法》,这是当时美国最自由的堕胎法之一。五年后,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创造,近70%的共和党人表示,只有女性和她的年夜夫,而不是政府,才该当参与终止受孕的决定。但是,在韦里奇与福音派建立联系后,共和党选民,连同里根和乔治·H·W·布什等著名的共和党政治家,成为了公开的反堕胎支持者。他们利用了女性的身体换取政治权力。
此时此刻,间隔最高法院通过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女性的隐私权和身体完全权近半个世纪之后,涌现了本末倒置般的转变——福音派已经将共和党纳入个中,后者鞭策着愤怒,在许多州通过法律,使选民(尤其是有色人种选民)更难以投票。这一做法使右翼的少数人比多数人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最高法院堆满了为追求基督教议程而被任命的大法官。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平常,许多人没故意识到的是,罗诉韦德案的推翻很可能并非这场游戏的终点。
任务编辑:沈关哲
校正: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