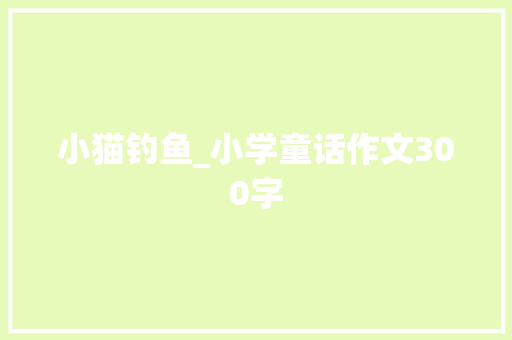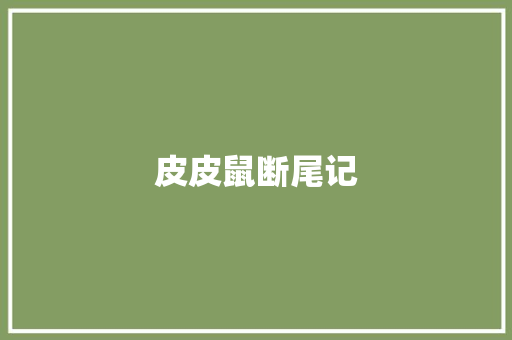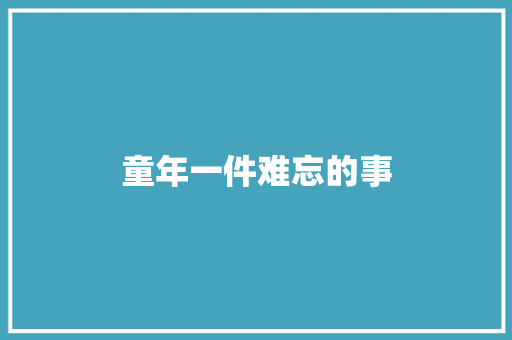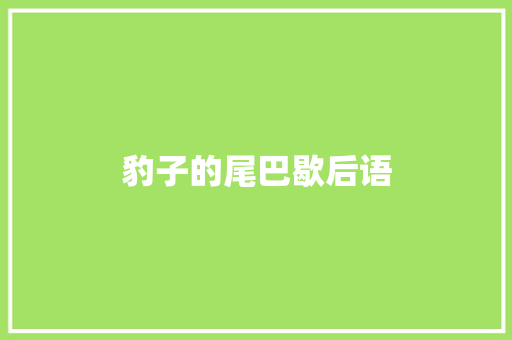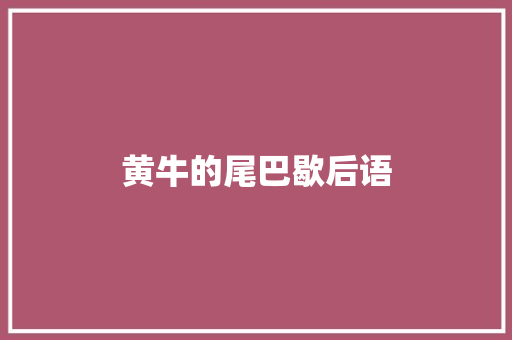前段韶光,喜好上了看画,西方的、中国的;古典的、当代的。整体有个觉得,西方长于人物、静物,余下以事或风景入画的那些,画面大多也静穆,仿佛画成的那一刻,韶光是停滞不动、凝固在面前的;而中国画多山水,空间感很强烈,哪怕是画花鸟虫鱼等物,也着重“弦外之响”,尽得留白之风骚。
视觉的饱和使得灵魂饥饿起来,便上网淘了几幅小画。买回家,才创造许是自己真中了鄱阳湖那场盛大花事的蛊,喜好近乎有些偏执了,看看,好几张都有蓼,比如仿花鸟画名作《红蓼水禽图》,仿宋徽宗赵佶的《红蓼白鹅图》及仿齐白石的《红蓼群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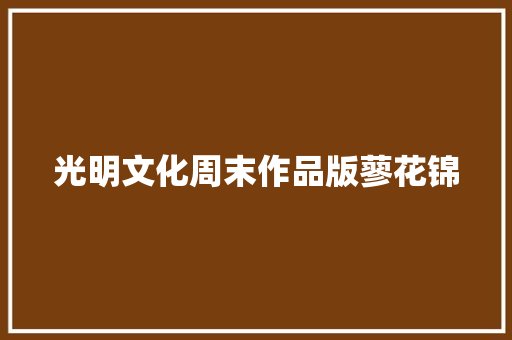
去岁秋日,余干康山大堤附近的鄱阳湖湿地成了“网红”,一场花事在我微信朋友圈口耳相传。像大家一样,我也欣喜赶了这场热闹:青葱的长杆;圆熟的叶子;细碎的花儿,使人触目惊心的原是一坡密密匝匝的红蓼啊。这些蓼花,亦红亦紫,蕊心透丁点儿白,若染了喜庆的米粒。它们挨挨挤挤结成曼长、丰腴的穗状。低垂的紫红花穗,一穗接一穗地,从我身边倾泻而去,以谦善又桀骜的姿态,一起向北,怒放着心中的壮美。仿佛一匹只应天上才有的灿若云霞般的锦绣,又宛如从地心深处长出的一片熠熠生辉的星河。
春来萌芽绽叶,夏秋着花结果的蓼花,又称荭草、水荭,多数临水,生命力兴旺,在我们家乡随处可见,是很野性的花。许是受其花穗形状的影响,我们打小就叫它狗尾巴花。狗尾巴花,狗尾巴花,喊叫起来,是叫喊屯子平凡小孩名字般的随意;狗尾巴花,狗尾巴花,田园里只要长出,大人便会下重手绝不留情地拔除,认为这没啥用的东西太随意马虎纷生侵略地皮,且叶片上还带着涩涩的茸毛、味辣刺激,若煮之作食,猪牛都避得远远的。只管大人的许多“不待见”实在并不能真正影响小孩子对世间万物的欢畅,但那时的我,却也真不以为红蓼有多特殊有多妍美。
孩子的天下是至美的天下。在孩子眼睛里,春夏秋冬,每一天都是色彩斑斓的,每一刻都是活气勃勃的,万物都等着他们去探究、去不雅观摩、去创造、去收受接管,因此他们来不及去钟爱一件事。而认为红蓼不屈常的,从来都只是那些悲秋伤怀的墨客、托物言志的画家和装满离愁别绪的大人。孩子根本觉得不到秋的萧瑟凄凉,体会不了红蓼深处所谓的人情冷暖、世事无常。
紫红一片,杂以青绿,红蓼花海如此强烈的颜色,对所有到来的人显然是一种不可抵御的领导。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红的着绿的,丢开文雅与村落俗的禁锢,尽情开释他们内心的天真之气。他们或雀跃或打滚,仿佛要在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掀起另一种狂澜。我起初也这样雀跃着,愉快着,跳进相框也好,一旁闲望也罢,领受了,心生知足,总是可以叫自己兴趣勃勃好一阵子。
当太阳下山,喧嚷的人群各自离开,湿地又规复它本来的清寂,有如歌残筵散。天地辽远,气温微凉,美的事物总会有某种无端的寂灭,这种悲剧意味使花海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场。个体作为理性生命的骄傲与光彩消遁,作为有限个体的微小、卑微无奈突显,我头枕双臂,仰躺草洲,睁开眼睛看天上的流云,日本宗次郎的曲子《故乡的原风景》开始在心里盘旋。陶笛的空灵携裹如梦似幻的雾气飘飘荡荡,这雍容、朴实,与地皮、河流、星光、候鸟十全十美的花海,使我以为生命中所有关于梦想、活气和道路的谋划都不主要了。原来我只是太爱这鲜活的人生了。
如此看来,红蓼在我心里便是极致的美了。如此看来,我便再不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了。
十分秋色无人管,半属芦花半蓼花。生命里的秋意,浓了。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0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