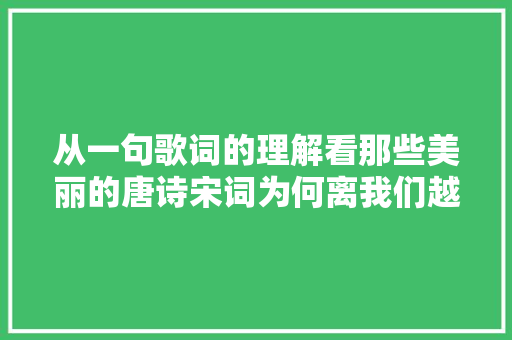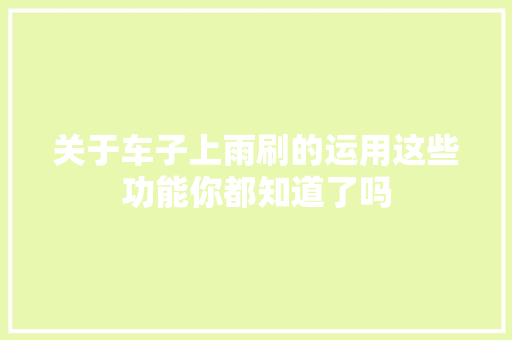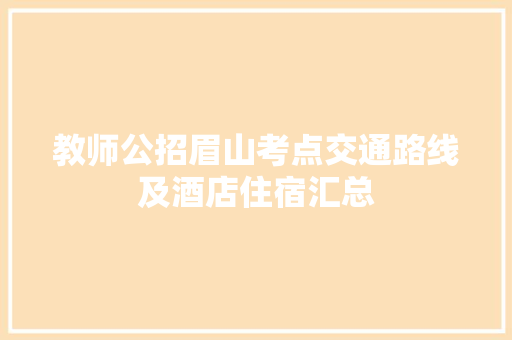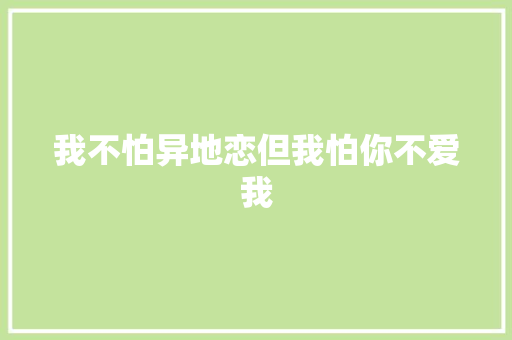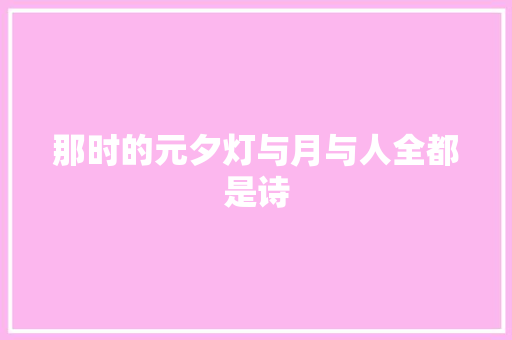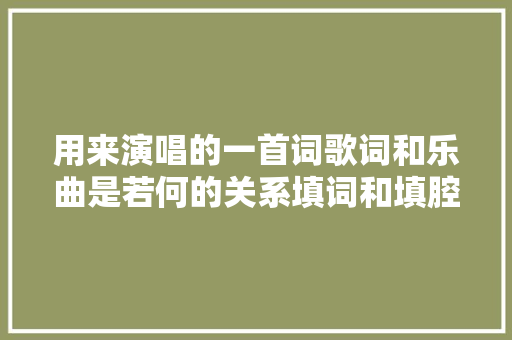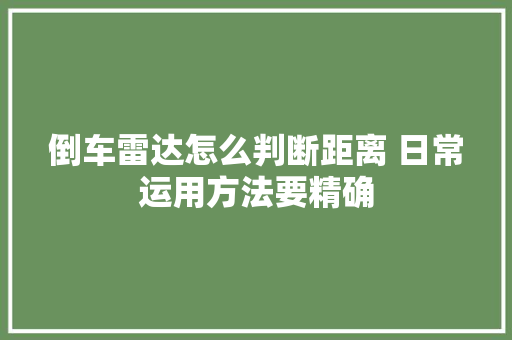南宋词人吴文英写过一首《齐天乐》:
三千年事残鸦外,无言倦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幽云怪雨。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雁起上苍,数行书似旧藏处。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
这首小歌词的第一句看起来貌似有点儿“不象话”:“残鸦外”缀在“三千年事”背面,犹如驴唇缝在了马嘴上,叫人猜不透吴梦窗说的是什么谜语。究竟,这两个意象之间暗藏着若何的逻辑关系呢?
从前写作专栏《晋公子读词》的时候,有好心的朋友为我发踪指示,他说歌词里的“残鸦”定是斜阳的代名词——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太阳中间是站着一只三足乌鸦的。
从远处看,红日在乌鸦的周身镶上了一圈金边,故而太阳又得名“金乌”。斜阳西下,金乌凋残,便是光阴流逝的象征。
对多愁善感的词人来说,这很随意马虎引发他对历史的追思,更何况,此刻他正徘徊于大禹这个九州岛版图的缔造者的葬地。
最初听到“残鸦”即“金乌”的阐明,的确给了我一阵醍醐灌顶的错觉,只是愉快过后,一点迷惑却逐步浮现了出来,详细地说,就聚焦在“三千年事残鸦外”的“外”字上。
据朋友的说法,词人是由残阳起兴,遐想到了三千年前的旧史,而歌词中的“残鸦”又是残阳的代名词。
那么,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勾起三千年沉思的就该当是“残鸦”而不是“残鸦”之外的某个东西,既然如此,吴梦窗又奈何要写“残鸦——外”呢?
提出这个疑问,我并不是要质疑朋友对这一句歌词的起兴逻辑的剖析,相反,我承认他的逻辑梳理是成立的,词人该当便是从斜阳遐想到了古史,只是歌词里的“残鸦”未必可以和斜阳划等号。
柳永有词云: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
——《少年游》
想象一下这幅场景:萧瑟的秋风中,天边的倦鸟正蹁跹投林。而在更远处,一轮残阳正要沉入地平线下,它的余晖也将很快燃尽。
柳永说,斜阳的位置在哪里?正在“鸟外”——也便是比飞鸟更远的地方。
我想,写下《齐天乐》的吴文英,他所看到的场景大概与柳永差强仿佛。所谓“残鸦”乃是实指残阳下的昏鸦,词人是看到了远方的残鸦和残鸦之外的斜阳,才情不自禁勾起怀古之思的。
这个阐明听起来彷佛有点儿“绕”:既然词人选择的兴象是残阳而不是飞鸟,他为什么不径直写残阳,而要说“飞鸟外(的残阳)”呢?只从文法上着眼,我们是无法理解词人的苦心的。
一个精良的作者一定懂得,只有塑造出详细可感的意象,才能授予诗词以鲜活的生命。而当我们说到“光阴流逝”的时候,很遗憾,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描述。
人称“词中老杜”的周邦彦写过一首《西河·金陵怀古》,个中有这样两句:
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涯。
——《西河·金陵怀古》
词人说,当他瞥见长江里远行的白帆缓缓地隐没在天水相接的尽头,就彷佛瞥见曾经的六朝脂粉悄无声息地消逝在金陵的历史之中。
前一个消逝是由空间上的间隔造成的,后一个消逝是由韶光上的间隔造成的。所不同者,空间上的间隔肉眼可见,而韶光上的间隔却只存在于我们的抽象思维之中。
词人正是“用空间换韶光”,才真实可感地写出了金陵的古今之变。
吴文英是周邦彦的衣钵传人,他的那句“三千年事残鸦外”正是对周邦彦的夺胎换骨。
我们试想一下,以词人容身的禹陵为坐标点,他间隔飞鸟之外的夕阳无疑是迢遥的,就彷佛以词人生活确当下为坐标点,他间隔三千年前的禹王间隔迢遥一样。
当词人把韶光上的间隔(三千年事)和空间上的间隔(残鸦外)连缀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微小、生命的短暂和历史的悠远就悉数被他“缝”进了这句歌词里。
— THE END —
笔墨|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