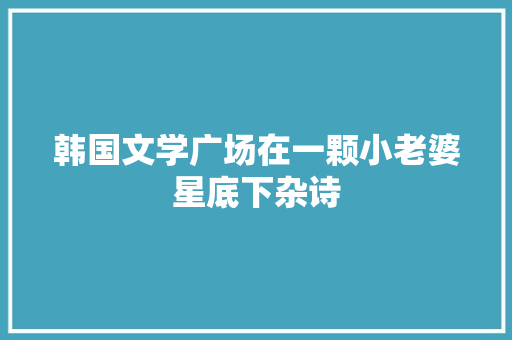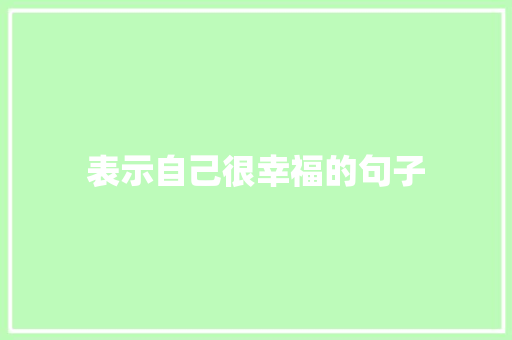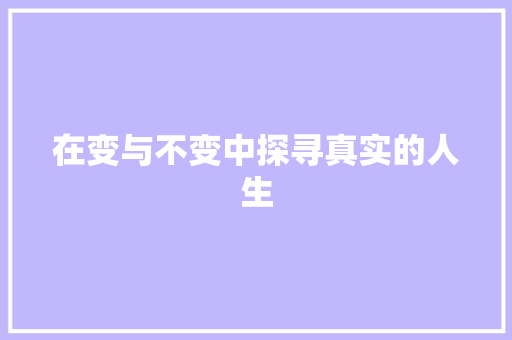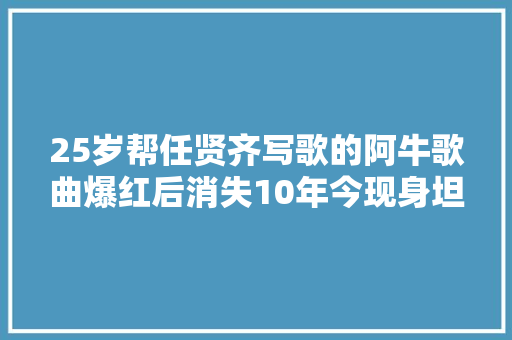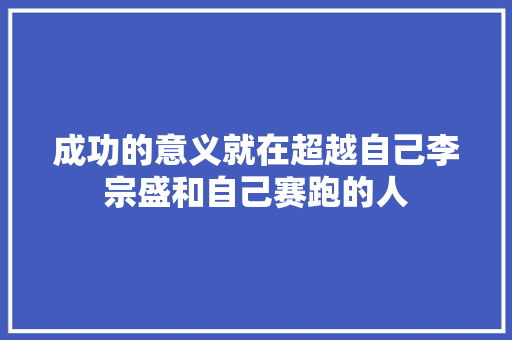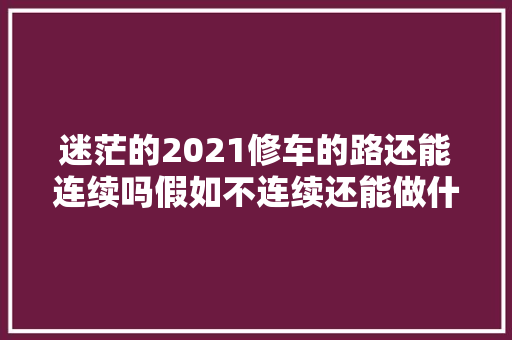/陈璐
2019年,由哔哩哔哩主理的大型线下活动BiliBili Macro Link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央举行

破次元的百万Up主
和ilem初见,是在约定的采访地点楼下。这是条不足摩登却足够烟火气的上海老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后多是些砖赤色的老居民楼。当ilem戴着口罩从远处走来时,我脑海中竟浮现出他创作的《普通Disco》中那句歌词:“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地走在这普通的街/取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觉得/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
比起音乐人这种自带光环的称号,他看起来更像是个爱好音乐的普通理工宅男:穿着一件朴素的玄色外套,背着一个双肩包,脖子上还挂着一副头戴式耳机。大概是长期对着电脑的缘故原由,他身形轻微有些佝偻,话不是很多的样子,看到我后礼貌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呼唤。
ilem原名杨栝,是一位1993年出生的年轻音乐人,由于给VOCALOID的虚拟歌姬“洛天依”创作了许多热门歌曲而深受“95后”“00后”粉丝追捧,在B站上拥有百万粉丝,圈内人称“教主”,被认为是真正可以冲破二次元(动漫游戏)和三次元(现实天下)次元壁的人。
VOCALOID这天本雅马哈公司开拓的一款电子音乐合成软件,用户可以调用软件里的声音演唱不同歌曲,每种声音都对应一位虚拟偶像,个中“初音未来”和“洛天依”是中国有名度最高的两位VOCALOID虚拟歌姬,其他还包括“言和”“乐正绫”等。这些虚拟偶像真正的幕后推手,是浩瀚像ilem一样的创作者。
ilem和洛天依可谓相互造诣。只管初音未来在2007年推出后很快席卷环球,但2012年VOCALOID为中国市场开拓的中文虚拟歌姬洛天依却一贯未能成功破圈,只在小范围内自娱自乐,直到《普通Disco》涌现。
《普通Disco》是VOCALOID目前唯一一首中文神话曲。VOCALOID有一套自己的音乐评价标准:超过10万播放量的殿堂曲,超过100万播放量的传说曲,以及超过1000万播放量的神话曲。在中文VOCALOID现有的78首传说曲中,ilem创作的歌曲数量高达21首。
2015年,李宇春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翻唱这首二次元神曲,令《普通Disco》很快风靡全国。次年,创造洛天依这个IP的湖南卫视约请杨钰莹与其差错,在小年夜大晚会上共同演唱了ilem的另一首传说曲《花儿纳吉》。此后,随着薛之谦、汪峰这样一些有名歌手越来越多地翻唱ilem的歌曲,他逐渐在圈外收成了有名度。
但自己真的火了吗?ilem倒不这么认为。今年3月尾,周深在综艺节目《歌手》上演唱ilem创作的《达拉崩吧》,一人分饰五角,高超的技巧、洗脑的歌词,让这首歌迅速走红网络,播放量很快逼近900万,是一首“准神话曲”。
那天晚上,两人各自的粉丝群都在为这次超过次元的互助彻夜狂欢。ilem却以为这热闹并不属于自己,在家泡了碗方便面、喝了瓶啤酒看完节目后,就“该干吗干吗去了”。毕竟,在ilem看来,“如果你去问一个原来没有打仗过(这首歌)的人,提到歌名,他们第一个会想到周深,如果他乐意穷究一下,会创造原唱是洛天依,然后要再穷究一下,才会看到我”。
“那你会失落落吗?”面对我的疑问,ilem急速摇头否认。“现在已经是遇上好时期了。往前推20年,写歌能被知道的也就那么几个人。纵然现在,大家听过的可能也就张亚东和高晓松。小柯许多人都不认识,但他已经是行业顶尖水平了。音乐制作人这种幕后职业,火到像台前的人一样,不该是对我们的期待。当然做梦是可以的,但把这当目标就不对劲了。”
ilem的谦逊和自省超乎我的预期,那个会在直播间穿女装、舞蹈,在知乎上怼黑粉,显得有点张扬和自傲的ilem,和现实中的杨栝之间彷佛难以建立起联系。他确实拥有可以骄傲的成本。在Z世代中拥有百万粉丝的ilem,早已不再是一个隐蔽在歌手背后的传统音乐人,不论是发布单曲,还是直播间谈天、打游戏,他的一举一动总能得到巨大的流量。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二次元用户规模约为3.32亿人,估量2021年将打破4亿人,市场潜力巨大。而A站、B站仍旧是二次元的两大紧张垂直视频网站,占比超过五成。2016年,一家厂牌看中ilem在B站年轻用户中的潜在代价,与他签约。面对这条逐渐商业化的道路,ilem非常复苏地表示:“做你能做的事情,剩下的交给成本家去想。”
“我在B站上已经是个老人了”
和许多VOCALOID的创作者一样,ilem打仗洛天依纯属有时。2014年时,ilem还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他喜好音乐,学过一点儿电子琴,读高中时心里便产生过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写歌作曲,但这还不敷以构成清晰的未来职业方案。于是,ilem循规蹈矩地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填报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专业。“专业是随便选的,以为自己学工科该当还可以。然后选了离家比较近的学校、分数得当的专业。”
大学期间,ilem开始对未来感到困惑:就业、考研、出国?彷佛都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他想从事有创造性的事情,便开始在网络上写小说、学编曲。《一样》便是在这种心境下出身的:“无眠的夜晚我躺在床上/骗自己说未来路还长/遍体鳞伤/失落去了方向/但请相信/这没紧要/由于我们都一样/总有一天会发光。”
歌写完了,找谁唱呢?一件自己辛劳酝酿的作品,他不肯望随便找个人来演唱,朋友建议,要不试试洛天依?他俩常常在一起玩PSP游戏《初音未来:歌姬操持》。“实在当时是他想学习怎么用洛天依唱歌,我们俩一起学,但他后来放弃了。”ilem回顾说。
谈到创作道路上对自己鼓励最多的人是谁,ilem绝不犹豫地回答,“是B站上的不雅观众”。ilem形容自己是表扬型人格,来自不雅观众的互动是他坚持创作的紧张动力。“他们有时写一些挺长的评论,说从我写的东西中得到一些乐趣、力量,或者想起他自己的事。”
对付一名新人Up主(在B站等视频上投稿的人),最开始这些互动只是零零散星的,却极大地鼓舞了ilem。2015年,当他发布新歌《阴阳师长西席》后,另一位Up主三无Marblue演唱了这首歌。比拟当时只有不到两千粉丝的ilem,拥有几万粉丝的三无Marblue,由于翻唱日文和中文歌曲在B站上小有名气。这为ilem吸引了很多不雅观众。
后续三无Marblue还翻唱了ilem的许多其他歌曲,成功地帮ilem在很多不能接管电子合成音乐的不雅观众中积攒了粉丝缘。比如三无Marblue版本的《深夜墨客》,便曾是许多ilem粉丝的入教单曲。“以是她算是对我帮助最大的Up主之一,尤其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透明。”大概是由于这份感激,ilem提到三无Marblue时都以老师相称。再后来,陆陆续续有许多其他Up主前来寻求互助,令ilem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有名度。
2016年本科毕业后,ilem搬到大连,开始全职投入到音乐创作中。没有去公司就职,整天不知道在家里捣鼓啥,虽然看起来能够养活自己,但起初ilem的母亲仍旧感到很不理解,一度还以为洛天依是ilem的网名。为了能够靠近儿子所做的事情,她时时关注ilem在B站上的动态,有新歌也会分享给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们。
“到目前为止,除了《达拉崩吧》她都以为可以接管,但她会以为没准年轻人就喜好这个。”许多圈外人对洛天依的认知也和ilem父母态度的转变类似。ilem坦诚表示,几年前,许多人还会质疑,这些歌曲能叫音乐吗?对虚拟偶像的电子合成声音接管度比较低。但近几年,VOCALOID从最开始的小众亚文化,已经逐渐进入主流文化圈。
如今,ilem的母亲有时乃至还会在电话中对他的创作提些见地。“比如会说你要写点那种正能量、主流的歌曲。《大氿歌》这种弘扬国风文化的歌曲她就很喜好,会说‘儿子你这个歌词写得不错’,乃至还拿去给我高中语文老师看。”4月26日,腾讯电影官宣《大氿歌》为电影《伏虎武松》的推广曲。
2018年,ilem受邀和张亚东互助完成了一张专辑《2:3》。这首专辑的观点是二次元和三次元的一个比拟。7首歌曲都有两个版本:洛天依演唱的二次元虚拟歌姬版,以及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三无Marblue、戴荃等人演唱的三次元真大家声版。洛天依版本由ilem作曲填词并调校后完成,张亚东则会在ilem创作的原版上重新编曲,制作真人演唱版。
这张专辑的名字是ilem取的。最开始他希望专辑名能叫“二向箔”,这是科幻小说《三体》中涌现的一种前辈武器,能够使三维宇宙向二维宇宙坍塌,和他那句圈内颇为著名的宣言不谋而合——“愿我有生之年,得见VC穿越次元障壁,让这歌声响彻每一个三次元的角落。”不过末了由于版权问题,换成了现在的《2:3》。
2019年1月26日,B站举办首届BILIBILI POWER UP颁奖仪式,ilem成为8位荣获“十周年造诣奖”的百万Up主中唯一一位来自原创音乐区的音乐Up主。这批曾经在“小破站”上自娱自乐的少年,已经成为青年文化的领军人物,而ilem常被视为二次元文化的代表。
当我提醒ilem,间隔他在B站上发布《一样》已经由去6年时,他彷佛也有些不可思议地感慨道:“我在B站上已经是个老人了。”
2017年7月8日,在日本仙台的一名动漫迷手持带有增强现实(AR)运用的智好手机,不雅观看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演出
最想互助的艺人是大张伟
采访快要结束时,大概是轻微熟习了些,ilem溘然对我说,以为最开始的一个问题“你是由于喜好二次元才开始创作的吗”带着对二次元巨大的偏见。我有些诧异,但他却坚持,“不论动画、漫画还是游戏,都只是丁宁韶光的一种办法”。
我以为他彷佛有些敏感,却很快对此感到释然。6年间,随着不断走红,ilem经历过许多非议。由于没有接管过专业演习,再加上他的歌曲每每以“鬼畜”“洗脑”著称,不少评论认为他的“作品完成度不足,艺术层次不高,还不能代表二次元”。这些负面评价曾在很永劫光里困扰过ilem。
2016年,他亲自回答了知乎上的一个帖子,帖子的题目是:“B站的Up主ilem有什么黑点吗?”最开始他只是匿名回答,后来又实名制地交往返回补充了好几次内容,末了一次他写道:“快过去一年了,大家都须要你们,你们在吗?……纵然你对付虚拟歌手的声音并不感冒,在B站也同样可以有自己的平台。我在B站投稿以是我推举这里,当然还有很多更大的舞台,面向每一个怀着梦想的、年夜胆去做的年轻人……如果这一年里你还是什么都没做成,然后还是乐此不疲地黑黑这个喷喷那个,那我祝你玩得愉快。”
“现在我可能不太须要每个人喜好自己了。”ilem如此阐明,“哪首歌末了被人接管了,你的哪一壁被人看到了,这件事不归我掌握。”他谈到比如《2:3》中,虽然传唱度最高的是《勾指赌咒》,但自己最喜好的却是《夜间出租车》。
《夜间出租车》源自ilem的一次午夜经历。那天他到上海出差,晚上睡不着觉,决定出门溜达。骑了辆共享单车,ilem迎着微风四处转悠,白天恰好下过雨,晚上空气难得地清新,市区居然可以看到星星。等他骑到一处高架桥附近的工地时,只见天上点缀着星星,地面水中也倒映着星星,远处的街道上还有车灯闪烁,“特殊神奇”。这段经历,再结合后来坐出租车回家的感想熏染,便有了这首《夜间出租车》。
实际上,ilem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歌曲,都源自这些非常普通的日常。比如《达拉崩吧》,是由于他在哈尔滨时碰着的一块路牌。路牌上标注的街道名字,袭自苏联期间,又长又不通顺。他以为好玩,想把这些绕口的名字串成歌词,便套用《勇者斗恶龙》的故事情节,变成了歌词中那句“达拉崩巴斑得贝迪卜多比鲁翁/他降服了/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西拉松/救出了/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妮谢莉红/回到了/蒙达鲁克硫斯伯古比奇巴勒城”。
而《精力病之歌》,是有次他在学校公共澡堂里,“当时恰好阁下有人在嘎嘎笑,我想,如果有一种人类通用的措辞,能够表达一种共同的感情,估计便是哈哈哈哈哈”。
他在创作中记录生活,变得更加乐于媚谄自己。曾经有粉丝问ilem,能不能写点实验性的音乐。他说:“我自己都不听这个,也不会有希望去写。我喜好听让我以为很愉快的歌曲。要不要打仗那些艺术性特殊高的音乐,虽然客不雅观来讲有时是能力有限,但这也是我主动的选择。”
对付是不是该当提升自己的音乐专业能力,ilem不是没有纠结过。“这些学习到的知识是资源、能力,但也是框架。不好说哪一边会先起浸染,是会先给自己供应更多的能力,还是先给自己制订更多的规则?”
他乃至觉得这种不敷,反倒令自己在创作中找到了“立足之地”。许多专业人士听到他的创作时,常常会表达出惊异之情。ilem举例道:“朋友有次听我的一个Demo,见告我说,你用的拨弦是印度的,拉弦是中国的,鼓组是中东的。也便是说,任何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不会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
大概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建立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以是当我讯问他和张亚东的互助时,并没有听到想象中单方面的溢美之词和崇拜之情。他和我分享两人创作中对付《夜间出租车》的不同理解:“我的是前半夜,9点到12点,但张亚东老师编曲的版本可能是后半夜,2点到5点。两个版本表示出的情境和气氛,差别挺大。我自己的感情比较积极,有点像打个车出去玩或者刚玩回来的状态。他的像是前半夜闹够了,之前就跟人嗨去了,饮酒、唱歌、开Party,再回来时的那个状态。这时可能脑壳有点痛,路上也已经没有什么车,乃至路灯也没有了,更像是激情亲切轻微冷却一点儿之后。当然这是我自己听到的感想熏染。”
“你喜好谁的版本?”我追问。ilem绝不犹豫地回答:“那肯定还是我自己的。”
我又问他最想互助的艺人是谁,ilem说是大张伟。“有机会我想听大老师给我讲课。”至于为什么是大张伟,ilem的回答彷佛更像在表述他自己:“我以为他可能也是那种从舞台高下来后,自己会想很多的人。以是有些事情还挺想跟他请教,但一贯没有找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