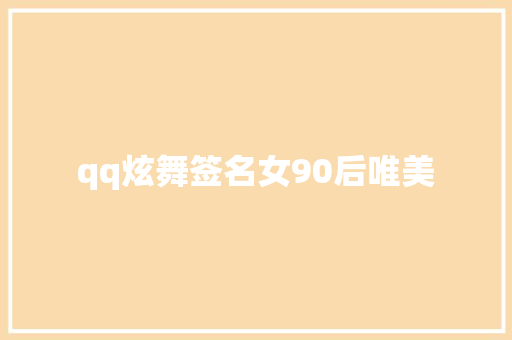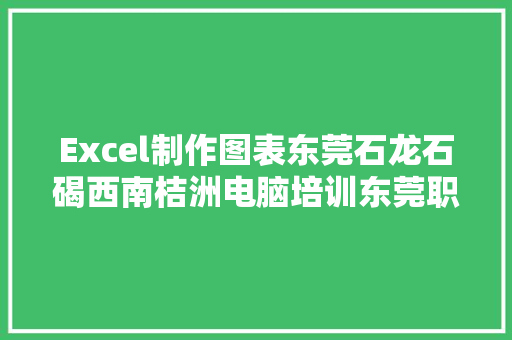狂野的噩梦——Iggy Pop的意义
原文刊于《音乐天国》第28期

文:杨波
在美国正统人士与中产阶级的鄙谚词库里,Sex Pistols意味着粗俗和无用,Iggy Pop则替代了恶心这个词。譬如他们会见告自己的孩子:“这种食品不能吃,它很Iggy Pop。”这个评价对一位业已六旬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而他本人对此不但无所谓反而很满意。“这至少比称我为朋克教父或背叛偶像更恰当”,Iggy耸耸肩说。他30多年来由于总习气于利用夸年夜表情而将面孔折磨得如卫生纸般松软而多皱,由于总乐于用吼叫的办法唱歌而嗓音沙哑。他现在坐在自己豪华的客厅里,穿着一件用美国国旗裁制的坎肩、一条嵌着几个小破洞的白色牛仔裤,垂过肩膀的棕赤色、干枯、乱蓬蓬的头发使他了望去像一只将头伸出海面的、顶着海草的海象。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的坐在这间用烛炬照明的客厅里,在Iggy模糊而倦怠的目光里有些惴惴不安,他试图从这尴尬的沉寂里摆脱出来,将把稳力转向了这间布满了Iggy狂野生活标志的屋子,譬如满墙的裸女油画。
“那个叫‘第一次神交’”,Iggy溘然说,指着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有一个表情惊悸的年轻女子的画:“她正在被一条蛇所攻击,显然,她不喜好它。”他转向另一幅色彩光鲜的裸体女人的肖像画说:“她是Erznlie,海地神话里的爱之女神;她相称于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但她不是处女——她放荡、妒忌、贪心并恶毒,但如果你精确对待她,她会给你爱情。”
这个评论辩论着油画并在那双威慑的蓝色大眼睛上配了一副很小的椭圆形金丝眼镜的男人,显然不是在夸年夜自己的文雅与随年纪增长的名流态度,他更像一位将自己放任自流在噩梦里并借此取乐的自虐型精神分裂者。如果你在街上碰着一个有如此面孔与表情的老人,你一定会对他的过去发生兴趣。他出生并发展在密执安州的一间汽车拖车住宅里,一个极聪明活泼并带有一种附着于底层环境的严重的不互助生理的范例美国儿童;于1964年以前他的名字是James Osterberg,在一个R&B乐队做鼓手时得到了Iggy Pop这个永久的艺名。在一些风格壮实的英式摇滚,如The Who;一些向1950年代回归的朴素而直接的美式摇滚,如The Kingsmen;一些乐于在街头演出的即兴爵士乐,如Cannibal的催化下,从芝加哥领受了Doors精神感化的Iggy回到家乡底特律后与几个对乐器一知半解的辍学生组建了Stooges。这支至少在音乐形式与演出上奠定了朋克乐根本的乐队的意识基调是非常直白的:年少浮滑的姿态与心中充斥的不满;而Stooges的形象定格即是Iggy女性化的浓黑眼影、光滑面孔与男性化、肌肉结实、常常仅穿一条裤子的身体。
“旧金山的迷幻运动放到底特律就成为了一场革命”,Iggy回顾起了1960年代末期他20岁时与MC5的经济人John Sinclair所率领的激进组织“白豹党”打成一片时的日子:“我们摆荡着封面用大号黑体字印着:‘摇滚,吸毒和在街上作乐’的小册子,这在底特律制造了许多行为意义上的地狱,我们大骂市长与总统,并在舞台上嗜血成性……那是Green Day之流永久做不到的。”撤除Stooges用扭曲的吉它与来自原始部落的鼓击交织成的巨大的轰鸣,它更因此Iggy在台上夸年夜、戏剧性的演出被人们记住——那可能是摇滚史上最负自虐性的演出。“这点是我乐于去保持的”,Iggy愉快地说:“在舞台上不存在我做不出的事,我喜好猖獗,那使我的表达变得很随意马虎。”是的,包括用破碎的酒瓶将皮肤划成血淋淋的,赤身倒在碎玻璃上,咬破唇舌后将血抹到脸上与鞭策并参与台下的群殴。Iggy说:“朋克决不但局限于音乐,我证明了这一点。”
贯穿Iggy坎坷而荒诞的生平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海洛因,一条是David Bowie。海洛因使他三次(1971年、1974年和1982年)离开音乐并差些去世去,毒品对身体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好几年里在戒毒所与精神医院间疲于奔命,特殊在1980年代初,滥用药物将他扔到了社会与生命的边缘,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乐意给他一纸合约,“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若何才能离开一克古柯碱或两份双倍的Jake Daniels(一种烈酒)去制作那些恐怖的噪音”,Iggy严明地说:“我为自己所下定义之一是:唯一能杀去世我的事物是正常而清洁的生活——譬如现在,哈哈哈……”他又疯子一样大笑起来。Iggy的康复与重振精神皆来源于一个英国人的帮助,他便是Bowie——Iggy所有最好的专辑险些全部是在他的制作下完成的,包括Stooges末了一张专辑“Raw Power ”(未熟的力量)(该唱片在1997年被Bowie重新混音后出版)、Iggy前两张个人专辑“The Idiot”(白痴 )(这张专辑伴随了Joy Division的Ian Curtis自缢前的末了一个夜晚)、“Lust For Life ”(生之希望)和1982年那张回归的专辑“Blah-Blah-Blah”(废话-废话-废话)—它为Iggy赢得了一个崭新的年轻的听众群。缠绵于“变色龙”称号的Bowie本色上在貌似千变万化的音乐表层里,始终没有摆脱英伦摇滚看重旋律与自察功效的音乐内涵,这点无疑深远地影响了Stooges往后的Iggy:风格的摇摆,许多细碎的细节涌如今不加润色的吉它和弦里,雄性而干瘪的嗓音有时会阐释出一种勉强而不失落说服力的柔和腔调,不再只评论辩论性而适量地加入一些深情但痉挛无望的爱恋,以及被强行压制的激情与爆发希望……Iggy的音乐在意识的不断扭曲下日益悦耳乃至盛行起来。
Iggy从最早Stooges期间的两个和弦、一个效果器加上直白而傻乎乎的Ramones式瞎叫:“她今晚会来吗?你说过我们会有很酷的光阴”——这种15岁荷尔蒙式的生理措辞在1969年的那首脾气狠恶、缺少自傲却简洁有效的“I Wanna Be Your Dog”里发挥到极致——到后期涌现了弦乐和风琴的音乐与寻思熟虑、无所不谈的文本,尤其是对政治弗成一世的参与,如那首1993年的“Wild America”(失落控的美国)。“我总是有话要讲,谁也别想堵住我的嘴”,Iggy说。他同Mick Jagger一样永久保持着牛犊的勇气、激情亲切与斗志;但又同Jagger不一样,他无法亦无意去保持自己原始的一壁,这显得更加老实可信,而不像某些复出的既虚饰又虚伪的摇滚老鬼用年轻时的装扮与和弦来为自己的坟头裱金。譬如Iggy在1990年代出版的三张专辑:“Brick By Brick”(垒砖)、“American Caesar”(美国政治家)和“Naughty Little Doggie”(下流的小狗),险些全部没有激烈暴躁的时候,一种回归的思虑与按捺在倾圯边缘的愤懑掌握了所有的音乐片段。应特殊被提到的是“American Caesar”这张大碟,那是一部冒昧但颇具诗意的英雄叙事诗,是他1970年代以来最抱负非凡、首尾一向的专辑。
1996年, Iggy分别在英美推出了个人精选集并发行了措辞更加越轨但音乐更加悦耳的新专辑“Naughty Little Doggie”。个中的歌曲“Pussy Walk”成为了众矢之的,在这首歌里,Iggy一边指鸡骂犬、明贬暗褒地挖苦猥亵着女性,一边用一种尖利的声音嘲讽着男人(自己),大胆并刁滑的歌词使这支本色上是老调重弹并颇为讨巧的歌曲引发了闻腥而动的传媒的兴趣,只管Iggy个人对歌曲的诠释十分暧昧而简洁:“女人教会了我许多恐怖的东西,法国电影,英美文学和葡萄酒。在我沉浮的生平里很晚才打仗性。在我年轻时,姑娘仅象征着钱和一大堆废话。”评论者们仍旧授予了“Pussy Walk”“深邃”的含义:对女权的的支持、对人性虚伪的讽刺、对精神麻痹的戳穿。专辑主打曲目“I Wanna Live”被人们忽略,但它朴实、准确而详尽地阐述了一个已到了知定命的50岁的老朋克依旧坚忍的不学无术的贱民态度:“我的灵魂就在我的眼睛里,谁都可以看到:我比百事可乐还要好,比MTV还要酷,比加利福尼亚还要热,比一粒豆子还要便宜,比我深居个中的狗穴还要深,我真的不是在谩骂,我想活下去,仅仅多活一下子。”我们很明白Iggy努力用平实的自我戏谑揭示出个人灵魂的纯洁与真实,当然你亦可认为他什么都没说。
Iggy在他的音响里放了一张音乐古怪但绝对不是朋克的CD,并将音量放到很高,他一脸奸笑地望着可怜的眼睛,说:“这是海地的民族音乐,我喜好它的节奏。”然后他闭上双眼,双脚则像蜜蜂的翅膀一样随着鼓点颤动着,他可能陷入了他最初在节奏布鲁斯乐队敲鼓时的回顾。
Iggy说:“必须坚持去戳穿那些真实的东西,不是亮晶晶的阳光或资产阶级式的奢侈无聊,亦不是旧调重弹的个性解放的斗争与绝望,而是活生生的对现实恶行的白描——对性、吸毒、暴力的忽略便是对它们的纵容。”1996年,他在复仇电影“The Crow”里出任了角色,并在许多公益场合频频亮相,而形象是赤身穿着洋装,冷冷地站在那些打着领结的有名人士身旁——这以他在西方文化圈的地位来说是得当的,但以他个人一向的处世态度与性情来说却颇为冒昧。
这便是时期与韶光、个性与共性、理念与麻痹、自虐与自释、摇滚与娱乐的碾转磨和下展现的风景,“偶像传奇=狗屎”,OK,没有什么领袖或小丑,诚挚或虚伪,听说最近老Lydon(Sex Pistols)在电台办了一个朋克精神讲座节目,Black Sabbath又重组了……这里不须要去批驳、辨析或褒扬什么,只假如发生的便是真实的——大多时候,意识形态的术语,如主义、精神、朋克什么的,只是一个个圈套——我们都有自己的逻辑系统。
……
在蹩脚的海地音乐里Iggy忘却了客人,他睡着了。他反复地进出在自己狂野的噩梦里,而那梦的门楣上刻着Iggy的人生箴言:“若将妖怪从我的灵魂里一脚踢走,我的天使亦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