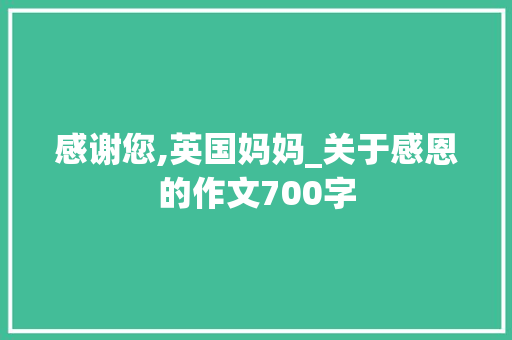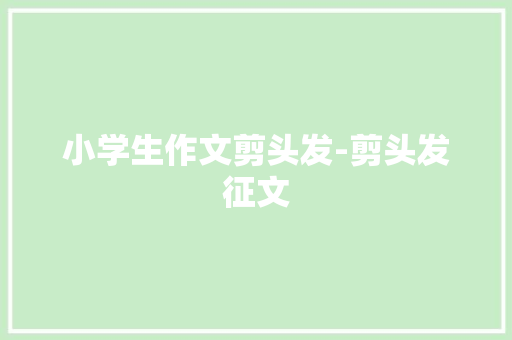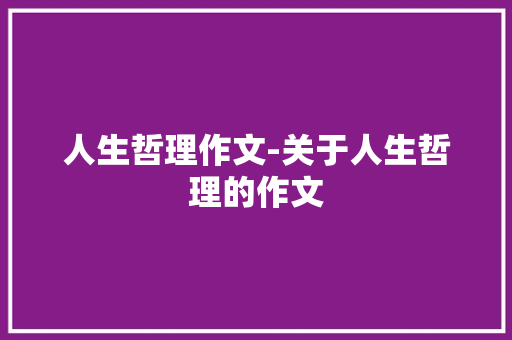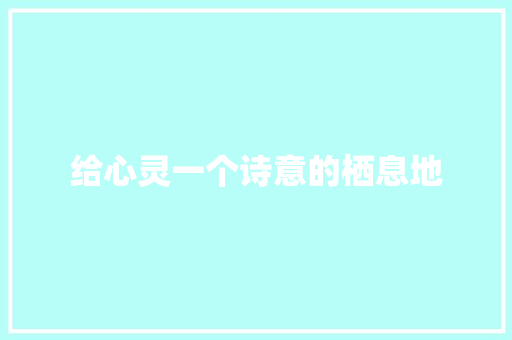淡粉色,白色波点,缝着一圈塑料花边,开车的棕熊随着收伞的动作皱起脸,久而久之棕熊的脸蛋便涌现了缝隙。
不下雨时,我会听妈妈的话,把伞挂在店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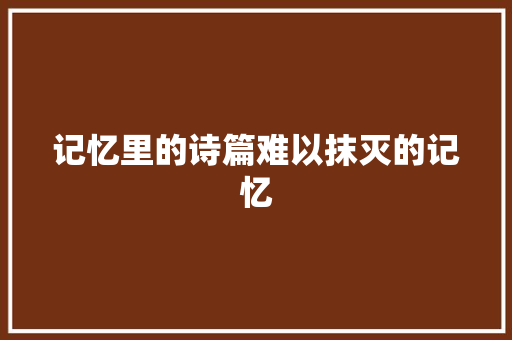
那条街上林立着很多店铺,从左至右依次是五金店,社区诊所,饮水机店,童装店,粉面店,还有刻墓碑的店。妈妈经营着那家童装店。爸爸曾牵着我的手在五金店买插线板,或是螺丝。我在社区诊所打点滴,阁下带着一个男孩的女人递来一个袋子,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枇杷,之后再也不肯吃了。水果里,我爱吃芒果,我总是在童装店和粉面店之间那堵窄窄的墙缝中伸出来的水龙头下洗芒果。
晴天街角摆了很多石碑,阳光晾干上面的红漆字。我们踩在石碑上蹦蹦跳跳,不平的石碑高下晃动。没人会求着孩子知道,那些石碑即将插在坟头上。
街外是一个妇产医院。沿着蜿蜒的小道爬上去,是医院的大门。我们在门前玩滑轮,从坡上滑下来。影象中有个男孩摔了一跤,手骨折了,扎着绑带和支架,却还是气概地站在高处,唾弃所有不肯为滑轮付出到骨折的小孩。倘若不是他妈妈在身后,他铁定要穿着轮滑鞋来了。
坡道一边是花坛,花坛边上贴着滑滑的瓷砖。没有游乐举动步伐,小孩子们姑且把那当做滑滑梯,实在是滑不动的。
入夜了,顺道去医院洗手。妈妈托着我,我才够得到洗手台。洗手台与表面的不同,拧开水龙头,水向上喷出,散开的水花宛如海豚的尾鳍。那天妈妈洗了良久的手,然后开始洗脸,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洗手液喷鼻香,我站在洗手台下,面前是脏污的水管。
当时我不知道我失落去了一个小妹妹,只不过后来妈妈不会再和我展望妹妹的出生,谈论妹妹要叫什么名字。反正这些事叫一个小孩子忘却也不过是须臾即逝的事情。妈妈说国家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多年往后,不知道妈妈还会不会记得有个小妹妹曾经来过我们家。
有个卖臭豆腐的爷爷和一个卖糖油粑粑的老奶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对老伴,回顾中已经如此认定了。臭豆腐好吃的不是本身,而是加在个中的萝卜丁,是甜的,微辣的,油油的。坐在阁下的石凳上完,又要伸出碗,央求爷爷再舀一勺萝卜丁。
路口还有卖豆腐脑的,雨花亭的豆腐脑要卖一块五的时候,这里仍只要一块钱。我常常站在路口吃着豆腐脑等爸爸回家。
家住顶楼,隔壁住着独身的老爷爷。十年前,他请我吃喷鼻香蕉,一贯历历在目。十年后,又递过来一只弯弯的喷鼻香蕉。我仍旧记得他家阴暗无比,铺着深色木地板,脏脏的。
家是斜斜的屋顶,我总记得我坐在屋顶上,阁下是爸爸。想想又不可能,偏偏又对此笃信不疑。饭桌上,拨动筷子的声音,挑鱼刺的声音,电视里沉闷地播放着新闻,默默撩筷子的声音,那句爸爸,你是不是带我爬过屋顶啊,哽在喉中,欲言又止,总之,无论如何也问不出口了。无论如何,疏离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回到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