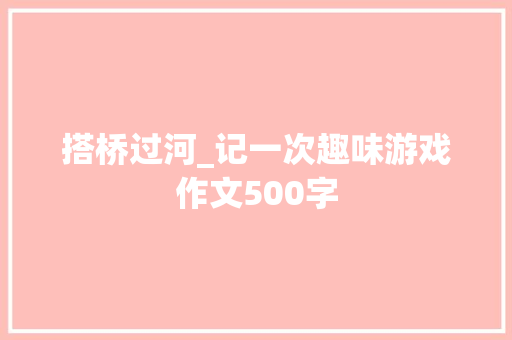“浮生”这个词,出自于庄子。语本《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去世若休。” 以人生涯着,虚浮不定,因称人生为“浮生”。后来,又派生“浮世”一词,人间间是浮沉聚散不定的,故称。
无论“浮生”还是“浮世”,都是我很喜好的词语。人生浮城,四季变幻,雪月风花,灯火勾阑。人间间的统统,就好比漂浮于水面,流水滔滔不绝,日昼夜夜往永恒的大海流去。

漂浮在水面是什么觉得?可以想象自己是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一条小鱼,一只不慎落水又挣扎着跃出水面的小鸟,水没过你的足、小腿、腰、胸,你感想熏染到水流的承托、漂浮。浮躺在缓缓流动的河水里,远处的村落安谧无声,夜空的颜色是一种神奇的湛蓝。水的凉意覆盖着你,月光与星光倾洒在河面之上,你只能在个中载沉载浮,被大河裹挟着奔向不可知的远方。
大概由于我在水边终年夜,水的影象已经刻入灵魂深处。水乡儿女的影象,大都是依河成街,桥街相连;河埠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咫尺往来,皆须舟楫……一次次午夜梦回,我常常在半梦半醒中,又回到童年时期的大水时令:浑浊的大水,蔓延了全体城镇,已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河,绿树像漂浮在水面的浮萍,屋顶像是袒露在河里的褐色石头,人们用低廉甜头的简陋舟筏逐水漂流,与水共生。大水固然带来苦难,但大河在潮汐起伏之间,也送来生存、温饱和财富,这便是河流和村落夫之间奇特的依存。河流阴晴不定,有时怒涛拍岸,有时柔美多情,有时野性难驯,有时灯火可亲。大地倚在河边,水声轻说变幻,在这宽广、年夜方却又喜怒无常的河流上,村落夫寄存的便是全部的生活、整整的生平。
当然,“浮世”、“浮生”并不是就水乡而言的,而是高度概括了普遍的人间间。在茫茫人海里,面前潮起潮落,身后沉浮半生,我们如一个个水面的漂浮物,彼此靠近、离开、滑过、悬游或沉没,各有各内在的精神,外在形态也不一,但相同的是,我们都在这波荡不息的人间间。身处平稳的时期还好一些,但如果碰着的是大起大落的时期,常有震天动地、天翻地覆之事,那么,个人命运就只有在水中无常地沉浮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流动的河水,天边的浮云,时时刻刻处于变革当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某人某事会降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某人某事会消逝。降生于哪一片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每片水,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每个人的生平,浮沉由浪、输赢无算、机缘可遇而不可强求。
日本江户时期盛行的艺术形式“浮世绘”,在亚洲和天下艺术中,呈现出特异的色调与丰姿,历经三百余年,影响深及欧亚各地,十九世纪欧洲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诸流派大师无不受到此种画风的启示。它取材于时期的细节,记录着漂浮的人生。它是大众的、日常的、噜苏的,也是真实的、激情亲切的、繁华的;它描述的山河迤逦、熙攘街市、娱乐人间、异闻传说是年代中的剪影,它记录的爱憎、乐趣、苦恼和欲望是普通人与时期的碰撞。“浮世绘”,这个名词让我感想熏染到一种虚浮的轻盈感。正如浅井了意在《浮世物语》中写道:“让我们把全部把稳力转向美好的玉轮、雪景、樱花和枫叶,唱歌,饮酒……这便是我们所谓的浮世”。日本人的美,属于“樱花式”,即开即落、及时行乐,以是发展出镜花水月、浮生若梦的浮世绘美学,面对浮动的天下,只愿珍惜光阴,知足常乐,一期一会,活在当下。
以浮云的眼力来看,无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风里。以游鱼的眼力来看,无论漂在哪里,都是漂在水里。以永恒的眼力来看,短暂的、寄居的人生,统统都是浮红涨绿,浮花浪蕊,无论是在哪里,都是暂时栖息而已。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我们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都在蓝色地球上面度过他们的生平。而地球也只是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小小地球是比这些还要微小太多的存在。
想起张爱玲在战役的烬余中,曾经幽幽地说过:“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也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的夜阑书写中,用笔墨来定格这浮萍般无定的人间,赢得一瞬间的抚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