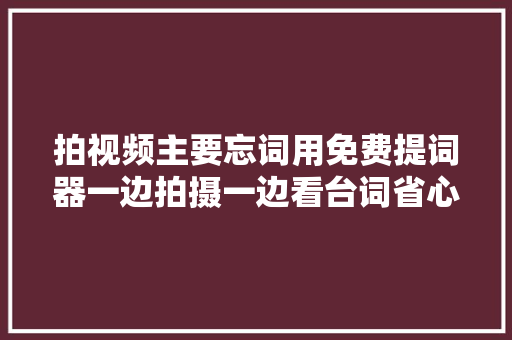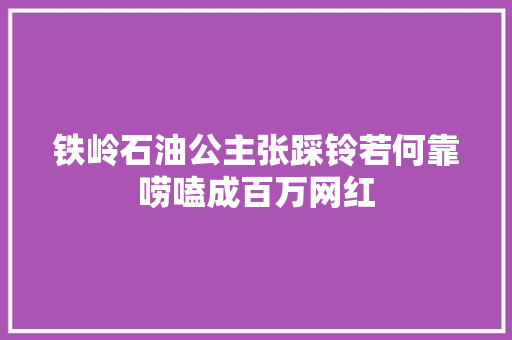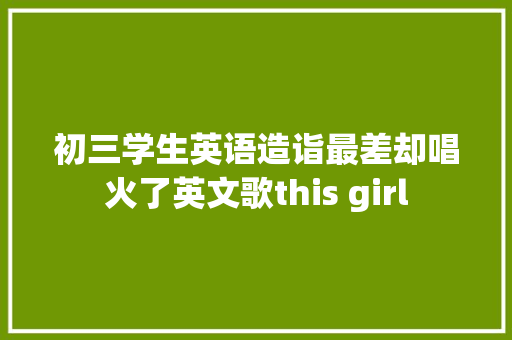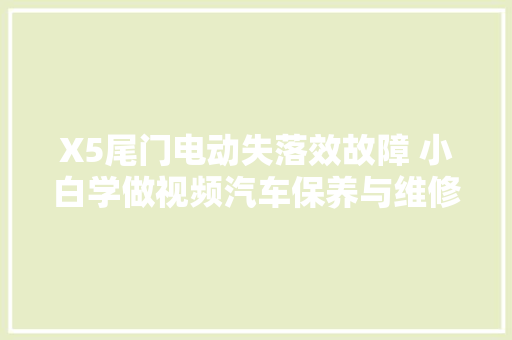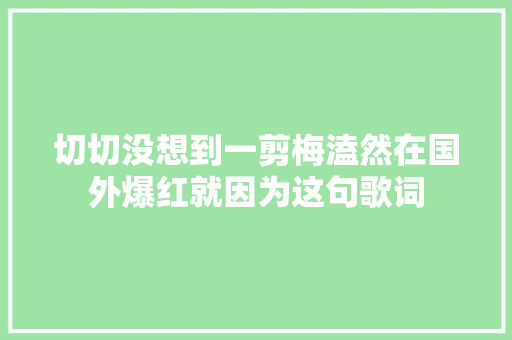出道47年,去年正式封麦引退歌坛的费玉清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首发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歌,会在大事频频的2020年,以这样一种无厘头的办法席卷环球。
在拥有近3亿月活用户的有名音乐平台Spotify上,《一剪梅》跻身多个国家Viral 50榜单前三。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上,国外网友们以《一剪梅》为素材进行的二次创作得到了巨大的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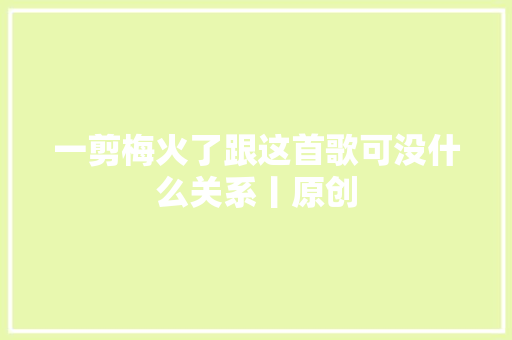
歌词“雪花飘飘,北风潇潇”更因此拼音的形式,被收录进素有“当代青年网络文化风向标”之称的Urban Dictionary,只管其引申义在网友的造梗狂欢中,已经跟它的中文涵义绝不相关。
在这之前,中文歌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地区收成弘大且真实的影响力的案例险些没有。此番《一剪梅》在基本没有粉丝和营销操作的情形下于外洋爆红,彷佛令人惊喜,有人乃至视其为李子柒后又一例“文化输出”。
但轻微理解下事情原委,不把虚无缥缈的“文化自傲”放嘴边的人都会明白,《一剪梅》的外洋翻红,不仅跟“文化输出”沾不上边,乃至跟这首歌本身都没什么关系。
费玉清假如真听了营销号们的引诱,复出输出一波,恐怕就真的晚节不保了。
歌曲《一剪梅》发行于1983年,是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
火的不是《一剪梅》
只是另一个meme
一个叫“蛋哥”的快手用户,上传了一段自己在雪地里唱《一剪梅》的视频,被一个国外网友看到,又把这段视频上传到YouTube。
由于“蛋哥”神似卡通人物Humpty-Dumpty,喜感的形象和深情的唱段形成强烈反差,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迅速达到了几十万的播放量,随后国外精神小伙们纷纭跟进,以《一剪梅》为素材开始了一场自由创作大赛。
首当其冲的是各种版本的remix,在动手能力强又吃饱了撑的网友手里,费玉清用柔情似水的声音毫无压力地驾驭着狂野嘻哈,45度仰头风姿翩翩地与欧美大咖们跨界互助。
对中文充满好奇的网友则开始动手歌词翻译事情,听说有位颇具想法的外国网友,以中国通的身份见告大家,歌名的中文意思是“疫减没”,歌手叫“肺愈清”。
以“蛋哥”视频和《一剪梅》为素材的二次创作,在YouTube上收成百万点击。/YouTube
在这个过程中,歌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以拼音“xue hua piao piao bei feng xiao xiao”的形式成为热梗,用来表达某种类似无奈、无力、无语,乃至无意义的觉得。
随后,各大短视频平台上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种干系的视频,正式引爆了这首歌的热度。一个常见的二次创作格式是,先描述某个让人无语的情景,然后对嘴型来一句“xue hua piao piao bei feng xiao xiao”。其戏剧效果和热度,丝毫不亚于前些年墨镜配烟的“Thug Life”系列视频。
以是,实际上并不是《一剪梅》火了,而是一个以《一剪梅》里的一句歌词为载体的网络梗火了。《一剪梅》的确是经典老歌不假,但在这次狂欢中,网友们的二次创作和群体跟风模拟才是主角。
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化。英国蜕变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将措辞、不雅观念、崇奉、行为办法等通报过程,类比于基因的遗传过程。他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基因,称之为“meme”。我们也可以大略的理解为互联网上的“梗”。
“xue hua piao piao bei feng xiao xiao”跟“真喷鼻香”、“奥利给”以及各种表情包一样,不过是又一个meme,它不仅跟国与国之间文化输出没什么关系,反而大多数时候只在相同的文化氛围中才能起浸染。
与YouTube上迢遥的歌声类似,电影《夏洛特烦恼》早在几年前就玩过《一剪梅》的梗。
常日情形下,传播广泛的meme都具有大略、易于辨识和表达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整首《一剪梅》只有“雪花飘飘,北风萧萧”这一句频繁出镜的缘故原由。
同时,类似基因的遗传,在meme的传播中,“变异”是极其主要的一个过程。网友们对《一剪梅》的这句歌词进行模拟与二次创作,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变种”,某些作品由于更受欢迎而当选中,得到持续的传播与调度,到末了新的作品已经拥有了独立的全新意义。而原始的出处此时已经不再主要,乃至会被遗忘。
因此,热心网友如果单凭《一剪梅》在Spotify上的传播数据,就鞭策费玉清复出的话,显然是要陷小哥于尴尬田地了。
短视频再盛行,
也不是音乐家当的救命稻草
回顾全体一剪梅事宜,短视频平台在个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浸染。与其说《一剪梅》有多火,不如说是短视频有多火。
今年第一季度的环球APP下载记录,由一款短视频App刷新,达到3.15亿次,同时不才载量和用户均匀时长两项数据上,击败了社交平台的王者Facebook。
当环球大部分公司面对疫情影响叫苦不迭的时候,短视频平台却逆势扩展。被迫宅在家里的年轻人,社交娱乐需求无处知足,短视频平台所做的,是为他们供应一个恰到好处的出口。乃至不止是出口,而是一个舒适的房间,里面有沙发可乐和朋友。
受益于短视频的火爆,作为短视频内容主要组成部分的音乐,彷佛也迎来了新的家当机会。在短视频平台兴起之前,还没有什么平台能够如此频繁的引爆各种“神曲”,流水线般地打造爆款。
2017年下半年,借着短视频的东风,《海草舞》《学猫叫》和《纸短情长》险些响遍大街小巷。2018年,全网唱过70%的热门音乐,都来自短视频平台。
歌曲《一剪梅》的评论区,已经换了天地。
不止是新歌,很多老歌也沾了短视频的光,莫名翻红。林俊杰的《醉赤壁》在2008年第一次发行的时候,跟同一张专辑里的《小酒窝》比起来,完备算不上热门。就由于“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这句歌词,被网友通过短视频演绎成了一个热梗,十多年后回光返照,大火了一把。
亮眼的数据和强大的影响力,让音乐家当开始重视起短视频的代价。不少歌手纷纭开始入驻短视频平台,并发布新歌,个中乃至不乏周杰伦这样的重量级大咖。
但是,我们重新核阅一下这些通过短视频成为爆款的音乐作品:要么像《学猫叫》《海草舞》一样,凭借视频里的舞蹈动作引发模拟传播,要么像《一剪梅》《醉赤壁》一样,被玩成了一个梗。很多依赖短视频走红的歌都背负着质量低下的争议,被人们以褒贬不明的“神曲”二字称呼。
还记得几个月前被《处处吻》支配的光阴吗?/哔哩哔哩
由此可见,短视频对付音乐的宣发代价有多么鸡肋。从《学猫叫》到《处处吻》,再到《一剪梅》,的确是一个比一个火。这些以爆款BGM身份走红的歌,会有多少人在意它本身的意义,作为爆款的附庸,它自身独立的代价又有几何?
当然,BGM有自己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视频和音乐也可以在形式和内涵上合而为一,只不过我们要明白,短视频平台的盛行,依赖于碎片化的内容、超低的创作门槛和大数据的喂养。
对付视音乐为具有独立代价的艺术作品的音乐人来说,如果不专门针对短视频平台的特性调度自己的创作,自然也无法轻易占到这个新兴宣发渠道的便宜。但若要为了平台削足适履,不妨转头想想当初自己做音乐的初心。
黑镜中的歌声与我们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打了个有趣的比方,我们的把稳力就像看门狗,而各式各样的内容只不过是用来引开这条看门狗的鲜肉,真正的进入我们思想的小偷,实在是媒介本身。
也便是说,《一剪梅》的爆红,不仅跟这首歌无关,实际上也跟疫情,跟大家面对疫情时的心态都无关。所谓的“丧文化”也并不是在当代年轻人在面对社会环境时,自发产生的不受滋扰的应激反应。
不管是《一剪梅》还是其他的meme,想要获罹病毒式的大盛行,必须符合某些特点:大略、辨识度、低门槛,有时还有些讽刺和诙谐。
90今后的听众,最熟习的小哥恐怕不是《一剪梅》,而是《千里之外》。
这些特点不是由网友决定的,而是由移动互联网这一传播媒介决定的。短视频为何会短?碎片化因何而来?
由于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信息极其便利,这也意味着你会被海量的信息打扰。在这种情形下,严明长内容的体验自然不如那些让人哈哈一笑,快进快出的短内容友好。
罗振宇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国民总韶光GNT(Gross National Time)”的观点,用W表示网民的总数,T表示网民的日均上网时长,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公式:GNT=WT365。随着网和颜悦色数逐渐饱和,大公司们的计策开始从“抢人头”变成了“抢韶光”。
当代人本就所剩无几的空闲韶光,被互联网巨子们切割霸占。微博、微信、短视频、短剧......只微、短、快的碎片化内容,才能更有效地挤占每个人的每一分钟。
我们都在巨子们“算”出来的网上冲浪。/unsplash
于此同时,标榜“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子们,用机器算法为每个人打造定制的信息流,让那块用来吸引看门狗的鲜肉更加美味诱人,终极让“媒介小偷”的入侵更加肆无忌惮。
2015年,微博开始测试将原来按韶光排序的信息流,更换成“智能排序”,试图通过算法让人们看到自己更想看的。
智能排序上线后,微博的用户增长与用户利用时长立即涌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也涌现了大早上刷出晚安图,天下杯结束后刷到揭幕战宣布这类“人工智障”般的笑话。
我们常说盛行的不一定是好的,现在的情形是,盛行的不一定是真的。
天下上只有一首歌可以听,我们可以通过大家都在听这首歌,来断定这首歌是公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吗?
更真实的盛行还会发生吗?/《黑镜》
承认某件事物是否受到喜好的条件是,人们有所选择。而移动互联网现在正在代替我们做选择,这个过程隐秘而持续,它带来的影响又如此深刻。
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多元和宽容的天下,但走到本日,互联网彷佛只带来了一个个相互割裂的同温层,这些同温层看似千差万别,个中谈论的内容却始终未曾分开互联网媒介为我们框定的范围。
首创《黑镜》系列的查理·布鲁克曾经这样阐明剧名的含义——你在每面墙、每张桌子、每只手掌间都能找到的东西:电视、显示器、智好手机,一旦关闭屏幕,就像玄色的镜子一样,使人感到冷冽、畏惧。
还能做些什么呢?
连续盯着屏幕,手指不断向上滑动,还是停下来关掉电源,好好看看黑镜中的自己,在追逐虚妄的盛行的过程中,是否不由自主地眯着眼,再看不到镜子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