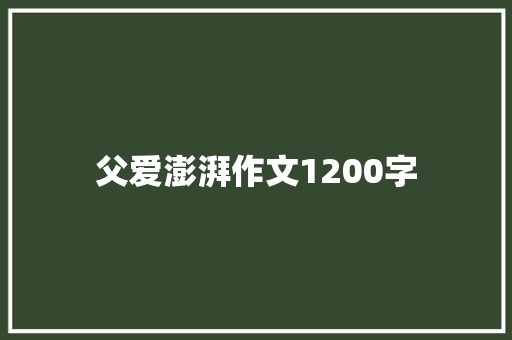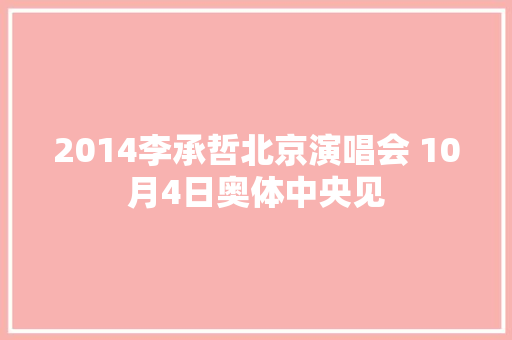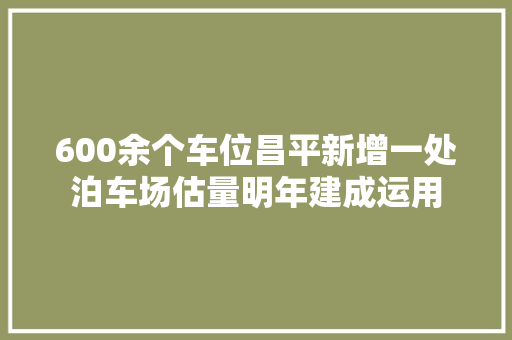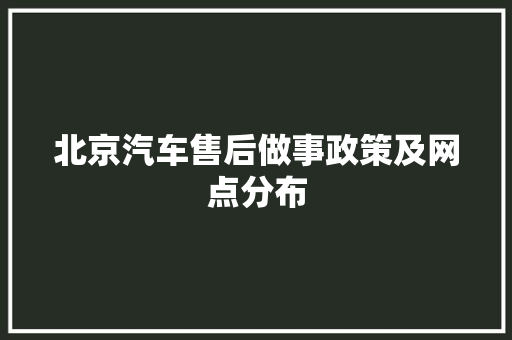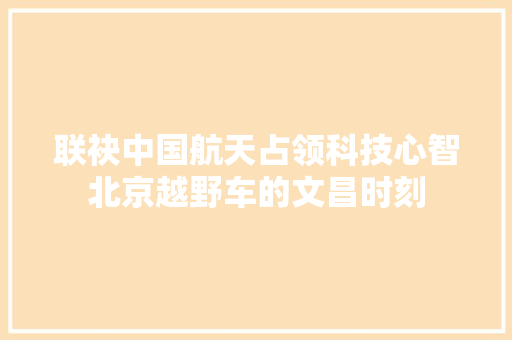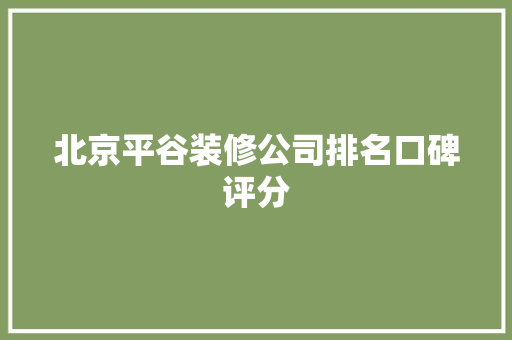“啊,北京啊北京……”国庆节前几天,歌唱家李光羲受邀参加一家养老机构的联欢活动,在不雅观众的强烈哀求下,他再次引吭高唱《北京颂歌》,台下的老人们听得心潮澎湃,有的乃至热泪盈眶。
△李光羲(资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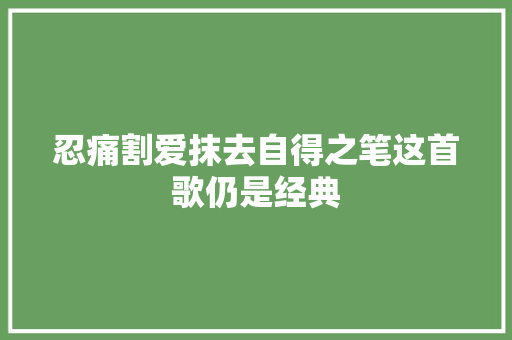
李光羲早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唱《北京颂歌》了。在近70年的舞台生涯里,这支歌伴随他近半个世纪,深情早已沁入血液。而对付李光羲曾处的那个时期而言,《北京颂歌》不仅是一首歌,这一幽美抒怀的旋律带来的是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1971年,一次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文艺事情者时强调,艺术创作要尊重艺术规律。这个指示对当时受到政治冲击的音乐创作领域而言,犹如一股东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颂歌》等传世之作出身了。
《北京颂歌》曲作者之一的田光曾这样回顾这首歌的创作过程:“1971年4月,我溘然接到总政歌舞团一位领导打来的电话,想让我给他们团里的独唱演员写几首歌曲,并点出了几个题目,特殊强调‘歌唱北京题材的更为须要’。”当时词作家洪源、作曲家傅晶同道正巧在田光家研究创作问题,他们便商定一起互助。在两三天内,洪源写出了歌唱北京的两首词,经由研究,终极选用了个中一稿。
△田光(资料图)
△傅晶(资料图)
“残酷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两三天内写出这独具诗情画意的绝美词作,洪源并非依赖天才,而是发自内心的火热真情。
早在《北京颂歌》出身之前,作为战友文工团的一名专业作者,洪源就去天安门当过兵、站过岗。
“不是采风,便是去当一绅士兵。”几十年后洪源这样回顾那段经历,他在被派岗时还特殊哀求每个哨岗的位置上都要去站一站、每个韶光段都体验一下。“比如深夜里站在纪念碑下,黎明前站在金水桥上,那种觉得真的便是不一样。”洪源说,他最喜好的是在日出之前在金水桥上这班岗,“最早是洒水车过来,把长安街洒过水之后,站在金水桥上向着东方放眼望去,真的是残酷的朝霞升起在北京”。伴随着朝霞的逐渐升起,耳边传来北京火车站响起的钟声,洪源将自己对北京黎明的特殊感想熏染都写在了日记里。
△洪源(资料图)
听说,洪源当时在天安门站岗时并没有想到创作歌曲,但写过颂扬英雄纪念碑、五星红旗、金水桥、天安门以及中南海的“五颂”的诗歌,这都为后来写歌词做了积累。
“好的歌曲能够住进听众的思想与灵魂之中。”几十年来李光羲一贯武断着这样的信念。在他看来,这首《北京颂歌》历经岁月依旧流光溢彩,就在于它令身处困难中的人们相信未来,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相信来日诰日一定会更好。
忍痛割爱抹去了得意之笔
人们常说“事事开头难”,作曲彷佛也不例外。正由于这个道理,同一词可以谱出多种不同节奏、调式和风格的曲调来,而且都有可能成为各具特色的佳作,当然也都存在着失落败的可能。《北京颂歌》的创作构思,开头碰着的自然便是采取什么样的音乐素材的问题。田光曾回顾,他和傅晶先是谱写出了一个四分之三拍、圆舞曲形式的曲调,但词作者洪源以为四分之三拍的风格不足庄严,建议他们重新谱曲。对原曲,作曲家们舍不得丢弃,便商定作为成品保留,由田光将歌词谱成后来的曲调。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都城,是天下名城,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歌颂北京就必须表示出各族公民共同的意愿。”田光他们首先明确了一点,即凡属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特点均该当避免,而同时又必须在民族腔调的根本上进行创作。初稿写出后,田光创造第二个乐句“升起在金色的北京”有点西藏腔调的影子,为了风格上的统一,只管这是得意之笔,末了他也只好忍痛割爱抹去了。
据田光的子女们后来回忆先容,当时父亲谱写出来之后,历经一年多的广泛搜聚见地,进行过大大小小很多次修正,个中还包括田光的妻子、作曲家朱霞的修正见地。险些每修正一次都有底稿留存,仅手稿就一大厚本。
艺术佳构都是在不断打磨中炼成的。经由反复地搜聚见地和加工修正,《北京颂歌》于1972年冬季全军分片文艺会演中得到精良作品奖。
《北京颂歌》的旋律激情亲切旷达、豪迈洒脱,一洗当时政治口号式的歌曲模式,经由中心公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立即风靡全国。
都城的听觉符号
《北京颂歌》先后由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和男高音歌唱家李光李光羲、李双江录音,形成了一首歌曲三个录音版本的征象,这在中国音乐界也是亘古未有的,传为了一段佳话。三位歌唱家的出色演绎使得《北京颂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起床号吹过往后,天还黑着,在飘荡着草木和露水喷鼻香气的天空中,响起了部队广播站播出的《北京颂歌》,我和我的战友们手里端着打饭的搪瓷碗,如醉如痴地站在微寒的晓风入耳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陈凯歌这样描述自己最初听到《北京颂歌》时的情景。1969年春,北京成长的陈凯歌远赴云南插队下乡,后来在当地参军从军。在那个分外的年代,少年离家又背负很重政治包袱的他,心里有着多少很多多少酸涩、多少很多多少乡愁,“炊事班的赤色炉火在远处跳动,辽阔的天涯逐渐升起曙色,每每是歌声消歇的那一刻,天色大亮,由歌声所构建起的伟大北京才在面前消逝,我们的乡愁也随之而去,那时会有一滴骄傲的泪水点落眼角。”陈凯歌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那个分外年代,《北京颂歌》在抒产生发火者民族自满感、表现各族公民对都城北京的神往之情的同时,更是很多大家生路上的一抹光亮。
李光羲向回顾,1979年他参加中国文学艺术事情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与电影演员孙道临谈天。孙道临说,1973年国庆节那天晚上听到李光羲唱《北京颂歌》时,他正在屯子劳动改造,大喇叭里传出的歌声让不少人顿住。虽然广播里并没有报歌者姓名,但孙道临他们都听出来“这是李光羲”,不少人当时就哭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大批的干部、学者教授、文艺事情者和我的处境一样,都在屯子劳动改造,根本不知道这生平还能不能规复从事自己的奇迹。大家溘然听到我出来唱歌,就以为肯定是我被解放了,顿时每个人感到自己也有希望了。”忆及往事,李光羲无限感慨。
犹如天安门是北京的视觉标识一样,《北京颂歌》无疑便是都城的听觉符号。20世纪80年代,北京公民广播电台每天开始广播时,先播放《北京颂歌》的旋律,然后报告电台呼号,再先容这次的广播节目内容,然后开始正常广播。之后,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阳光残酷的日子》更是将之作为主题音乐利用,让更年轻的人们知道了“残酷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的意境。2019年,《北京颂歌》更是入选“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
半个世纪过去了,作者洪源、田光、傅晶都已不在了。但《北京颂歌》作为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还将会被咏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