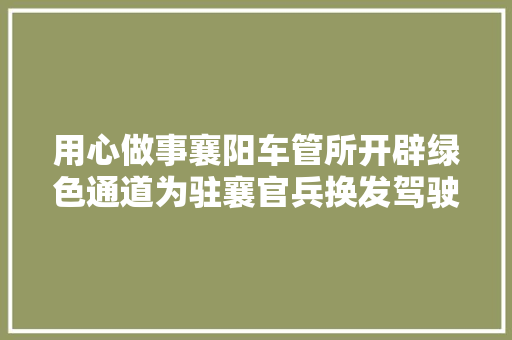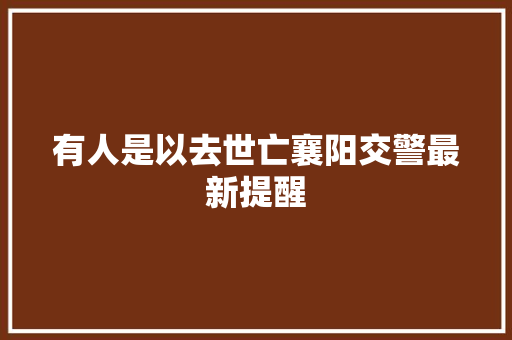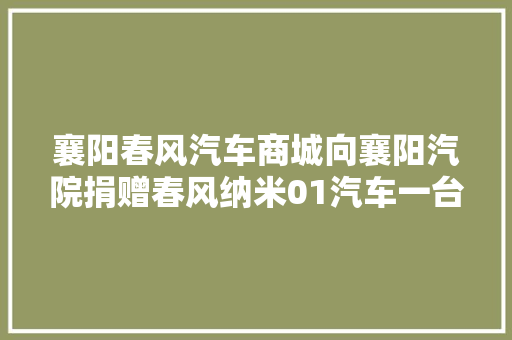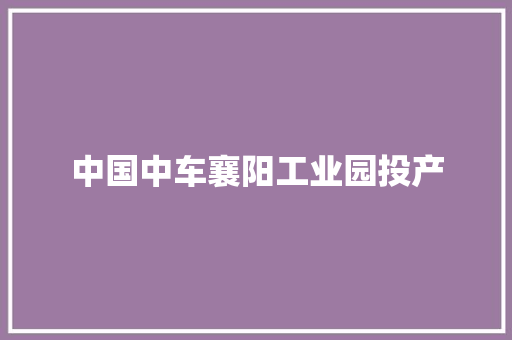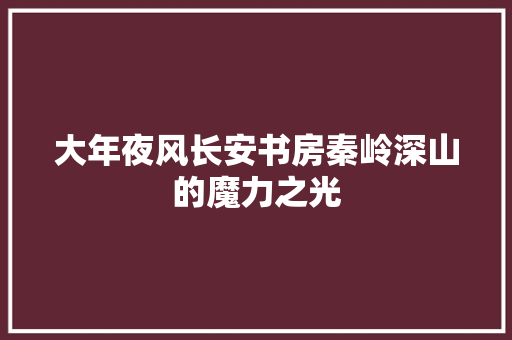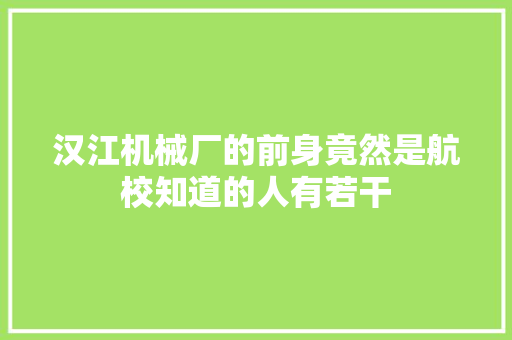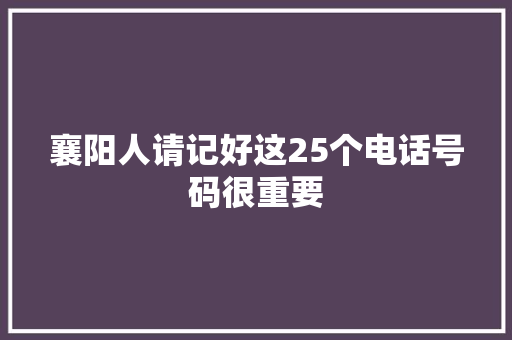由于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热映,汉江边沉寂许久的湖北襄阳被网友“挖”了出来。
这是一座罗贯中笔下的历史传奇之城,一座金庸作品里的兵家博弈之城,一座南北文化交融、新旧和谐共生之城。千百年来,这里上演过汉皋解珮、三顾茅庐、水淹七军、宋元鏖战等诸多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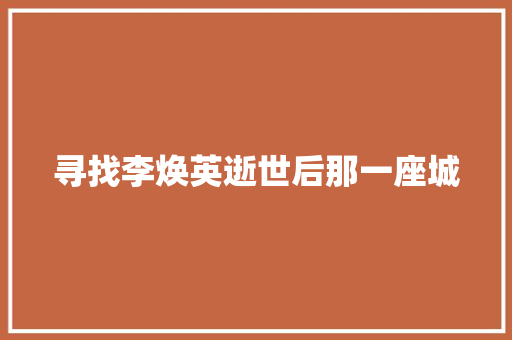
登上古老的襄阳城,面朝汉江,手抚墙砖,沧海桑田,万物皆变,不变的只有那伴随青砖愈发浓厚的历史气息。
三线培植为什么选择襄阳?
老街区、老厂房,红砖墙、筒子楼;纵横的钢架、袒露的水管,掉色的门窗、迂腐的瓦房……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环山路孙家冲1号,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国营卫东机器厂)的大院里无处不透着浓浓的年代感,所有的建筑和装饰都保留了20世纪80年代的风格。
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要取景地,随着电影票房及口碑的持续走高,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厂区内的食堂、饭店、理发店、幼儿园等生活场景,散发着浓厚的怀旧气息,引起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顾。
“李焕英”之以是能引起强烈共鸣,除了有亲情之温暖,也有历史之厚重、时期之斑斓。
“电影中,那些斑驳的机器、迂腐的砖墙等,激活了人们对三线培植期间的历史影象,让人们回忆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史论部西席刘精科说,除了原卫东机器厂,襄阳还有很多类似的三线培植期间工厂大院。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规模巨大的国防及工业培植,历史上称作三线培植。
三线培植者们唤醒了沉睡的鄂西北大山,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会战在山林中打响。刘精科说,仅在襄阳就建有汉光电工厂、建昌机器厂、红旗机制厂、红山化工厂、华光器材厂、汉江机器厂、宏伟机器厂、汉丹机器厂、襄樊内燃机厂等40多家三线企业,这些企业紧张集中在南漳、谷城、宜城、老河口以及襄阳市区的郊区等地。
“襄阳地处荆山山脉,是鄂西北主要交通枢纽,山高林密,七省通衢,既有适宜三线培植选址布点的地理位置上风,又有较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符合‘靠山、暗藏、分散’的三线选址原则。国营卫东机器厂建厂初期,第一批生产设备便是通过水路运输,从武汉运抵襄阳的。”中国三线培植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勇先容,当时国家三线办在全国13个省区市进行三线选址调研稽核。末了,将襄阳确定为三线培植重点区域,襄阳、咸阳、绵阳等成为全国三线培植重点城市。
至今,卫东机器厂仍藏在襄阳城郊的山林里。在与卫东厂一同发展的顾勇眼里,那不是只存在于冷冰冰笔墨阐述中的历史,而是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空想的澎湃岁月。“师长西席产,后生活”的日子,对付早年提相对优胜的城市来到襄阳山沟的培植者们来说,适应生活条件的落差,是他们要过的第一道关。
“建厂初期的孙家冲,杂草丛生,虫蛇随处可见,都是泥巴路,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已逾耄耋之年的方恒明净叟是卫东厂早期的培植者之一,1969年参军队转业后,他从北京来到卫东厂参加三线培植。刚来那会儿,住的屋子叫“干打垒”,便是土坯房,喝的是泥浆水,一些年长已成家的老师傅们更是携老带幼住在阔别厂区的二生活区的棚子里,四处透风,一天高下班几趟路就得走一两个小时。生活中的艰巨可见一斑。当时厂领导们办公的地方叫“指挥部”,见过的同道都知道那是一间不折不扣的牛棚。
方恒清没想过转业后会是这样的生活等着他,但他对那段岁月却从未后悔。“说实话,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更好的平台,但我舍不得,我的青春在这里,我的家人在这里。”他说。
汗水、青春、生命,艰辛、激情、无畏,忠实、拼搏、捐躯……在“备战备荒为公民”“年夜大好人好立时三线”的方针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号召下,当年无数像顾勇、方恒清这样的工人、干部、工程技能职员、屯子劳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鄂西北山林中。
三线培植改变了那些从外地来的培植者们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襄阳,在这座城市的履历上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眸往事,翻阅档案,襄阳不止一次在历史上扮演如此主要的角色。
“先秦之邯郸,明清之秦淮”
打开舆图,襄阳古城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它既把控着南下与北上的陆路通道,也紧握着东进与西出的水路交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从来不短缺历史故事。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襄程度日被认为是汉水支流,古又称南渠。只是到本日,汉江成为主脉,襄水隐没不再。
无论是巢居穴居、茹毛饮血的早期人类,还是筑屋群居、亦猎亦耕的氏族社会,彷佛都可以在汉水中游这块山川沃土找到适宜的生存居住条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叶植见告,在现在襄阳太平店镇至樊城团山一带,已创造多处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采集点。从神仙渡镇到樊城的汉江北岸,新石器至六朝时的遗址和墓地星罗棋布,邓城遗址更是被几十处大型遗址和墓地所包围,已发掘的墓葬超出4000座,鏖战岗上也发掘出东周楚墓300余座,正在发掘的小型墓葬数以千计……
那时,这个处于北方原始文化与南方原始文化的中间地带,带有明显的南北方文化过渡交融的特色。
叶植说,襄阳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北津戍,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襄阳耆旧记》记载:“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意指春秋战国时这里是楚国北方的两个渡口城邑——东津和北津,成为北通中原和向东拓展的主要渡口和军事要地,造诣楚国一代霸业。个中,东津一名现仍保留。
在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期,处于汉江中游的襄阳,与长安、洛阳险些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关系,沿水路西上长安,沿南襄盆地过方城,可直抵洛阳。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到清代中期,汉江上汉口到襄阳的船只每年约有两万艘,老河口到樊城、樊城到社旗,长期来回的船只大概有1600艘。可见当时襄阳水运的发达。”叶植认为,襄阳能够成为商贾云集、货流利畅的商品集散地,与汉江这条“黄金水道”密不可分,从汉口到襄阳的汉水航线则是推动襄阳经贸发展的动脉。
楚人的活动区域,也环绕汉水展开。史料记载,楚之先祖原是中原部落,在一代代部落首领的带领下举族南迁,其活动的路线大约便是沿着汉水向南,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终极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一个可以问鼎中原的强大诸侯国。
楚文化融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蛮夷文化)为一体,被著名历史学家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盛赞:“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中原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这北南两支中原文化是上古中国残酷文化的模范,而与时期大致相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遥相照映。”
一条汉江,完成了上游与下贱的文明连接,同时也让襄阳成为南北文化交融贯通之地,荆楚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这里孕育了楚赋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典故流传至今,留下了穿天节、端公舞、牵钩戏、苞茅缩酒等楚风遗俗,留下了西周邓城、宜城楚皇城、南漳山寨群、枣阳九连墩等楚文化遗址。
“汉晋以来,代为重镇”
在襄阳的大小餐馆用饭,总会被问道:“主食要什么,面食还是米饭?”在吃米的南方,很少见。汇通南北,亦南亦北,早就嵌进襄阳的骨子里了,这座城因此而原谅。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刘表领荆州牧,把襄阳管理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为浊世中一片安宁的“绿洲”。为避战乱,不少士人流寓襄阳,诸葛亮、司马徽、徐庶、崔州平等一批打算精英,文学家王粲、书法家梁鹄等一批精彩人物,与当地绅士庞德公、庞统、马良等汇聚襄阳。当时的襄阳,人才荟萃,盛极一时。
诸葛亮躬耕陇亩,并非真的是“苟全性命于浊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只是要选择一个地方,以便更好地不雅观察天下大势。襄阳是南北交汇之地,东西交融之域,或为空想之选。
两汉期间,襄阳的水陆码头地位更加凸显。东汉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这样描述襄阳码头:“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
隆中距汉水不远,无论陆路还是水路,和外界联系都很便利。后来事实证明,诸葛亮的选择是精确的。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紧张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空隙之际拜会绅士、结交朋友。他在这里和庞德公、庞统的联系更多了,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朋友圈子,如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等。
或许是汉水的滋润津润,卧龙山松青柏翠,喷鼻香樟树高大挺立,当年诸葛孔明的读书处,刘备来访的三顾堂、六角井,显得神秘而森然。恍惚之中,“三顾茅庐”的场景在面前重现了:卧榻上,诸葛亮睡得正酣;刘备拱手而立,静候阶下;关羽、张飞站在门外,烦躁不安。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这是《三国演义》中对隆中的描述。隆中是诸葛亮“躬耕陇亩”的隐居之地、刘备“三顾茅庐”的求贤之地,更是《隆中对》的出身之地。隆中保存了诸葛亮学习、交友、生活的许多遗迹,历经1800多年的岁月洗礼,依旧风采盎然。
在此“隆中对”,“三顾频烦天下计”,诸葛亮终出山远行,从汉水到长江再汉水,辅佐刘备。
都说一部三国史起于襄阳,终于襄阳。马跃檀溪、司马荐贤、三顾茅庐、水淹七军……这些传奇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在襄阳的大街小巷,常常会与《三国》撞个满怀,比如诸葛亮广场、广告牌上的孔明菜、古隆中酒,一部《三国》被掰开了、揉碎了,分放进这座城的街巷与食谱里。
“山水不雅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襄阳城东南约15公里处,一座山因孟浩然、皮日休隐居于此而誉满天下。鹿门山,并不见危岩绝壁,山道宁静,林荫迎面,眼帘中只见野花奇树,耳畔时闻鸟雀啼鸣。
在孟浩然的诗中,处处能看到这里的美景:“结交指松柏,问法寻兰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屡惊马。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云簇兴座隅,天空落阶下。”
生于襄阳的孟浩然一定是喜好这里的清幽,喜好这里的天籁。在孟浩然的笔下,襄阳城是一座俏丽的山水城,“山水不雅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汉字的精妙,融化在这样的诗中,就像襄阳城边汉江的流水,爽然清澈。在襄阳寻山问水,再回味他的诗作,又有了不少详细生动的印象。
水从城中过,中间横一条浩大的汉江,不仅让襄阳城温润许多,而且南船北马,处处可见活气。
在唐代,襄阳是都城长安与江南财富之区往来的咽喉,史称“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从而带动了沿途文化的发展繁荣。
这等奇丽风光与繁华市井也让不少文人墨客为之容身。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既是一个旅人的感怀,也是对一个地方风华的最朴实、最激情亲切的褒奖。大墨客王维从洛阳经襄阳南下,因与孟浩然的交谊,他在这里逗留了数日,或是自然风光触发了发达诗情,或是容身汉江边远眺,吟出了这流传千古的诗作。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而要理解王维这句诗,最好登城墙一望。汉水苍苍,古城悠悠,视野尽处,是繁华市街,是水运码头。
一江春水绕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一方山水,因诸多诗词更添韵味;一方水土,之于文人骚客,也如同一个不尽的宝藏。山水灵气哺育了孟浩然这位唐代山水田园墨客,引李白、白居易、王维、岑参等来往于岘山、鹿门山、万山、习家池、汉水等地,用诗文记载游历于此的感想熏染,尽显历史的风华与自然的佳美。
李白的一首《襄阳曲》,写尽了风华,还原我们对当年襄阳的想象:“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篱,倒著还骑马。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金戈铁马踏“江湖”
优胜的地理位置,加之丰饶的物产和南船北马的便利交通让襄阳拥有了“其险足固,其土足食”的成本。
襄阳既把控着南下与北上的陆路通道,也紧握着东进与西出的水路交通,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多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战役都与它有关。
从春秋战国到20世纪40年代,此地文为绅士荟萃的登临之所,武为群雄逐鹿的争雄之地,兵戈频仍。根据襄阳有名学者晋宏忠的研究,襄阳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曾发生过约200多次大小不等的战役,他在其著作《襄樊兵事春秋》中就详细先容了172次战役。
个中,耳熟能详的宋元襄阳之战,既是一场王朝更替的决定性战役,更是一次南北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这场中国军事史上规模巨大、历时漫长、去世伤无数的重大战役,放在金庸武侠小说里,虽已是英雄末路,仍旧让人荡气回肠。
在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渲染之下,为千百年来充斥着征伐气息的襄阳蒙上了一层江湖情怀滤镜。正如小说中,杨干涉干与郭靖能否守住襄阳?郭靖只留下“鞠躬尽瘁,去世而后已”八个字。
频年的战役和厚重的文化也为小说家们供应了绝佳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末了一回让主人公郭靖、黄蓉于西岳论剑后驰马助守襄阳城。《神雕侠侣》自第二十回起,全书约1/4内容的背景都在襄阳一带。郭靖、黄蓉的小女儿也因出生于襄阳而取名郭襄。这两部书中不少情节都以宋元襄阳之战为背景。
经由了无数场大战洗礼后,战火已经刻入了这座城池的风骨之中。就像古城临汉门前雄伟耸立的城门,风蚀不倒,经久弥新。
而无论史籍还是武侠小说,凡是提到襄阳城,从里到外也都是一个大写的“侠”字,比较安稳度日,他们更期待来一场雪夜风陵渡的寒暄。
襄阳古城建城史长达2800多年,经历了楚国军事渡口“北津戍”、西汉初年设县筑城、东汉末年扩建、南宋建筑砖城、明朝再次扩建定型的几次营建,或许正是经历过太多战役之后的一种自觉。
从孟襄阳(孟浩然)的不羁到米襄阳(米芾)的洒脱,从“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名句,从战火纷飞的《三国演义》到铁血赤心《射雕英雄传》,“襄阳”之名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不过,从襄阳地区的城市发展与行政建置沿革来看,历史上今襄阳地区地名几经变更,或谓襄阳,或谓襄州,间曾侨置雍州,新中国成立后还曾用过襄樊之名。2010年,告别60年的徘徊,“襄阳”的历史名称终于重归这座古城,可见这一地名已经内化至本地地方文化之中,难以割舍。
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有许多襄阳人乐意慢下来,在茶前饭后走上城头,抚摸青砖,看岁月下的苔藓,不雅观战役下的痕迹。这也包括当地“90后”音乐人管泽祯。
“走遍古城穿小巷,飘满酒喷鼻香黎明望,抚一滴神往洒向汉江,圈圈荡漾无声无响……”管泽祯在自己的原创歌曲《古城襄阳》中这样唱道。
战歌渐远,壮歌未央
“这些老屋子跟我原来事情的工厂一样,特殊亲切。这么多人,彷佛又回到了那时的热闹。”70岁的王道琴领着儿孙一起来卫东厂探求当年的回顾。面前,挂着老式招牌的红砖屋子依然能让她感想熏染那个年代散发的灼热。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襄阳市共接待游客83.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404万元。《你好,李焕英》上映后,每天到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六〇三文创园等电影取景地打卡的游客超3万人次,襄阳市还特意开通了从城区去取景地的公交专线。
随着20世纪80年代天下格局的变革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履行,三线培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企业转产或迁居,原有的厂区闲置下来,并留下了大量设备、厂房等三线工业遗产。
“建筑作为可见的物质载体,对那段期间在襄阳展现出的风起云涌的激情岁月,供应了翔实而生动的触摸空间,为民族精神延续、地域文化培植和城市家当品牌开拓供应了优渥的根本。”湖北文理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教授朱亚斓说。三线培植工业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属于城市的稀缺性文化资源。发展工业旅游家当,不仅有助于传承三线文化,而且能够创造经济效益。
襄阳市已经明确,通过政府的方案和政策勾引,调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工业企业以工业资源为吸引物,通过工业旅游的开拓扩大企业影响力,丰富全市旅游产品,发掘新的旅游增长点。
在襄阳城南岘山脚下,另一处工业遗迹笔墨六〇三厂也完成蝶变——六〇三文创园聚焦文化艺术、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教诲培训等业态,方案有创意设计办公、视觉艺术展示、文化休闲体验等区域,聚拢造就了40余家文化企业,从业职员近1500人。
在城市更新与家当转型的浪潮中,烙印着“三线精神”的老厂房并未埋没,镌刻着历史故事的古城墙仍旧耸立,当代经济和文化创意在这里找到根脉。
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襄阳主要军事计策地位的功能发生了积极转变,它的主要影响力已由军事领域逐渐过渡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计策布局中。不过,与襄阳相互造诣的汉江,依然是襄阳未来发展的主要支撑。
国家颁布履行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支持襄阳巩固湖北省域副中央城市地位,加快打造汉江流域中央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明确了襄阳的城市定位和义务任务。
襄阳市市长郄英才说,“十三五”期间,襄阳2条高铁通车、1条高铁开工培植,还开通了5条中欧货运国际专列、4条铁海联运专线。面向未来,襄阳要在“十四五”期间全力打造汉江流域中央城市。
在对历史的回眸中,襄阳也更明确了自我的历史归属。(皮曙初、侯文坤)(稿件部分内容参考:《襄阳印象》《汉水的襄阳》《襄阳印记》)
【纠错】【任务编辑:张樵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