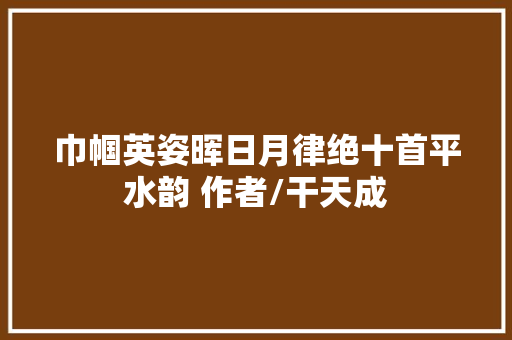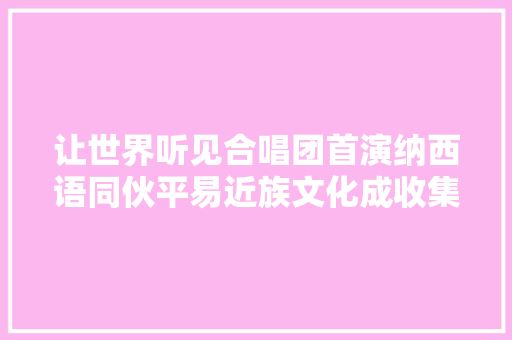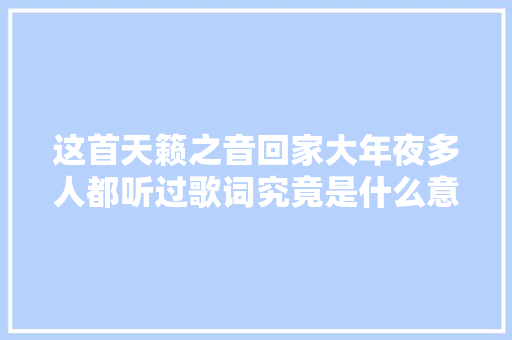文/杨大侠
从西昌出发,穿过雅砻江,途经泸沽湖,是很多人从四川到云南丽江的自驾游选择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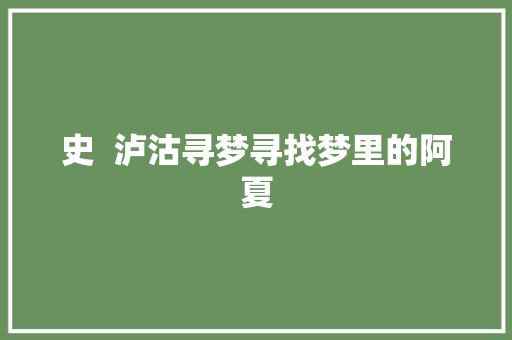
泸沽湖,这个蜿蜒了约50平方千米的“高原明珠”,横跨川滇两省。它的起源已无从考证,首次涌现的笔墨记录,出自于明朝旅游爱好者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元朝末期,横行霸道了160多年的蒙古军节节败退。个中一个分支流亡到一个温婉柔美的湖畔边上,从此世代定居于此;此处,便是泸沽湖。
也正是蒙古人的定居,泸沽湖孕育出了新的传奇:这里的居民,一部分属于四川,另一部分属于云南;史料的记载,他们一部分属于羌族,一部分属于纳西族。这个居民的族群,叫做摩梭族。
摩梭族的摩梭人同时属于两个民族,但他们自身的民族属性却难以确定。犹如身为珠峰“脚工”的夏尔巴人、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克里雅人,由于缺少历史资料加以佐证,摩梭人亦是未识别民族的分外存在体。
到现在,摩梭族总体人口5万多人,在未识别民族中的人口数量属于中规中矩。而便是这5万多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迷惑与美好:民族属性、母系制度、走婚、“阿夏”与“阿柱”。
溯源摩梭人
摩梭人的民族属性难以定位,紧张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措辞,但没有自己的笔墨(这也是大部分未识别民族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正由于没有笔墨记录,后来的考古、历史学家才有机会对其进行反复对敲,各自为政,百家争鸣。
3000多年前富商期间的甲骨文上,第一次涌现“羌”字;东汉《说文解字·羊部》有对羌族的确牢记录。到了西汉,羌族开始遍布全国各地,个中就有泸沽湖的一端——云南。
但记载也止于此。没有干系记录解释古代羌人生活在泸沽湖畔。因此,对付摩梭人的溯源,我们分成两种设想:一是在元朝之前,羌人没有到泸沽湖畔定居;二是已在此定居。
第一种情形,牵扯到纳西族。纳西族是古代羌人与土著人结合的产物,到元朝,忽必烈征服大理后,对云南进行全面统领。纳西族的牵制,紧张由当地部落首领卖力,同时派大量蒙古人驻扎。
从此,纳西族的内部构造开始分裂:由蒙古族与纳西族同时组成。
因此到元朝衰落,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开始涌现,他们以两个民族的形式呈现:蒙古族、羌族、纳西族(根据少数民族的划分,现在的纳西族跟古羌族没有关系)。
如果是第二种情形,那就大略多了,就只剩羌族和纳西族——蒙古族作为“客家”的身份乱入,不列于此内。
而无论摩梭族以哪一种情形存在,都不能否认它是纳西族的“后裔”;而无论纳西族的文化如何纷繁,也不能粉饰摩梭族人神一样平常的“贵族”地位——以母为贵的民族。
母系家庭与“走婚”制度
母系家庭,摩梭语称“日杜”,是摩梭族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这种社会单位,在全天下已险些消逝殆尽。
摩梭人中,女人的地位远高于男人。每个家庭的生产、生活、财产管理、集成,都由女性担当(达布);而每个家庭的女性长辈,更是德高望重的代名词。家庭中任何决策、赏罚、财务支出,都由最为年长的女人说了算,丈夫、子女、孙辈、子弟的旁系父老等人,只需百依百顺,按操持实行。
也正是这种女性当权的文化,所有的子弟与母亲/祖母的关系,要比父亲/祖父的关系近得多。
正是基于此,摩梭人的观点里,没有“我”这种个体,只有“我们”这种群体——当然,“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类人。这样的好处,是所有劳务男女共同担当,所有财物男女共同分享。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圈子里,男女还算是平等的。
同一血亲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别扭,就更别提“外人”了。在摩梭文化中,血液中没有母亲/祖母血脉的人,都是外人。也便是说,父亲、祖父、丈夫、媳妇都是“外人”。所有“外人”,都不能享受财产的继续、利益的分配,也不能随意在女方家走动,于是,母系文化中的另一种制度——走婚制度涌现了。
中原中原文化,男性是在20岁举行成人礼,女性在15岁举行成人礼。而摩梭人的成人礼,男女都在13岁。也便是说,13岁往后,摩梭人就能谈婚论嫁了。然而,摩梭男女之间奉承的是,“男不婚女不嫁”。
夜晚,是成年摩梭男子随意出行的时候。此时,男子可以翻墙、爬楼、用开锁工具进入另一家庭的成年女子闺房,与其发生性关系。一名男子可以与多名女子发生关系,女子亦可与更多男人发生关系——多么混乱的天下,万一艾滋爆发咋办?
一番巫山云雨之后,在天明之前,男子必须离开温顺乡,开门、下楼、翻墙,滚回自己家里去,规复“女尊男卑”的民族地位。
这种性关系的产生,没有大摆酒宴的仪式证明,因此“男不婚女不嫁”;但两者结合,代表了另一个生命的出身,它符合平凡夫妻关系,因此这叫做“走婚”。
走婚是摩梭男轻男女考验好奇心的快活进程,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乱象。下一代子女的父亲根本无从考证,同时早已冲破了二胎政策的规定。如果女方生养子女过多,还增加了家庭生活包袱;如果女方有数位姐妹,后代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无从定义。
也正是如此,母系的机制在摩梭族无可撤消,毕竟对后代卖力的,只有女方。
到现在,这种乱象逐步得到改不雅观。文革爆发后,摩梭男女有不少人被逼迫“一夫一妻”。到现在,摩梭人已经接管这种逼迫理念,并能与族外人结婚,实施一夫一妻。
也正是“一夫一妻”,摩梭青年男女逐渐懂得耻辱礼仪之心,学会尊重和爱一个人。他们将生活活成了摩梭族的传说——阿夏与阿柱。
梦中的阿夏与阿柱
任何混乱的国度,都不缺少动人恻隐的传说,即便混乱如奇葩的摩梭族也不例外。
传说,自这支无从考证的民族从记事开始,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就有了自己的盟约。摩梭语中,“阿”代表情人,“阿夏”代表男子心中“永久的情人”,“阿柱”代表女子心中对男方的爱与留恋。
阿夏与阿柱,隐喻了一对男女之间互倾衷肠的情话,守望白首的誓约。朦胧情愫之中泛起这两个词,就代表了生平一世,无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然而在有记录的几百年里,这样的定情盟约却成了一个笑话。民族男女除了家庭不雅观,基本上没有道德不雅观、耻辱心,混乱犹如天子后宫。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令人切齿腐心的文革,也举措看成了一件好事。它让一个民族的道德沦丧回归正统,让摩梭人能走出本族感想熏染精彩的天下,让人们对其心生神往,也让现实与传说形成了美好的无缝对接。
摩梭的历史,在光阴罅隙中逐渐模糊;摩梭母系文化的好坏,每个人心中有自己的解读;而“阿夏”与“阿柱”,又显得那样隐晦飘渺。这当中的美好,或许只有当泸沽湖畔的夕阳下沉,走入纳西族村落的“摩梭之家”,倚在风格拙朴的圆木寨楼上,到梦里去寻吧。
附:关于阿夏,有一首悠扬大气的古风歌曲。可惜QQ音乐素材库没有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意境,非我所能力及,就借用过来,当做结尾吧。
泸沽寻梦
文案:梦里我是你的阿夏,统统仿佛真实存在过,循着零星的影象来到这里。等到决定离开的末了一夜,你涌现了,湖光山色都已经来不及。
歌手:银临
允山风一抹缥色
拂绿青衫袖上新荷
渺层云独行千万里
舟中吾且作远来客
梦里一碗青稞酒接过
辗转欲寻梦外的篝火
听不真切此刻你是因谁而歌
行囊不多只为解惑
船家停泊靠岸那一刻
仿佛前世江湖我来过
白裙红衣的姑娘桥上婀娜
这一方风土名曰摩梭
日出而作岁月如梭
那传说本不属于我
开春后崖边覆雪薄
轻烟未霁犹向藤萝
行尽处双鹤穿云过
大概只在诗行停过
梦里曾有雕花楼一座
凭栏宛如彷佛梦外的轮廓
摇红烛影今夜少了你的醉卧
投望天井微澜泛波
循着幻梦却等它陨落
实在若寻不到又如何
我再次围着篝火曼舞欢歌
叫嚣所有想说不能说
临别时候蓦然回顾
忽而相遇触目惊心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世上原有许多因果
都来不及逐一道破
我应是泸沽烟水里的过客
孑然弹铗,划天地开阖
重逢过的,梦醒之余
却忘了该如何洒脱
史籍是一壁镜子,它能反射出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
侠义是一种力量,它能刺破世上所有坚不可摧的壁垒;
看不见的是灵魂,无惧壁垒是正气;
当商业有了灵魂与正气,它就有血有肉,精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