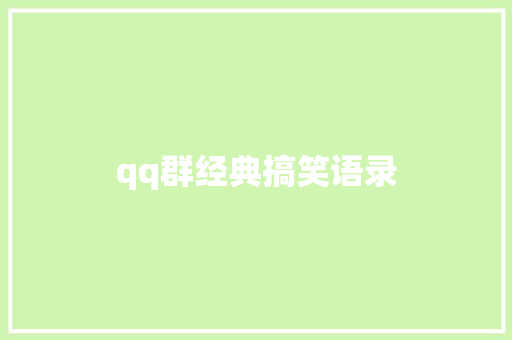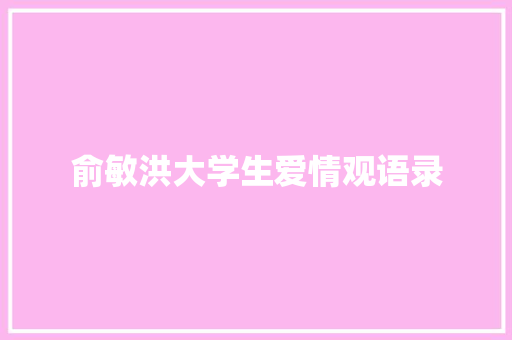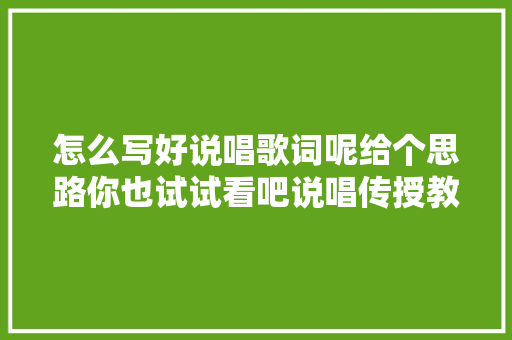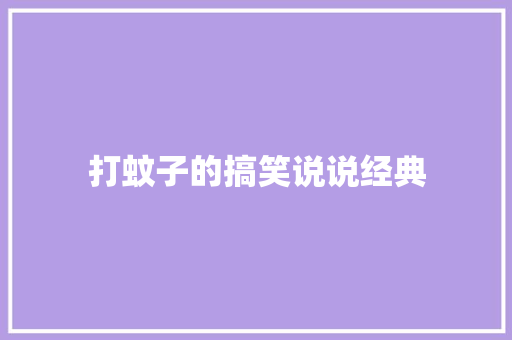我赶紧劝道,别哭,别哭,有话好好说。话没说完,又招致了对方歇斯底里的一番哭骂。
原来这小妮子一贯找不到我,打电话到我宿舍都不知道我干嘛去了,她竟然费劲巴拉的找到了王辉。王辉本来不愿意见告她手机号码,但架不住这妮子的去世缠烂打一番哭闹,末了终于屈打成招。以至于我刚一接电话就噼里啪啦挨了一番年夜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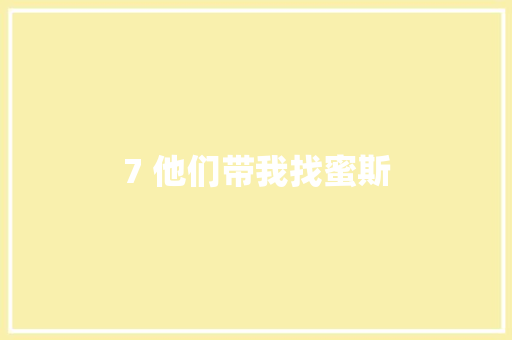
「去世欧阳!
去世忘八!
这么永劫光你都去世哪去了?亏你还用了手机,给我打个电话你能去世啊你!
去世忘八,你怎么不去去世啊你……」我无语的听着杨蒙哭泣的谩骂,无端想起了周星驰的台词:我是一个跑龙套的,但不是一个去世跑龙套的。
「……杨蒙,你骂我忘八也就算了,但能不能把前面的那个去世字去掉?」我刚说完,又招致了一番更剧烈的年夜骂:「你便是去世忘八!
去世欧阳!
去世忘八忘八忘八!
去世去世去世去世忘八……」
看来我跟周星驰一样,注定命运多舛。
不过我还是松了一口气,这小妮子感情虽然激动,但还好王辉没有见告她我现在的情形,否则我不敢担保她会不会直接打辆面的杀过来,在基地大闹一翻。到那个时候,恐怕我是没能力保住她了。
我只能费劲的给她阐明,说现在阑尾被切掉了,伤口刚刚愈合,还不能下地走路,住在亲戚家里暂时不能回学校去……我还没说完杨蒙就喊了起来:「啥?!
都一个月了还没长好?!
」
「呃……我长的慢……」意识到有了疏忽,我赶紧找补:「实在前两天都已经快好了,但一欠妥心刀口又传染发炎了,嗨,这闹得……」
「呃,那你、你可适合心点,自己把稳好了身体,别再传染了……」杨蒙一边抽咽着一边说。我顿时绝望到抓狂,这她也信?!
费了半天口舌,总算把她给劝住了。末了挂电话的时候,杨蒙几次再三叮嘱:「记得要给我打电话啊!
一定要常常给我打电话啊!
你不给我打,我就给你打!
」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拜拜……」我挂了线,看动手机无奈的想,往后没得清净了。总是以为自己被外边的天下忘却了,但只有当失落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天啊,连续忘却我吧。
天津,今夜请把我遗忘。
丁宁了杨蒙,我正要去睡个回笼觉,队长凶器忽然喊了一声:「好了,大家都整顿整顿,去洗把脸撒个尿,一会就要出发鸟!
」
「出发,去哪啊?」我看了看外边的大太阳,晨跑,不可能吧,这都几点了,再说本日周日啊。
「每过四个星期,到了周末就出去狂欢一次,这是基地的传统项目。」留着一侧偏分,长的有点像盛行歌手王杰的阿强推了推我:「在这一个月都憋坏了吧,本日哥们带着你出去好好玩玩。」
「呵呵,阿强,憋坏的是你小丫的吧,非要西毒一块跟你背黑锅。」小妖接过话,跟阿强打打闹闹,两个人发出一阵阵的淫笑。我看了看宿舍,乃昆不在,问道:「教练呢,出去玩的话打个电话叫他一起吧。」
「你还是算了吧,别招惹他了。他知道我们本日出去玩,昨天就一个人自己回市里了。」凶器耸耸肩,「别看教练不比我们大几岁,他可是老死板,连唱卡拉 OK 都不会,标准的清心寡欲型。」
听了凶器的话,我琢磨了一下,还真是,乃昆长那个样子,就不像是会唱卡拉 OK 的。
门口一辆破吉普车,一辆掉了漆的赤色夏利。我选了夏利坐,觉得小车更舒畅一些。阿强坐了副驾驶的位置,打开收音机听刮风行歌曲来,哼哼唧唧的。
「阿强,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听点有营养的东西?」凶器打着了火,发动车子道:「换个频道。」
没办法,教练不在的情形下,队长便是老大。阿强只能乖乖地调台,「呲啦啦」传出一阵杂音。
「喂,这位朋友啊,你说的情形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在每次行房的时候……」忽然一个清晰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如同一股清泉淌过我们的内心。凶器急速道:「唉,这个好,就听这个。」
「这不是津城夜话吗?怎么大白天的也放这个?」阿强一脸忧郁。
「重播呗,这节目火啊。」凶器一边陶醉的听着一边说。
这个节目我倒是第一次听,不由得有些好奇。听了一起,我也基本上明白了,这个节目便是几个生理咨询专家坐阵,然后有听众轮番打电话过来讯问,然后专家予以解答。提出的问题一开始貌似很新颖,但听得多了,也没什么新意,翻来覆去就那几样。不是我的短了,便是我的痿了,要么便是嫌自己韶光不足长。够长够猛的又嫌对方不和谐,反正便是逃不出床上那点事儿。还有个女的打电话过来说,一到最关键的时候她就忍不住大喊大叫,搞的街坊四邻都很有见地,问怎么办。我都疑惑这女的是不是托,假如我,打去世也不打这个电话。
专家的解答也乏善可陈,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不是说你压力太大,便是说你就寝不好,情形再严重一点的,就说你可能有点神经质,平时把稳保持好感情。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人家以为那玩意太短跟压力太大有什么关系,难道压力太大还能影响长度?马克思一早请教诲我们,物质决定意识。这帮专家很明显哲学学的不好,公开鼓吹唯心主义。
车子跑了半天,在津城夜话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到了目的地。好久没来市里,一下车还真以为是一片繁华,我举头一看,正对着我们的是「红川娱乐城」。
2
红川娱乐城。很大很派头,很好很和谐。
「娱乐」两个字,在中国可谓是博大精湛,原谅统统,无法言明,总之觉得统统不太良好的东西都跟娱乐有关。本来好好的一个词儿,「老师」臭了,「小姐」臭了,「娱乐」也臭了。
下了车,哥几个没有直奔娱乐城而去,而是进了阁下的一家川菜馆,胡吃海喝了一顿,光大虎自己一个人就干了六瓶雪花啤酒。吃过饭后,几个人带着全身的酒气,醉醺醺的进了红川娱乐城。
我们径直上了二楼的 KTV,要了一个大的包间。上了一桌子的瓜子啤酒花生豆,把门一关哥几个就飙起歌来。
这 KTV 的音响效果极好,立体环抱声出来的效果清晰醇厚。再加上哥几个都喝多了酒,劲头刚刚上来,不管是谁抢到麦克风都是高歌一曲,卯足了嗓子吼,震得桌子上的啤酒瓶子都嗡嗡直颤。
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个麦克风根本就不足用。为了抢麦都快打起来了。大虎好不容易抢到了麦,随后一首气势磅礴的《纤夫的爱》唱的让人热泪盈眶。那调跑的……切实其实太旷达了。
KTV 我在老家也唱过几次,实在还有点觉得。但看他们激情四溢的挥洒着自己的音乐才华,我只好坐在一边嗑瓜子。就这样唱了两个多小时,我耳朵都快被震聋了,凶器把麦克风抢去说道:「行了行了,你们都恰到好处啊。西毒到现在一首还没唱呢。」
「你们唱行了,我对这玩意儿没瘾。」我一边磕瓜子一边说。妈的,磕了两个多小时,我嘴都麻了。
「那弗成,一块出来玩,都得来两首。我这个当队长的,总得一碗水端平吧。」凶器把发话器递给了我。得,人家都说到这份上了,也不好拂了他面子,我便接过了麦克。
「唱啥歌?」坐在点歌机阁下的小妖问。
「我自己来吧。」我坐了过去,翻着菜单。翻到「M」字母开头的一栏,猛的眼睛一亮,没想到,竟然有这个组合的歌?
怎么可能,难道他们出名了?不过菜单上只有他们的两首歌,我苦笑一声,明白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出名,这两首歌,或许只是在网络上略有传播罢了。没想到这家 KTV 收录得还挺全。
我点了一首「梦机器」的歌。名字叫做《青锋》。
「梦机器」是一个组合,两个人,一男一女。那女的是我表姐。她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组建了一个电子乐队,一贯梦想着有登台演出的那一天。当时我上高三,表姐知道我文采不错,平时颇能写点东西,便让我帮她写点歌词。在她的一番彩虹屁吹捧下,由由然的我自然效犬马之劳,个中就包括这首《青锋》。表姐后来给我听了那些歌,很不错,但他们却一贯没有出名。
舒缓的音乐响起,带着一丝空灵的中国风。我看着屏幕,唱了起来。
昼夜想要解脱,
却终不为过。
一千年的韶光,
仍预见不到结局的寂寞。
你只要逐步拜别,
你不要再声声唤我,
我今日淬火,
不得触摸。
山下剑炉泉水,
身边无数过客。
流转人间,
多少失落足又成千古差错。
青锋流动,
百步无形,
我身在地狱却有一念之间,
铺就梅花喷鼻香墨。
……
一歌唱毕,全场竟然鸦雀无声。哥几个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半晌小妖才问道:「这是谁的歌。这么好听,之前怎么没听过?」
「小乐队,不出名。」我淡淡说道,装逼于无形。
「西毒,再来一个。还有一首呢,唱了吧。」不等我说话,小妖就自动的帮我点了下一首。
是「梦机器」的《诸神混乱》,KTV 里一共就这两首歌。当然,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我写的。
不要再看流沙,
指间流去尽是繁华。
祈求所有的保佑落下,
烽火顺着帷幕轻滑。
统统梦幻,
统统泡影,
往事犹如隔夜陈茶。
西域洞窟斑驳壁画,
塞外佛像万仞山崖。
玄奘从这里走过有夜郎自大,
诵经无数口号抚平参差狼牙。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吧,
芸芸众生灵魂在此,
万物清明,
统统如他。
……
唱完之后,哥几个迷瞪着眼,一幅意犹未尽的样子。凶器愣了半晌说道:「不对啊,原来怎么没听过这歌?」
「真理总是节制在少数人手中。」我放下了麦克风说道。
短暂的中国风带来的一阵清新空气很快就被接下来的喧华淹没了,他们接过麦克,连续没心没肺的吼着,一副舍我其谁天下独尊的样子。当我嗑到第五包瓜子的时候,他们终于发泄完了压抑的音乐希望,一个个知足的走出了包间,只留下一桌的空酒瓶和一地的瓜子壳。包间看上去彷佛被壮汉撕扯过的少女一样平常可怜。
我原来以为本日的娱乐活动要结束了,他们又连续上了五楼。五楼的门口上写着「红川洗澡。」
我们刚一走进来,急速就有一个四十多岁,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采犹存的女人过来呼唤,激情亲切大方,不卑不亢,很明显受到过良好的职业性演习。
「何姐,有一阵子没见了,都快想去世我了。」小妖这家伙看起来跟这女人很熟,还顺便在她腰上摸了一把。
何姐嗔笑着拍了一下小妖,转身说道:「哥几个先坐着,我叫几个小妹陪你们说说话。」
大家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环视四周,装饰的很俊秀,相称有品味,墙上还挂着半裸出浴的仕女图和古典油画。我忽然明白了,这才是本日「娱乐」的重头戏。我坐在那里,忽然没来由的一阵紧张。
3
「洗澡」,恐怕是个男人都知道什么意思。我没来由的一阵发虚,转头看看他们几个,却是司空平常,一个个喜笑颜开,谈笑风生的。
过了好大一下子,五个小姐才从门口呼啦呼啦的走了进来,站在了我们面前。何姐随着走了过来,带着极不自然的笑颜说道:「哥几个,先让这几个陪你们说会话。」
我举头一看那五个小姐,就明白何姐为什么笑的那么不自然了。这五个姑娘一溜站开,容貌平平,毫无姿色,就彷佛在路边等着找事情似的,看上去让人没有任何希望。其他四个还勉强凑合,只能用通俗俗通来形容,也便是一样平常人。而有一个却长的让我终生难忘。
这姑娘个子不高,脸盘不小,怎么瞅怎么像凤姐。她穿着一双造型夸年夜的高跟鞋,站在那里瞪着一双去世鱼眼毫无表情的瞅着我们,就像在马路边上瞅着一堆发干的狗粪。她不笑还好,随后的勉强开口一笑,大嘴叉子差点咧到了耳朵根,让我险些当场晕过去。
这一次的非正式会晤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以至于后来凤姐横空出世,我都疑惑是不是这姑娘又重出江湖了,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何姐这么干练的女人,这个时候也显得极不自然,站在那里一脸不好意思的讪笑着看着我们。就算不说,我也知道,这肯定是他们娱乐城压箱底的角色,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拿出来示人的。
小妖站了起来,神色丢脸的彷佛刚吃了屎一样。他带着几分愠怒:「何姐,怎么个意思,恳切拿兄弟几个开涮啊?」
「不是,不是,小妖兄弟,你先坐下,听我说。」何姐赶紧劝小妖坐下,陪着笑脸道:「是这样的,本日周末,来玩的客人也多,小姐们都搪塞不过来,确实有点紧张。二炮哥带了几个兄弟来玩,就要了十来个小姐陪唱,你看,我们谁也不能得罪不是……」
「哪个二炮哥?」凶器皱着眉头。
「二炮哥,塘沽的刘二炮啊,洋货市场都是他的场子。」何姐说道。
「我还以为哪个二炮呢,原来是这家伙啊,他现在也是哥了?」凶器冷哼了一声,问道:「他在哪个房间?」
「二楼,206,KTV 包间。」何姐赶紧答道。看来她对这个二炮哥也是心有不满。
「这家伙当时跟李哥混的时候,也便是一个跑腿的杂碎,没想到一年多不见,他现在还得瑟起来了。」凶器转头说道:「小妖,西毒,阿强,你们三个下去一趟瞅瞅。」
「哎哎,小妖兄弟,有话好好说,可千万别打起来啊……」何姐忙不迭的在后面叮嘱道。我转头看了她一眼,心道干哪行都不随意马虎啊。
阿强二话不说,一脚踹开了 206 包房的门,「哐当」一声巨响。那个正搂着一个小姐,捧着麦克风陶醉忘我的歌手陡然愣在了那儿,一脸怔怔的看着我们。刚刚还繁盛热闹繁荣的包间一韶光鸦雀无声,都被我们溘然的出场给震住了。一个混混的手一边在怀里的小姐的胸上摸着,一边举头吃惊的看着我们,样子奇怪至极。全体房间里只有音乐的伴奏还在响着,是任贤齐的《心太软》。
「他妈的,你谁啊,想去世啊!
」那个摸着小姐胸的家伙第一个反应了过来,很不宁愿的拿开了他的手,站起来指着我们骂道。
我迅速的扫视了一下这个包间,有六个男人,分散的坐在周围一圈的沙发上。但在包房里的小姐却有九个,均匀一个人能占俩不到,占一个有点多,我不禁为他们怎么分而在心中迅速的打算了一下。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瞎操心,在最中间的一个沙发上,一个秃顶的家伙坐在那里,他旁边一共搂着三个小姐。我轻呼了一口气,这样一来就好算多了。
我们三个踹开了门,站在那里,也不说话,就冷冷的盯着他们。对方「呼啦」一下都站了起来,有两个已经把啤酒瓶抄在了手上,一边朝我们走来一边骂着:「妈的,从哪蹦出来的,找去世是吧。」
「等等……哥几个混哪的?」那秃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制止了他部下的动作,推开阁下的两个小姐向我们走来。
我可以肯定这个秃顶便是二炮。老大便是老大,在一群小弟中间果真显得鹤立鸡群,气度非凡。他踱着将军步走到门口,带着一脸狞笑:「你们混哪块的,我的地方也敢随便踹,找练来了是吧,活腻歪……哎呀,强哥,这不是强哥嘛?!
」
态度陡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二炮急忙转身,对着他的小弟叫道:「关音乐,关音乐!
」随后刚过高潮的《心太软》戛然而止,包间里彻底清净了。二炮再转过身来,已经是换了一副嘴脸:「强哥,哎呀,还有小妖兄弟,这位是……呵呵,你们怎么也来玩了?」
他身后的小弟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尤其是那两个手里拎着啤酒瓶子的,站在那里好生尴尬。
「本日周末嘛,兄弟几个没事就过来玩玩,没想到恰好遇见二炮哥也在这里高兴,真是巧啊。」阿强笑着答道,但话里藏针。
「呵呵,高兴,高兴。」二炮陪着笑脸道:「三位一块坐下来玩会,唱几首歌?我让做事员再送箱啤酒过来。」
「不玩了,楼上的兄弟们还等着呢。可是本日没有小姐,他们几个都在那发火呢,我得赶紧上去……」阿强说着,又故意朝包间里扫了一眼,「哎呀,二炮哥,你这里小姐倒是不少啊。」
「陪唱,陪唱,搞搞气氛嘛。」二炮也是明白人,急速就知道了什么意思,「便是多叫几个过来热闹一下。呵呵,呵呵,正想让她们上去呢。」
「那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妨碍二炮哥高兴了,你们接着唱。我本日喝的有点多,欠妥心踹了你们的门,二炮哥,不好意思哈。」阿强拱手说道,算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
「好好,等会儿下来玩玩,唱几首歌啊……」二炮满脸笑颜的目送我们离开。我走在末了面,隐约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对话声。
「炮哥,为什么不叫我们动手?」
「动手,动你妈了个逼!
你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他们随便一个就能放倒你们一屋子……」
4
虽然我很不喜好这种从别人手里抢女人的办法,但至少这样能让那个跟凤姐神似更加貌似的小姐快速从我面前消逝,于是我就默认了。
没过一下子,八九个小姐款款走了上来,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这几个好多了,完备符合期待。刚才在我们面前的那五个小姐已经消逝了。何姐说,把她们派到下面陪二炮唱歌去了。我忽然对二炮哥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他们每人挑了一个,搂着进去 happy 了,末了给我剩了一个看起来年纪比较小的,还保留着一丝青涩。我原以为他们是照顾我,后来阿强给我说,来这里是找乐子的,不是找感情的。挑小姐,就挑那种风月老手,技能闇练。瞥见略带羞涩的,肯定是刚入行不久,玩不起来,到了关键的地方,还得你教她。图啥啊,费钱来这里给他培训员工来了?
那小姐领着我,逐步穿过一条在昏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无比神秘而且深邃的走廊。走廊两边挂着许多油画印刷品,都是一些文艺复兴期间大师们所作的裸体画,男的肌肉健硕,女的皮肤白皙,充满了力与美的表达,让人看去顿生艺术敬仰之情。我忽然创造,洗澡城里是悬挂裸体油画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你想探求一些文艺复兴的气息,还真得来这里好好走走。
她在一扇门前停下了,轻轻推开,带我进去。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套间,散发着柔和的赤色灯光。气氛温馨,干净整洁,从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的紧张感情。
我坐在床边,装着若无其事的翻看着床头的「爱人」杂志,刚刚平复的紧张感情忽然又涌了上来,乃至能够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那小姐忽然甜甜的问道:「师长西席,你要不要先洗个澡?」
听这职业性的声音,看来以为她青涩还真是误会她了。势成骑虎,我只能说:「好。」
我正站在淋浴下面冲澡,毛玻璃推拉门忽然开了,那个小姐探了一个头进来。我急忙下意识的捂住了自己的要紧部位:「你干什么?」
话一出口,我就尴尬的想钻进地缝里去。都到这儿了,还能干什么?
「帮你沐浴啊,给你搓搓背。」小姐看我这样问,也是一愣,没有进来,就在那露着一个脑袋,看上去跟聊斋似的。
这太尴尬了,我急忙道:「不用了,不用了,我这就洗完了。」
我匆忙擦干身体,裹着浴袍走了出来。屋内的灯光更加暧昧,那个小姐就躺在床上,只穿着亵服等着我。在柔和的灯光下,她的身体仿佛一座宝藏,里面蕴涵着无数想让人探究的秘密。我的脑袋「嗡」了一下,仿佛被瞬间击中。
「师长西席,刚洗完澡好喷鼻香哦……」她坐了起来,帮我缓缓褪去身上的浴袍。当她靠近我的时候,我闻到了她身上所散发的那种独特的女性气息。那是我第一次跟女人如此亲密的打仗,眩晕感彷佛海浪一样一直的拍打着我的神经。统统有关人生、命运的思考都在那一刻停滞了流动。虽然只是一个大略的脱衣动作,我却浑身都战栗了一下。
「师长西席,你冷吗?」女人停下了正在脱我衣服的手。
「不冷啊,怎么了?」
「那你身上怎么起了一层鸡皮?」
我低下头看去,果真,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汗毛全都竖了起来。衣服还没脱完呢就激动成这个样子,真是让人汗颜。我急忙说道:「哦,哦,刚洗完澡,是有一点冷。」
良久良久往后,我还记得那种觉得,那种浑身一个战栗的舒爽感,从此往后再也没有体会过,不管用什么办法。或许,人生只有那么一次体验这种觉得的机会,可惜的是,我却把它送给了一位只有一壁之缘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
女人看到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又重新给我裹上了浴袍:「那你再暖和一下吧。」接着,她转过身,手伸到背后去解自己的亵服。
「等,等一下。」我竟然阴差阳错的捉住了她的手,这个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师长西席,怎么了?」她回过分问道,一脸迷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在她即将要解开自己亵服的一瞬间,我脑海中忽然跳出了阿果的身影。她坐在那里,抽着烟,精细的面庞如同一个堕落的精灵。紧接着,杨蒙的身影竟然也跳了出来,那个晚上,她在路灯之下瞩目着我,眼神中流动着彩色的哀伤。这两个女人的身影如此不合时宜的涌现,恰如冰山一样平常瞬间熄灭了我所有希望的火焰。
我抓着这个女人的手,迟疑了一下道:「不用解开,就这样就好。」
「哦,原来师长西席喜好这样的啊,那也好。」女人松开了手,转而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单子递给我,「师长西席,你看一下,喜好先玩哪个?」
我接过单子扫了一眼,全是一些「冰火、毒龙、漫游」之类的项目。我虽然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这些玩意儿详细不理解怎么个玩法,但想想也能大体估摸出来。我放下了那张单子,说:「我不喜好这些……这样吧,你陪我说会儿话行了。」
话说完,我自己都以为有点辜负人家。
「师长西席,难道你对我不满意吗?」她有些委曲,「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我会再换一个小姐过来的。」
「不,不是,我本日确实有点……太累了。」我随口编了一个情由。
女人急速错愕起来,带着哭腔说:「师长西席,你别这样,等一下这张单子上的每一项还要你具名呢。你假如哪一项不满意,领班还要扣我钱呢。你要这样的话,我这个钟就白上了……」
「满意,满意,我一会都给你签上字行吧。」我这人就见不得女人急,忙说道:「我不会让你被扣钱的,只是,你就陪我说会话行了,本日我没心情。」
女人这才止住哭腔,拢了拢头发看着我:「说话?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聊谈天呗。」我尴尬一笑。
「那你趴下,我给你推拿吧。」女人披上了一件外套,语气中带着一丝幽怨,彷佛我没有上她,反而欠了她多大情似的。
我趴了下去,浑身放松,女人开始在我身上忙活起来,很舒畅,相称受用。我抱着枕头问道:「你原来学过推拿吧?」
「原来跟过一个松骨的师傅。」女人答道,手上并一直下。
「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开始没话找话。
「你叫我 25 号就行了。我在这里是 25 号,下次来还记得找我。」
「嗯……25 号,听你口音,你是南方人吧?」
「贵州的,穷地方。」
她的回答让我想起了跟阿果的第一次对话,她也是这么回答我的。我突发奇想:「问你个人,叫阿果,你认识不,也是贵州的,你们老乡。」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不白问嘛,她干这个的,怎么能认识阿果呢。
「阿果啊?我认识她啊!
」25 号一边用力拧着我的腰一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