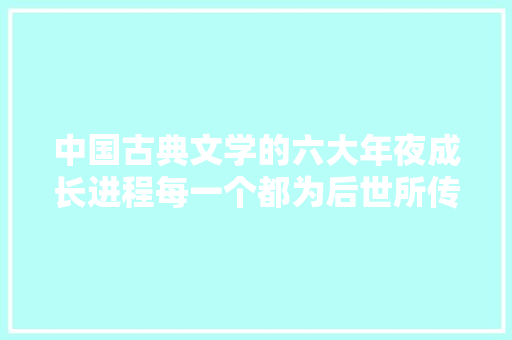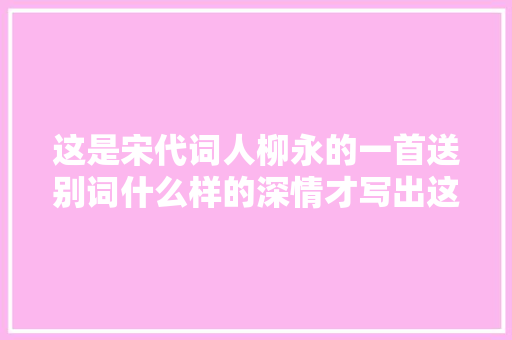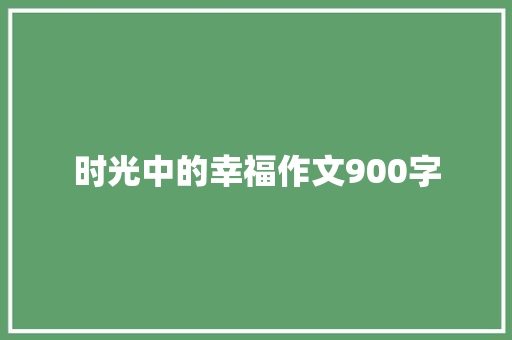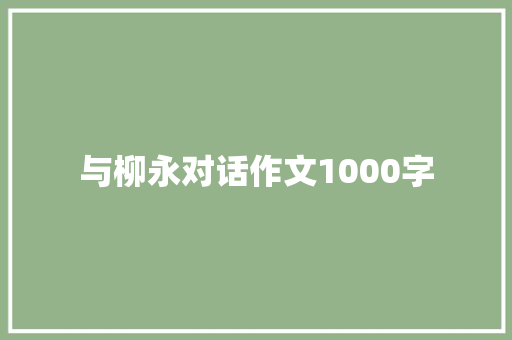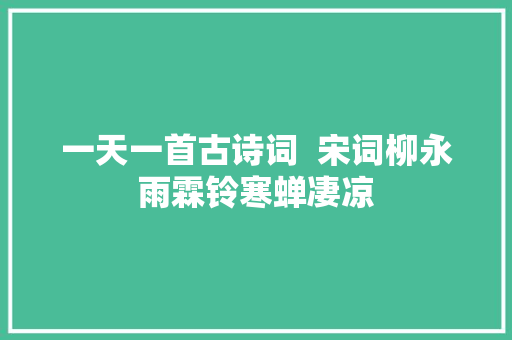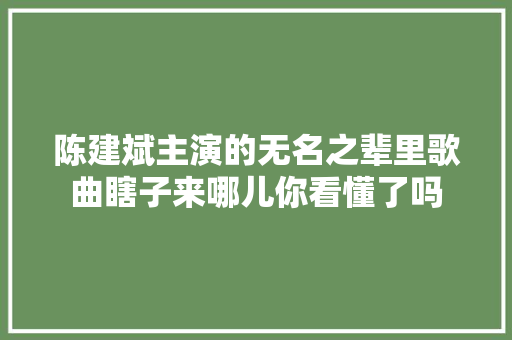谢稚柳《春后西湖》
李清照在《词论》里提出“词别是一家”,主见守卫词的文体特色,不赞许苏轼以诗为词的作法。宇文所安的专著《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可以看为难刁难“词别是一家”的延伸思考。他强调“苏轼确立宋词写作分水岭”这个学术共识,又把关注点扩展到写作手腕之外,即,成为文学文体之前,词作为一种演出实践,若何渗透在普通人的娱乐生活和官场社交中。从11世纪到12世纪初的百余年间,词的紧张功能并非个人言志,更不以文本传阅,作者、歌女和不雅观众共同组成的被暧昧和激情包围的小天下,组成完全的词的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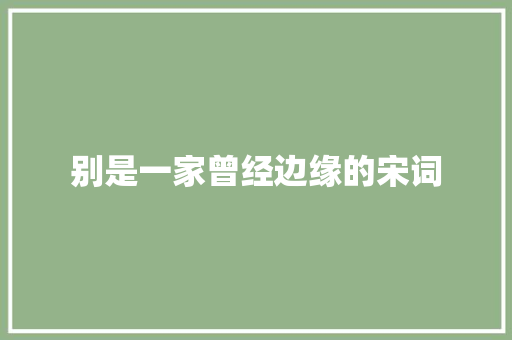
早期的婉约词即便不被视为引人堕落的违禁品,至少是边缘的文化产品。宋代在政治、道德等各种层面严格寻求统一性,不一致的个体的感想熏染和声音不被许可涌如今约定俗成的代价体系里。高官士大夫的本职是守护公共代价,于是,填词成为他们私生活里的秘密,许多位高权重的男性反复书写失落落的爱情和瞬息间的悲欢,那些被一体化的系统排挤出的剩余物,既是被唾弃的话语,也暴露了严苛的道德空想若何辜负了人性的需求:自上而下认可的代价体系和世俗实际履历中运作的代价体系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缝隙。
爆款词作者柳永和欢场舞台
关于柳永,最广为人知的一则掌故是说他言行轻浮,为仁宗厌弃,逐他“且去填词”,他从此纵情欢场,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则传闻涌如今柳永去世50年后,被证明是编造的。它的涌现和流传,佐证了“填词”不被视为士族的正途,浅斟低唱的词不符合宋代的时期精神,被流放在道德空想之外。
柳永的浪子形象,也是以讹传讹。柳永在史估中险些没有留下痕迹,学者们无法考据他的确切生卒年份,只知道他在11世纪的30年代考中进士,有过一段宦游经历。他写过许多羁旅行役的词,也提到对踏入仕途的仇恨,比如名篇《雨霖铃》,长亭骤雨,兰舟催发,烟波暮霭这些详细的细节催化了伤离去的痛。柳永创造过太多“相看泪眼”或“免恁牵系”的情境,但并没有充满说服力的考据证明这是作者的自传声音,乃至,作者柳永和词里的阐述者,不是一定合一的。自12世纪往后,读者所知的柳永,来自他写的慢词和长调,把作者生平和词作的内容勾连起来。这很可能是严重的误读。在柳永的时期,讲述作者的经历和想法,是古典诗歌的功能。词是舞台演出的半成品,词的文本供歌女演唱,不以书本的形式传播。
宋词分为慢词和小令两个大类。大部分小令创作或演出于高官们的社交宴会,常常是在户外助兴。慢词是封闭空间里永劫光的完全演出,是娼寮瓦舍的欢场里特有的,不雅观众的希望工具是歌女以及歌女在演唱中制造的幻象。
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柳永塑造了一个放浪形骸的文人,沉溺于风月场中的恋爱游戏。他扮演了一个伤情者的形象,曾是声色犬马天下里的玩家,浪掷了青春,错过了爱人,带着仇恨,回望逝水年华。“随意率性怜娇态”或“敦促少年郎”这样喷鼻香艳的想象,很可能是为了娱乐不雅观众而虚构的场景。他的这些慢词在汴京和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里,被有名的歌女们演绎得恰到好处,演出大受欢迎,他成了那个时期的爆款作者。
柳永书写的天下里充斥着个人的缠绵,陈设女子对爱情的渴望,展示男子的热望,他塑造的男女关系,在他的时期前所未有。歌女唱着他的词,演出思慕爱人、顾虑爱人的痴心女子,成为现场男性不雅观众的集体倾慕者。这个场景蕴藉地指向高官家宴现场所不能容忍的权力关系翻转。歌女被普通不雅观众追捧,形成市民生活里的代价体系:歌女演出幻象,出售幻象,金钱和权力追逐购买幻象,却不能节制她,更不能买断她。洞悉了成年男女天下秘密的女子们演绎柳永创造的那些不愿定的、繁芜的情爱关系,激起不雅观众希望,心潮翻滚的不雅观众也明白,歌女的深情只是幻觉,游弋在“至心话”和“看似至心话”之间——这种关于“不愿定”的默契和共识,是词作和演出的双重主题。低微的女性在不愿定关系中用柔弱的办法守卫自己的感情和意志,《瑞鹧鸪·宝髻瑶簪》便是对这种情态的生动呈现。柳永虚构了一个名伶,一曲阳春值千金,王孙帝子争相追逐,但是姑娘回眸,她心里存着“缘情寓意,别有知音。”
在这个天下里,柳永是制造游戏的人,也深陷个中,被其所羁绊。他因私德被非议,但“正统”奚落他,很可能是由于他颠覆了中国传统中关于爱情与希望的书写。柳永词作里的一部分女子,节制了亲密关系的主动权。“盈盈背立银釭,却道你但先睡。”《斗百花》里这个天真的女孩,她抗拒作为希望工具的不清闲,谢绝被看。《菊花新》的少妇风情万种,不仅“放了残针线。脱罗衣、恣情无限。”更会留取帐前灯,好让少年郎时时看自己的娇媚容颜。她主导着那个夜晚,不羞于暴露自己的希望,她渴望被爱人瞩目,也设计了“被看”的办法。最出名的那首《定风波》塑造了一个格外果决的少妇,“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这样的深闺思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多的,但这个不一样,她吸取了教训,决心不做被动的等待者,并付诸于行动,“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这可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而是驯服丈夫,让他屈服她的意愿,在日常的家庭场景中陪伴旁边。
柳永为慢词打开新的话语场,由于他,女性在盛行文学中争取到有限的自主性,即便是男性作者想象的自主,这仍旧冲击乃至颠覆了精英文学塑造的悲观女性。正好是这点,造成柳永的名声急转直下。
在宋代官场网络里传播的词
柳永的另一则著名传闻是他曾求问晏殊:“我们都填词,为何我被天子厌恶?”晏殊回他:“由于我从不写‘针线闲拈伴伊坐’这种词。”这个段子传开时,柳永已经身故,他和晏殊很可能从未谋面,这则传闻是后人附会的。晏殊写过许多与“往事旧欢”有关的词,说话之露骨,愈甚于柳永。上述这种轶闻的产生,揭示了在官场网络中作为社交办法的词,和市民社会里消费的词,是不同的。
晏殊15岁时考中进士,有神童隽誉,他受仁宗看重,生平身居要职,在11世纪上半叶权倾朝野。晏殊的家宴有盛名,宴会现场凑集了宋朝政坛最有权力的男人们,大多是位高权重的士大夫,纵然偶尔熟年轻男子受邀,但这群人的年事在30至60岁之间,不会有少年郎。他们在酩酊时,听到晏府家班的小歌女们唱起缠绵的词,这让他们有一瞬间阔别仕宦烦忧,被勾起心底的柔情,乃至可能因此落泪。
晏殊在宴席中写过一首《浣溪沙》,挽留一位想要提前离席的高官:“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匆匆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宽别恨,系人情,寥寥几个字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失落恋”,酒精和少女的歌声让那位政务缠身的官员想起在私人生活贪恋、然而不被公共代价认可的东西。在花园饮宴的特定情境里,词伸开了一个疏离于男性公共天下的结界,它是感性的,专注于自我,它把大一统的空想短暂地排斥在外。
国家,功名,家庭,都淡去了,身居高位的男人们少焉之间沉溺于惆怅的柔情,早已消散的爱情和不在场的情人以温顺的力量瓦解了他们的年夜志——这显然和社谈判定俗成的等级不雅观念与代价体系相悖。而晏殊特殊的才能在于,他的小令掌握了躲避主义的尺度。另一首《浣溪沙》有这样的下半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面古人。“空念远”三字微言大义,他暴露了躲避任务的渴望,忧思出息,但逃逸的方向不是向过去寻求虚无的抚慰,而是接管此时此刻的诱惑,怜取面古人,活在当下。
词的演出属性走向闭幕
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或第八个儿子,宋代的历史文献中险些没有留下关于他平生的记录,对他的生卒年份的考据,来自晏氏家谱——他生于1038年,卒于1110年,是苏轼的同辈人。
晏几道和苏轼是北宋文化里耐人寻味的一组对照。苏轼拥有激烈的脾气,且随时会在作品中展示,晏几道则用尽办法在写作中掩蔽锋芒。苏轼改造了词的写作,晏几道仿佛留在父辈迷恋的小令传统里,用固执的守旧主义呵护旧日风格,但他在自己的时期里写出了新的东西,用新的修辞给小令的迂腐的文体注入了新的可能。末了,晏几道对小令的改造,和苏轼的“以诗入词”,殊途同归地闭幕了小令的致幻和演出属性。黄庭坚是晏几道的好友,他敏锐地意识到:“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之风耳,罕能味其言也。”众人阿谀晏几道子承父风,实在很少有人读懂他。
晏殊写《红窗听》,开始于“记得喷鼻香闺临别语。彼此有、万重心诉。”晏几道的《玉楼春》结束于“忆曾挑尽五更灯,不记临分多少话。”父子俩在回顾的主题迷宫里分道而行,晏殊一次次在酒酣时写下,“我记得。”而晏几道总是踟蹰的,他说:“我忘不了分别的场面,却想不起许多的细节。”他授予“往事旧欢”这个词作的永恒母题以新的写法——当下的欢愉触动影象的开关,韶光变形,虚实之间,原形已经模糊,逝去的光阴在言语中被再现,被重修。
李清照批评小晏的词“苦无铺叙”。她有底气作这判词,论意识流的小令写作,没有人能比肩她的《南歌子》——“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景象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以景入情,情理清晰,而韶光的痕迹历历在目,正如宇文所安惊叹的,这样的词大略又完美。小晏被李清照挑剔是该当的,但他的弱点造诣了他的特点:在交错的韶光线上,梦和影象的片段相互渗透,这是蒙太奇快照跳接的恋爱史。
这首《鹧鸪天》可能是晏几道最让民气碎的作品:“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次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韶光在此刻和过去之间飘来荡去,词的阐述者在宴会上相逢阔别的旧情人,思绪把他带回“拼却醉颜红”的年华。当年的舞和当年的歌嵌在绵长的光阴里,一瞬间的影象融入川流不息的韶光。他们分开了许久,他在影象里复刻相逢相遇的场面,反复地在梦里回到爱情开始的时候,在梦里探求他渴望的人。直到命运终于让他们相逢,他却夜不成眠,提灯看她,又不敢看。这里没有夙愿得偿的宽慰,反而被双重的失落落笼罩了,韶光过去了那么久,他徒劳地在灯下探求梦里的她。他企图重历的旧人和往事,是无法抵达的目的地,那是已经无可奈何失落落了的天下。
晏几道执着于对过去的完美重复,而这是现实无法作出的补偿,那只能是影象,梦境,或酒醉时谵妄的想象。这些在意识中再现的场面,总会在复苏时散去,以是他写下的一字一句,是关于失落去,关于幻梦的破灭。他和他父亲的词,打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天下。晏殊的《破阵子》写曲终人散后的女子:“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晏殊家宴上的那些中老年成功男性,或多或少在年轻时有过“求得人间成小会”的经历,那些女孩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过客,当他们功成名就时听着小歌女唱着“言不尽、千万重”的深情,这些被倾注了强烈情绪的词在演出中实现完美的幻觉,仿佛失落落的青春往事能被寻回、被填补。晏几道反复写着“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一夜梦魂何处,那回杨叶楼中”……这样的词是一种“元演出”,它们关于再现本身,揭破了小令的致幻机制——大概梦里醉里能实现旧日重来,但统统究竟是回不去的。于是,技艺纯青的歌女越是明白地唱出这“求不得”的痛惜,她的技艺越是被摧毁,由于这种技艺制造幻象的力量被瓦解了。
至此,词的演出属性走向末路,它作为文体蕴藏的潜能,将由苏轼开启,苏轼用他独一无二的措辞辨识度,让词不再是原来的词,不再“只是一首歌”。(柳青)
来源: 文申报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