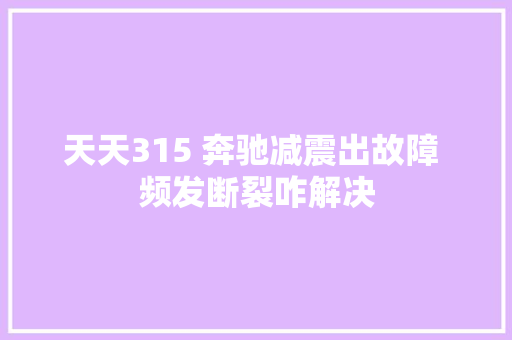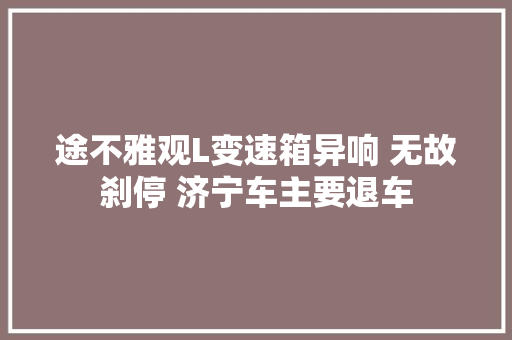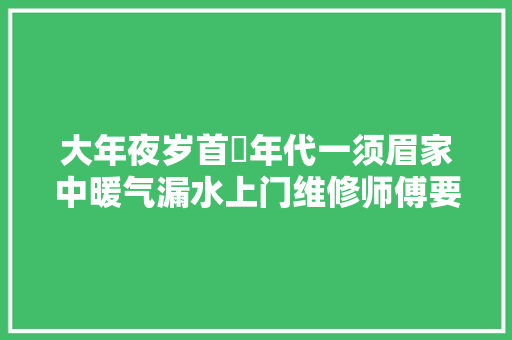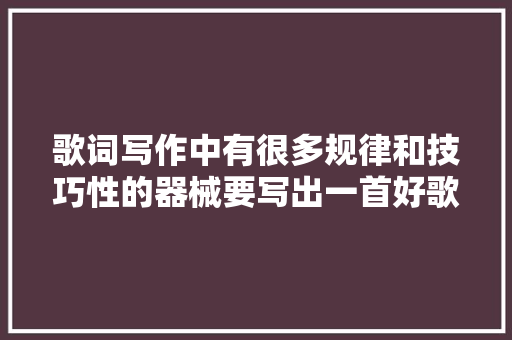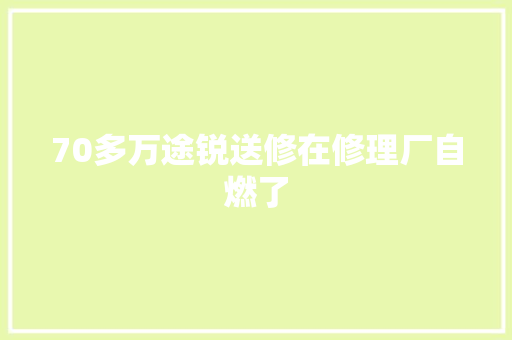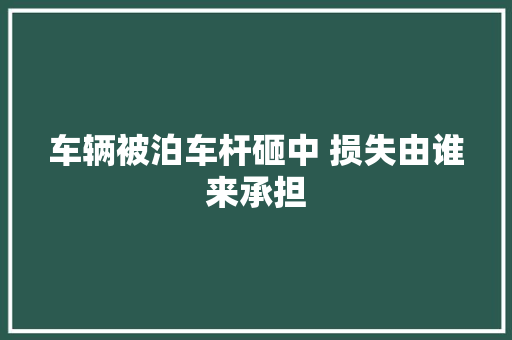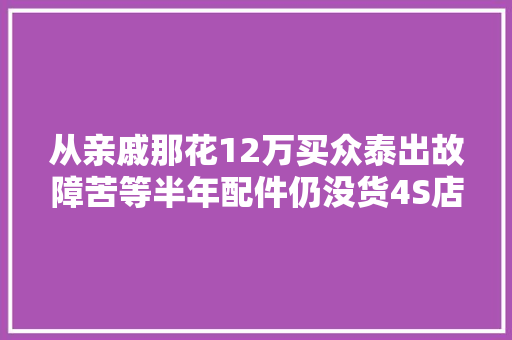这则题为《相逢》的“眇小说”出自布莱希特《K师长西席的故事》系列,主人公K师长西席是一个面孔模糊、个性暗藏的“思考者”。它的意外结尾让我遐想到博尔赫斯对阿谀话的反应。在辛辛那提,当一个崇拜者对博尔赫斯说:“愿你能活一千岁!
”博尔赫斯这样回答:“我高高兴兴地愿望着去世去。”
无论是布莱希特虚构的K师长西席,还是大作家博尔赫斯,都对日常套话持有一种当心。博尔赫斯长期身处失落明带来的巨大孤独中,他的回答透出对死活的超然;K师长西席发出的“哦”则掩蔽着明显的不悦,他竟然“神色发白”,使我这个读者也愕然。看来,“您一点儿也没变”这句阿谀话在K师长西席那里已掀起了一场生理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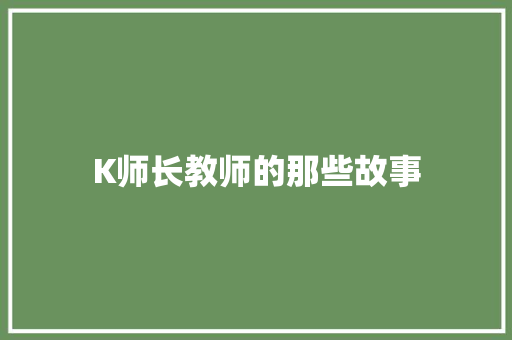
再一想到,布莱希特是那么钟情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易经》,视“变”为天下的实质,执迷于“变之辩”。而《K师长西席的故事》最早出版韶光是1949年,彼时,布莱希特已结束多年流亡生活,回归战后的欧洲。我猜想他会有类似“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心境。那么,“您一点儿也没变”这样的话,与其说是礼节性的安慰,不如说是轻巧的混账话,乃至是慢待的侮辱。毕竟,经历了纳粹和二战的肆虐,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幸免于“变”。人们该当觉察“变”,反思“变”,而不是对“变”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在另一则《成功》里,布莱希特借K师长西席之口揭示了内在改变与容颜气质之间的关联:
K师长西席瞥见一个女演员经由,就说:“她很美。”他的陪同者说:“她最近得到了成功,由于她长得俊秀。”K师长西席很生气,说:“她俊秀,是由于她得到了成功。”
你瞧,K师长西席对付陈词谰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这一次,他绝不客气地匡正旁人的缺点归因。在K师长西席看来,女演员的美,是成功带来的自傲的副产品,而非成功的缘故原由和手段。人们总喜好把他人的(尤其是女性的)成功归由于外部成分。
仅读这两则,我们就可以创造,所谓的K师长西席故事,是一些没有情节、类似寓言或警句风格的散文。它们实在是布莱希特在戏剧创作期间的笔墨小实验,一种不雅观察和思考的即兴记录。布莱希特去世后,瑞士苏尔坎普出版社存心搜集了这些创作韶光跨度达三十年、散落四处的纸草残片,在1971年出版了87则K师长西席的故事,2000年又弥补了15则。这些“故事”,短的仅一行,长的也不过三页,大多不到半页。我翻遍整本集子,创造里面既无奇闻轶事,又无风趣诙谐,乃至连K这个人的来龙去脉也未提及。布莱希特大概是故意隐去了统统详细化的人物特色,只让K作为一个抽象人物出场。K师长西席全名叫考伊纳(Keuner),布莱希特的至交本雅明考证过这个名字,创造“Keuner”在布莱希特家乡奥格斯堡一带的方言里和“Keiner”(无人)同音。这么说来,K师长西席是一个谁也不是,谁也不像的人,岂不正是一个“思考的幽灵”?你瞧,旁人的只言片语便能扯出他的一段议论:
K师长西席常常听人夸奖某位任职良久的官员“不可或缺”,“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他怎么个不可或缺法呢?”K师长西席听闻此言,不禁恼火。“没有他,全体机构就会无法运转”,称颂者们答。“如果机构没有他就无法运转,怎么就能称之为一个好官员呢?”K师长西席说,照理,他有足够韶光来管理他的机构,使得机构没有他的存在也能正常运转!
这些年他究竟在干什么?让我来见告你们吧:“他在打单!
”
随着“打单”一词的凭空砸地,这则名叫“一个不可或缺的官员”的故事便戛然而止。我难免不免以为这位K师长西席有些故作“出语惊人”状。但转念一想,则暗暗心惊!
K师长西席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位官员和同寅之间的关系。这位官员“打单”的是什么?是众人对他的依赖和倚重?在任劳任怨、殚精竭虑的外表下,是否隐蔽着唯我贤良的自大,顾盼自雄的得意?我遥想到王熙凤,凤姐这般喜好揽权弄权之人,在精力不济之时,也懂得适度放权,委托探春,颇有几分自知之明和识人之明。这位官员使全体机构寄托于一己之身,其他人就此失落去磨炼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在众星捧月,交口称道的景象下,难免隐蔽着怨言和危急。但让K师长西席恼火的,何止是这位官员的作风,他同样不满周围那些称道者。跟风赞颂实在源自思维的惰性和从众生理的领导。人们谢绝寻思,并天然地排挤质疑者。
《K师长西席的故事》问世以来,欧洲的布莱希特研究者评价不一。夸奖者认为,这是当代德语最好的散文,表示了布氏简练优雅、长于讽刺的文风,读者可管窥布莱希特的哲思天下,尤其是他对人类的社会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的不雅观察。批评者则认为K师长西席系列未能表示大师水准,K这个角色有一种“思想者”的自以为是和矫枉过正。实在,即便最精良墨客的笔端也会流出粗糙的诗句,最伟大的作家也难免出产一两部平庸之作。《K师长西席的故事》既有珠玉,又有沙砾。我这些年倒是把阅读K师长西席的故事当作一种“思维体操”,有时读得一知半解,如坠云雾,却也不乏柳暗花明的愉悦,乃至醍醐灌顶的欣喜。我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评价:《K师长西席的故事》并非那种供应伟大教益的哲学著作,说到底布莱希特也不是哲学家出身,但也绝非那种唾手可得的“心灵鸡汤”。它们犹如德国冬天的云杉,枝叶闪烁着灰褐色的理性。
我个人尤其喜好读有关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篇章,比如《两座城》:
比较A城,K师长西席更喜好B城。“在A城,”他说,“人们爱我;但是在B城,人们待我友善。A城人总是帮助我,B城人则须要我。在A城,我总是被请上饭桌;在B城,我被请进厨房”。
K师长西席的两座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交流关系。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道,城市的秘密在于它是发生无数交流关系的地点:“货色的交流,话语的交流,希望的交流,记录的交流……”在A城,K是交流关系的沾恩者。他被众人爱着,时候知足着,无须付出就能轻易得到。单向的交流模式隐蔽着一种危险——使人终极成为关系的附庸或贡品,沾恩者的终端是“被抛弃者”。对付K而言,倘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内核,将导致思想和创作能力的衰退。B城则为K供应了一种平等交流的可能,他和B城之间发展出一种友善的、康健的关系。本雅明曾经在《布莱希特诗歌评注》里写道:“关于友善我们找出的第三件事,是它不会肃清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而是把这种间隔带入生活。”我把布莱希特的《两座城》看作是社会关系的隐喻。良好的社会关系也包含了适度的间隔,能使置身个中的人拥有足够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空间,它也为个人隐私供应了庇护。
只管文学批评家们对K师长西席是否为布莱希特本尊一贯辩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把《两座城》和布莱希特当年选择东柏林作为定居地的这一事实相联系,就会创造,K师长西席替布莱希特道出了决议背后的情由。在别的城市,布莱希特能享受作为一个大剧作家和墨客的名誉,东柏林却让他看到了“被尊敬和爱戴”之外另一种可能——参与国家和城市培植的可能。
那么,在一百多则K师长西席的故事里,我最喜好哪一则呢?毫无疑问,是《K师长西席最喜好的动物》!
它的文风如此清晰明朗,仿佛布莱希特急不可耐地丢弃了K师长西席这个“思考面具”,亲口向读者诉说着他对大象的喜好。在布莱希特笔下,大象集计谋和力量、体积与机动、速率与耐力于一身;“既是一个好朋友,也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大家喜好它,也畏惧它”,大象耳朵有神奇的功能:“它们是可以调节的,大象只听适宜它听的声音。”“大象很合群,不仅喜好和同类相处,也喜好小动物和小孩子。”在结尾处,布莱希特还来了一句“它还为艺术作出贡献:供应象牙”。当一个人提及自己最喜好的动物时,每每也是把自身或者喜好的人的特色和品质投射在了它身上。就连大象的“刁滑”也是做大事的“计谋”,而不是为了弄点吃食或逃脱仇敌追捕的小伎俩。我相信,布莱希特在大象身上看到了一种空想人格,或者说:一个空想化了的布莱希特。
而我也在K师长西席的故事中,试图勾勒一个空想的“思考者”的形象,却听到K师长西席不满地对我说:“一个思想者,不须要多余的光,不多吃一块面包,也不须要多余的想法。”你瞧,K师长西席便是这样一个摒除了天真、浪漫和忧伤的思考者!
他还是市民道德的嘲笑者:“真正的善行不须要多余的捐躯者!
”不管如何,每次读上几则K师长西席的故事,我都有如经历了一趟不雅观念天下的“远足”,多多少少为“习气之家”带回一些新鲜干燥的气息。(黄雪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