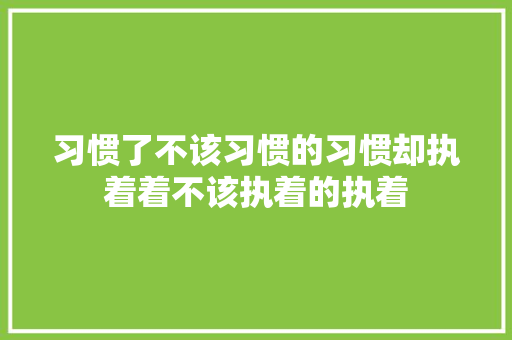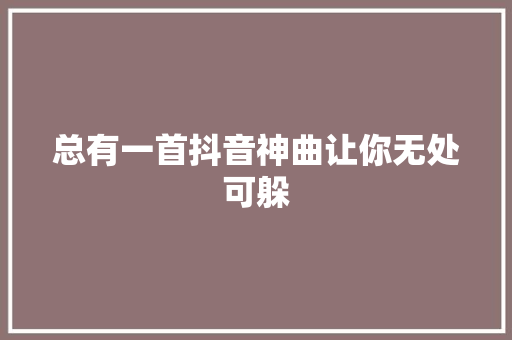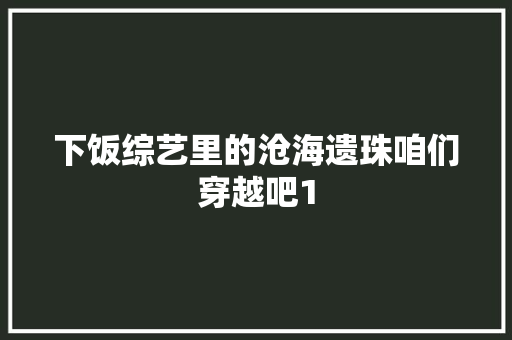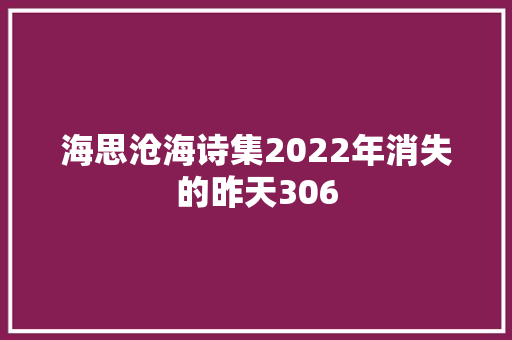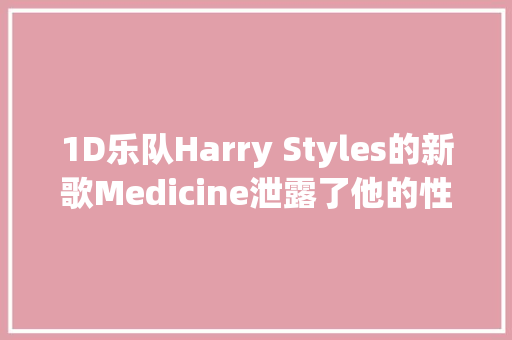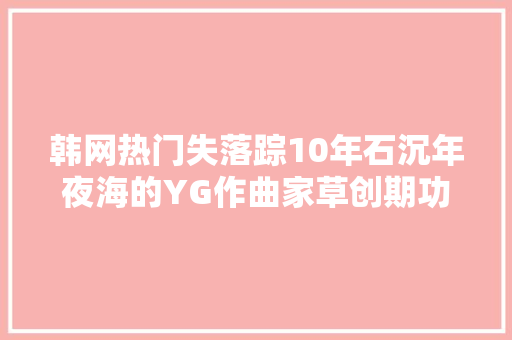资料图 图文无关 冯晨清 制
摇篮与摇篮曲 东西方的民间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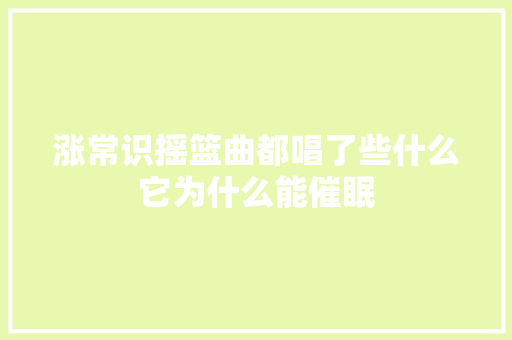
“民族的才是天下的。”这句话用在摇篮曲上再得当不过。
有一种说法是,天下上最古老的摇篮曲涌如今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摇篮曲的歌词被用楔形笔墨记录在一块巴掌大小的黏土牌上。但如果从摇篮曲本身来看,这种安抚婴幼儿入眠的哼唱该当发生在更远古的时期——在先人们结束了一天的佃猎、围坐火堆旁时,妇女们把婴儿抱在怀中,用体温和声音给族群的后代带来安全感。
至于声音通报的内容,可能是纯挚的嘘音帮助婴儿入睡,或者描述白天的佃猎场景,抑或是祈祷新的一天能有收成,吃饱喝足,躲过猛兽与自然磨难的威胁。以是很有可能摇篮曲是伴随着人类措辞的出身而涌现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继而成为民间音乐的一个独特分类。而摇篮曲的正式得名,也和民间育儿卧具——摇篮紧密相连。
在我国,摇篮早在明朝前就已涌现。明代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三里有关于“摇篮”的记载:“今人眠小儿竹篮,名摇篮。”另有明代郭晟在《家塾事亲》里提到:“古人制小儿睡车,曰摇车,以儿摇则睡故也。盖摇车即摇篮。”摇篮在不同地域的形态和名称略有不同:汉族的摇篮多用木、竹、藤做成框架,落地脚呈翘形可以旁边扭捏;我国东北地区的人们曾习气把摇篮置于炕上或吊在梁下,前者叫炕车,后者叫摇车;少数民族如达斡尔族的摇篮则仿佛一叶扁舟,半倾斜着悬挂在屋梁下,底部垂下一条长长的皮绳或麻绳,轻轻一拽摇篮就可以轻幅晃动。
虽然摇篮形态互异,但睡在摇篮里的宝宝,在他们人生的第一站里大多会听到摇篮曲的吟唱。当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婴儿,听到的摇篮曲内容也不大一样。古代西方摇篮曲的歌词大多和宗教干系。现存大英博物馆一段古埃及的铭文上,记录着一首“有邪术”的摇篮曲。这首摇篮曲的大存问思是古埃及的赫卡(邪术和医疗的神灵)正驱逐想夺走孩子的恶魔,保佑其安然。襁褓中的孩子不能为自己念祈祷文,因此摇篮曲被古人视作“护身符”一样的存在。不足为奇,东斯拉夫人的摇篮曲里常常涌现为孩子驱赶妖怪布加的场景;俄罗斯的民间摇篮曲里常常涌现睡神、睡仙和睡魔等多神教人物,个中睡神是旅行者,当他停歇在婴儿的摇篮边时也带来了就寝。睡仙类似于母亲的角色,睡魔则是父亲们战斗的工具,父亲庇护睡梦中的孩子免受恶魔的骚扰。
除了“护身符”功能,摇篮曲的歌词里也常常蕴含着父母对新生命的美好期待,希望摇篮里的婴儿身体康健、未来生活富余、出行远方实现梦想。阿根廷民歌《印第安宝宝睡着了》里就唱到:“你梦见温暖的阳光,石头也变得优柔……咱们的家门前,大路多宽广……”美国民歌《黑妈妈摇篮曲》里唱道:“小乖乖别哭啊,小宝贝,你快睡吧!
你醒来,我给你各种俊秀的小马。玄色马、灰色马,六驾马车跑天下……”可以说,摇篮曲是普通人家育婴生活的真实写照。一首摇篮曲的出身,最开始可能是某位母亲的即兴创作,之后以口传心授的办法在家族中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了民歌的一个种类。
天下各国的摇篮曲最初都以民歌的形式流传,经后人整理记录后保存下来。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基本都有本民族的摇篮曲谱曲记录,这些摇篮曲中的一些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民歌宝贝:如俄罗斯民歌《哥萨克摇篮曲》、日本民谣《江户摇篮曲》、巴基斯坦民歌《普什图人的催眠歌》……
从统计分布来看,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摇篮曲数量最多。欧洲国家以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德国等国的摇篮曲最为出名。亚洲国家中我国地域辽阔、民族繁多,自然也是盛产摇篮曲的大国。在我国,摇篮曲又叫“摇童谣”,属于民歌文体的一种。比较有名的摇篮曲有东北民歌《摇篮曲》、云南民歌《催眠歌》、安徽民歌《我家宝宝睡着了》、湖北民歌《儿睡觉觉》、台湾民歌《摇囝仔歌》等等。
古代鄂温克族利用的桦树皮摇篮。
从人声到乐器 音乐家创作摇篮曲
英语里有两个表示摇篮曲的词语,一个是“Lullaby”,另一个叫做“Berceuse”。按照音乐词条的定义,前者指以人声而作、母亲清唱的摇篮曲,民间流传的摇篮曲大多属于这一类;而后者虽然同样以抚慰孩子入眠为音乐主题,但演绎形式因此纯乐器(特殊是钢琴)演奏。经由作曲家专业的谱曲和编排,“Berceuse”涉及内容、音乐形象、曲式规模、创作手腕等更多方面。器乐摇篮曲最能打动人之处在于它的情绪流,通过表达情绪来折射音乐家对生活的体验和童年的抱负。
作为一个古老又常青的文体,摇篮曲的两个英语词语清晰地展现了这种曲调的发展过程:跟随音乐历史脉搏,摇篮曲从日常生活的即兴吟唱,变成了作曲家展现技艺、抒发情绪的路径。一个大略的小调,在日渐丰富、专业往后成为天下有名钢琴曲、管弦乐作品乃至进入歌剧,它的听众已经极大地扩展了。
音乐史上“Berceuse”文体的首次确立始于1843年,由肖邦创作的降D大调《摇篮曲》Op.57拉开序幕。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代表,肖邦生平未婚,未有子嗣,《摇篮曲》是肖邦为女中音歌唱家宝莉娜·维亚尔18个月大的女儿露易丝·维亚尔多所作,也是肖邦浩瀚创作中仅有的一首摇篮曲。这首钢琴乐曲采取降D大调,表现手腕看似纯挚,却通过14次变奏,在安宁的氛围中递进奇妙的变革。肖邦摇篮曲的听感,用大仲马的精彩描述来说便是:“静穆的音乐逐渐弥漫于大气之中,把我们笼罩在同一种觉得里。统统意识皆已驱散,进入一种沉着状态。此时的身体,除了须要安歇以外别无所求;心灵看见囚禁它的牢门已经被打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但它总是趋向于蓝色的梦境。”
肖邦的降D大调《摇篮曲》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几位作曲家,个中以李斯特最具代表性。出生于匈牙利的李斯特也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钢琴大师,在巴黎结识了肖邦,彼此惺惺相惜。肖邦逝世往后,李斯特以研究与再创作的办法延续了肖邦的风格,个中包括极具肖邦特色的音乐作品——钢琴摇篮曲S.174。李斯特钢琴摇篮曲S.174有两个版本,初版写于1854年,同样采取降D大调的办法向肖邦致敬,犹如音乐的诗句,于安谧处编织安宁美好的港湾;在随后的1862年,李斯特修正出了摇篮曲S.174的第二版,较之纯挚的初版加入了更多丰富元素,尤其是在结尾处添加了一整段的华彩。
除了肖邦和李斯特的《摇篮曲》,德国作曲家舒曼、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法国作曲家古诺、匈牙利作曲家毫瑟的《摇篮曲》也都创作出了器乐摇篮曲里耐久不衰的作品。事实上,在全体19世纪的西方音乐天下中,浪漫主义都霸占主流,音乐人才辈出。纯器乐演奏的摇篮曲带有人之初的美和蔼,也是音乐家抒发情绪、营造梦境的极好主题,因此前有肖邦、李斯特,后有勃拉姆斯、圣桑、柴可夫斯基、福雷、德彪西、拉威尔在内的多位音乐大师写下了大量经典的摇篮曲作品。也是在19世纪,纯器乐演奏的摇篮曲文体得以确立,一首首抚慰民气的幽美曲调,成为19世纪音乐财富中难以忽略的纯美之音。
在我国,从吟唱摇篮曲到器乐摇篮曲的花枝绽放于20世纪。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1934年编写的《摇篮曲》原为钢琴独奏曲,采取三段体构造,从母亲在婴儿床边拍打婴儿入睡的浅吟低唱,到构想未来生活图景的心潮澎湃,再到婴儿进入梦乡的沉着意境。这首钢琴《摇篮曲》后来又被改编为大提琴独奏曲。自贺绿汀的《摇篮曲》首开中国器乐摇篮曲的先河后,一批海内的音乐家也以此为文体投身创作,或在旧有摇篮曲调上配以当代乐器,或以中国古乐器合奏民歌摇篮曲,也有以少数民族的摇篮曲旋律为基调,用民族乐器表达情绪。作曲家杜兆植从事边陲音乐教诲五十年,以自己在内蒙古的亲自经历编写的民歌《摇篮曲》,便是以马头琴独奏的办法来赞颂草原母亲的宽阔肚量胸襟。
描述肖邦演奏摇篮曲的油画。
网络资源大爆炸 摇篮曲还会被唱起吗?
谁来为摇篮里的宝宝演出或者演奏摇篮曲?19世纪前,摇动摇篮的人也是哼唱着摇篮曲的人,母亲常日是摇篮曲的演唱者;19世纪后,专业演奏家将摇篮曲予以编排和演绎,在音乐大厅里以音乐通报情绪流动;而进入21世纪往后,在摇篮边发生发火声音哄睡婴儿的,则很可能是一部手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一部民用手机推向市场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便携式通讯设备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视频、购物、会议、网课等等场景的互动。网络资源信息大爆炸,搜索“摇篮曲”即有十多万条记录,意味着通过手机,婴儿可以听到天下上任何一首摇篮名曲的美妙旋律,也意味着母亲的摇篮曲彷佛越来越少地再被唱起。
另有一种趋势是手机里的早教内容开始逐渐压缩摇篮曲的空间。比起播放摇篮曲,国学诵读、英语童谣等“磨耳朵”的早教内容反复循环在摇篮边,乃至在婴儿还没有出生前就开始进行“早教”,焦灼的家长齐心专心想要赢在“起跑线”上,过去不紧不慢的摇篮曲彷佛没有早教内容的输入那么实际。
但人类还是须要摇篮曲的,无论是身心还是音乐美育,摇篮曲这种古老的形式都有它极强的存在代价,并且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哈佛大学的康斯坦斯·班布里奇和米拉·贝托洛牵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不雅观察了144个均匀年事为7个月的婴儿。他们给这些婴儿安装了传感器以监测他们的心率和出汗水平,接着为其播放包括摇篮曲在内的各种歌曲。除了心率和出汗监控,研究者还利用婴儿面部视频来监测他们的瞳孔变革,综合所有的数据,可以得出婴儿在吸收不同音乐时候的状态。终极实验证明,婴儿在听到摇篮曲时心率和出汗率都低落得最多,表明摇篮曲确实让他们更为放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母亲为婴儿哼唱摇篮曲所能营造的温暖和安全感,依旧是手机难以取代的。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永久保护你……”这是生命最初的温暖与美妙,它所铸造的甜蜜梦境是每一个人最纯挚的开始,也是最绮丽的心之归处。
刨根问底
摇篮曲都唱了些什么?
不同时期和民族的摇篮曲,曲调千差万别,但从吟唱内容上来说基本分为三类。按照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一篇研究论文《三种类型摇篮曲音乐形态之比较》中谈到的,这三类分别是:吟诵性摇篮曲、抒怀性摇篮曲以及叙事性摇篮曲。
吟诵性摇篮曲该当是最早出身的摇篮曲,它产生于母亲日常哄睡孩子的过程中,即兴发出的一些安抚的声音词汇,包括无意义的拟声词。吟诵性摇篮曲介于措辞和音乐之间,腔调随性而发,固定的歌词也是临时编唱,因此构造大略、曲子也很短小,但已经具有了基本的音乐属性。范例的吟诵性摇篮曲如我国北方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广为流传的《呜噜来》,全篇歌词只有“呜噜来”三个字。“呜噜来”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摇篮”,也可以用作动词表示“摇啊摇”,可以想象这首摇篮曲一定是在哄娃娃睡觉的过程中即兴哼唱,之后逐渐固定下来的。
抒怀性摇篮曲则是摇篮曲体系的主流,它在历史上的涌现比吟诵性摇篮曲要晚,随音告成上进入比较高等的形态往后应运而生。比较“依字行腔”、单词重复的吟诵摇篮曲,抒怀摇篮曲常日有完全的乐段构造,歌词表达的意境也更加具象,美妙、抒怀的主题旋律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台湾地区的《婴婴困》即是一首饱含深情的抒怀性摇篮曲:“婴婴困,婴婴困,一瞑大一寸。婴婴困,婴婴困,一瞑大一尺。婴啊婴,谁人生?婴啊婴,阿母生。”
叙事性摇篮曲的数目比较少,这种摇篮曲的视角每每不是从儿童而是从成人出发,核阅、描述儿童的发展过程与外部生活。从曲调构造来说,叙事性摇篮曲每每更为繁芜,同时伴有转调的手腕。例如盛行于日今年夜阪府一带的《竹田摇篮曲》:“守着孩子已经倦了,孟兰盆节之前,雪已经轻轻飘了……真想尽快走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哪边能看到,父母的家呀。”
原来如此
摇篮曲为什么能催眠?
能否快速入眠是影响就寝质量的一个关键成分。为了帮助孩子入睡,东西方的母亲不谋而合为襁褓中的婴儿哼唱摇篮曲;一些想要改进就寝质量的成年人也会在睡前播放类似摇篮曲的音乐,放松身心进入梦乡。为什么大多数摇篮曲具有催眠浸染呢?常日认为有生理和生理的双层次缘故原由。
从生理层面来说,音乐的频率可以浸染于人体大脑皮层,对丘脑下部以及边缘系统产生浸染,改变感情体验和身体性能。摇篮曲大多以行板为进行节奏,伴有一拍一音的重复,带领大脑从凌乱的思绪中专注到舒缓的旋律上,也勾引心率和呼吸趋于规律,这些都可以起到镇静浸染。
而从生理层次来说,摇篮曲的歌词寓意中大多会有“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这样安抚入眠的话语,对吸收者的生理产生暗示浸染,提示其身体正处在一个适宜放松入睡的韶光状态;同时摇篮曲的旋律音阶常日是由高到低,这样的曲线很像是经由一天的劳碌后精力逐渐回落,直至进入梦乡。末了,摇篮曲的温顺乐章也让人犹如回到童年,置身于母亲的温暖怀抱。情绪上的回归也会给身心带来安全、放松的觉得,让听者更加安心地入睡。
(原标题:摇篮曲 生命最初的旋律)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艾栗斯
流程编辑:L022
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容许,不得转载或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