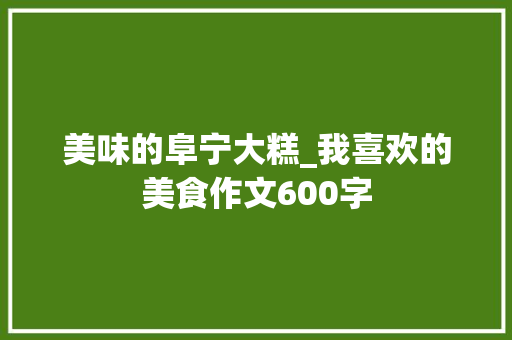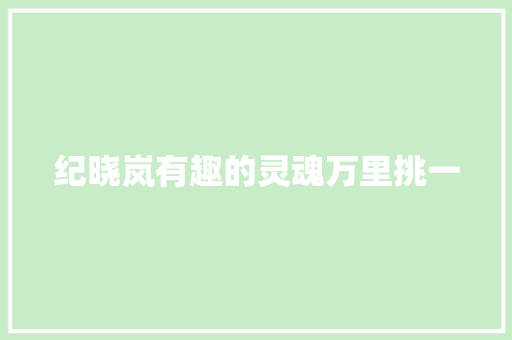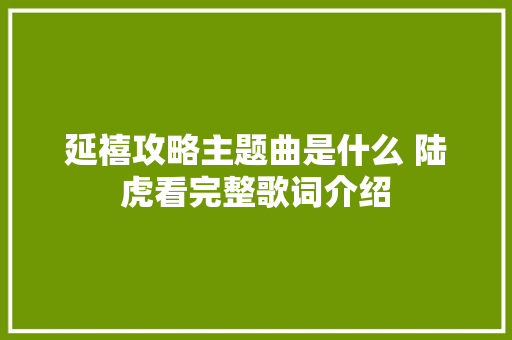作者:溪月弯弯,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户简陋的茅舍中还亮着一盏寒灯,灯下是一个儿子向老母拜别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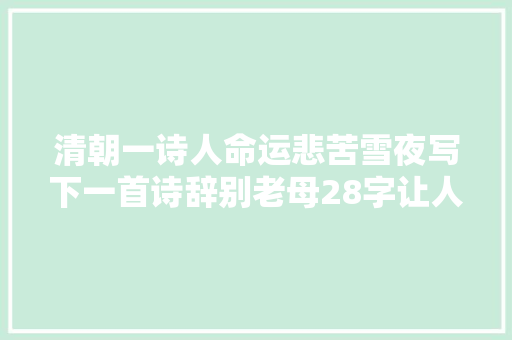
表面风雪肆虐,呼啸的北风透过轻掩的柴门,又从窗户的缝隙中挤进屋内,瞬间添了几分凉意。
墨客这些年为生存所迫四处入幕,如今正月还未过完,在这风雪之夜,不得不再次离家而去。多情自古伤离去,更何况在这冰冷的暮夜。
他掀起门帘,看到高龄体弱的老母亲愁容满面,眼中的热泪早已哭干。此去山高路远,夜黑风寒,母亲满是担忧,她怎舍得爱子远游呢。
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猛然瞥见母亲的双鬓不知何时已变得斑白,不觉悲从中来,由于这是让人刺眼和心痛的一种白。
夜色渐晚,风雪渐大,他推开柴门就要出发了,可双脚彷佛沉重得迈不开步子。他强忍悲哀,故作洒脱,待走出很远,才敢转头去望,创造老母还倚着柴门在目送着他渐行渐远。
离去让墨客思潮起伏,想起多年的流落奔忙和仕途失落意,不能奉养母亲于身边,感叹自己身为儿子有何用,还不如没有。
羞愧和着万千悲愤将墨客的内心填满,万般感慨化作一首伤感的诗篇《别老母》:
搴(qiān)帷拜母河梁去,
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
此时有子不如无。
01
墨客是黄景仁,这一年他23岁。受太平知府沈业富的约请,他前往去做幕宾。
多少人便是通过他这首拜别母亲的佳作而认识他的。没有太多的措辞表达,仅仅用寥寥几语描述了一个平凡生活中的母子离去场景,可是这份平凡朴质的真情却足以冲动无数读者。
全篇弥漫着的别离之痛、思念之伤让人生发出一种共情。反不雅观自身,在尘世中奔忙的我们,分明和他一样也有过四处流落的岁月。那份为生活所迫的无奈,那份依依不舍的酸楚,那份面对未知的惶恐,都是如此清晰可感。
他用平淡的笔触写尽了对母亲的歉疚、壮志难酬的悲哀,还有那份潜藏个中的怅惘和迷茫。深夜里,与高堂老母、娇妻幼女别过,更添一层凄凉,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无奈酸楚,令人无不堪怜。
一句“此时有子不如无”的凝重自责直击心底,浅语道衷肠,道出了天下所有离家远行的游子们的肺腑之言。
这种不能奉养亲母在侧的憾恨之情,非亲自经历,不能道出。这种最是难奈的沉痛之情古今皆同,只有体会过的人,才会感同身受。
要知道,在古代,离去是人生至关主要的大事。当时交通极不发达,最快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马和船了。一次远行每每要花上数月、半年乃至更长的韶光才能抵达目的地。
途中,既要穿过荒山野岭,还要超越江涛河浪,其间盗贼横行,医疗条件也差,可谓风险重重。因此,每一次远别都有可能是此生末了一次见面,一别成永诀的事司空见惯,黄景仁又岂能不知。
《论语·里仁》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慈母已是行将就木,游子却不得不忍痛离开,这怎能不使游子陷入深深的自责。
对出息迷离的他而言,远游实则是一场漫无目的且带着风险的闯荡,苍茫之夜奔赴的实则是一个遥不可知的未来,这样的痛楚和羞愧怎能不深入骨髓。
02
黄景仁,字仲则,又字汉镛,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四年(1749)出生于常州一个没落的一个书喷鼻香世家。
他是一位清朝墨客,我们彷佛并不太熟习他本人,却常将他的诗句挂在嘴边,比如那句很有名的自嘲诗“百无一用是诗人”。
黄景仁命途多舛,家世相称凄苦。父亲在世时,黄家尚能勉强坚持生存,不料父亲在他四岁那年就撒手人寰,家中只剩“田半顷、屋三椽”,甚至“家徒壁立”。
幼年的黄景仁就立志发奋苦读,寡母屠氏也把重振家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教之识字,督之读书。
他资质聪慧,好学上进,7岁随祖父归武进,居白云溪北,8岁入塾,9岁时便能吟出“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的佳句,令人讴歌不已。
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祖父、祖母也相继去世,16岁时兄长早逝,只剩他和母亲相依为命。门庭益发软弱,家境愈加窘困,母亲用柔弱的双肩担起身庭生活的重任。
含辛茹苦的母亲东乞西讨,艰巨贫寒的生活非常酸楚。小小年纪既要承受失落去嫡亲的悲痛,还过早地尝尽世间苦难,这样的人生经历让少年的黄景仁早熟又早慧,也养成了他多愁善感的个性。
03
16岁那年,他从三千人的童生试中脱颖而出,位居榜首,考取秀才。原以为自己才华横溢,出息将一片光明,不料后来他五度江南乡试,三应顺天乡试,均屡试不中。
19岁时,他参加了江宁乡试,名落孙山,只得把内心的失落落和激愤寄托笔下,写下那首广为传诵的名诗《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诗人。
莫因诗卷愁成谶(chèn),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景仁生于盛世,诗名远扬,深受当时大儒学士的讴歌与青睐。然而在那个功名决定自身社会代价的时期里,他空有一身诗才,却无用武之地,就像一只受伤的困兽,看不到出路与光明。
他看尽人生百态,尝尽人间悲苦,没想到一次次努力换来的是屡次的科场失落利,是多年的生存无着。
出身清贫的黄景仁将自傲孤高和敏感自卑集于一体,其内心的失落意和不平一时达到了极点,到头来只能悲惨地叹一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诗人”。
这句诗几百年来口口传诵,险些成为命薄运蹇的代名词,引得多少怀才不遇士人们的共鸣。
他多想靠自身所学摆脱贫穷的出身,多想让母亲过上稳定宽裕的日子,可是残酷的现实与自我抱负的巨大差距击碎了他美好的憧憬。
04
黄景仁生平落落寡合,却不乏良师良朋。乾隆三十一年(1766),时年18岁的他曾入常州龙城书院学习,为山长邵齐焘(tāo)所看重。
邵齐焘师长西席对体质羸弱却傲骄敏感的黄景仁产生了怜悯之心,曾作诗教诲他要宽容应对世俗,勾引他乐不雅观积极地面对人生。老师邵齐焘的知遇之恩他深深铭记。
正是在书院学习期间,他碰着了洪亮吉,黄景仁才情横溢,傲气骄矜,洪亮吉则气度宽容,豁达重情。相似的命运和同样的抱负让两位同窗,逐步发展成了生平至交。
乾隆三十四年(1769),迫于贫寒的家境,黄景仁满含凄楚地踏上负米出游、依人作幕的生涯。
幕客入幕,不为参政议政或谋划戎事,反而只能做些整理文稿之类的杂事,如修书、著书、校书,以及诗酒唱和、佐理文字、诗文娱人等。
他游幕于多家幕府,足迹遍及浙皖三湘,一边待考乡试,一边谋划生存。数不清有多少个日昼夜夜,他困难地跋涉在南来北往的途程之中,也记不得有多少次寒灯独夜,他孤寂地栖宿在异地他乡的旅舍之内。
在阔别故土,作别嫡亲的日子里,他凭靠着亲友给予的一点温暖,捱过生命中的愁苦、哀怨、病患和伤感。
就在黄景仁拜别老母的这年冬天,朱筠师长西席奉命督安徽学政,慕其名,他先后将洪亮吉、黄景仁延至幕中。
这是黄景仁生平中难得的快意安定光阴,他不止受到朱筠的赏识,还得以再次得以与平生好友相伴,白日饮酒校文,夜间切磋诗技。洪亮吉后来回忆:“君日中阅试卷,夜为诗,至漏尽不止。每得一篇,辄就榻呼亮吉夸视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达晓不寐,而君不倦。”
黄景仁虽在外游幕,但时常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尤其是对老母充满愧疚。客于朱筠幕中时,有家难回的他就写过一首《春日客感》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祇(zhǐ)有乡心落雁前,更无佳兴慰华年。
人间别是消魂事,客里春非望远天。
久病花辰常听雨,独行草路自生烟。
耳旁模糊清江涨,多少归人下水船。
05
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三月里的上巳佳节,朱筠于安徽马鞍山采石矶的太白楼上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人盛会。
那一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饮酒赋诗,好不热闹。席间,最年少的黄景仁,身穿白袷,洒脱洒脱,立于日影之中,挥笔自若,倾刻数百言,座客皆搁笔惊叹。
一诗既出,便被誉为堪比王勃滕王阁作赋的佳作,还在一夜之间,人竞缮写,传诵不绝,一时纸贵,从此诗名大振。
这位“著白袷(jiá) 立日影”的少年究竟作了何等好诗,引得诗友们争相传诵呢?即《笥(sì)河师长西席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
“彤霞一片海上来,照我楼上华筵开。
倾觞绿酒忽复尽,楼中谪仙安在哉……
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去世重山丘。
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
只管黄景仁诗名日益显著,但生性高傲的墨客终不免有“长铗(jiá)依人游未已,短衣射虎气难平”的嗟叹。仿佛热闹一贯是别人的,伴随他的是无穷的清苦和孤独。
对付长久仰人鼻息,长年客居在外的墨客而言,他骨子里的忧思是跬步不离的,哪怕是团圆的时候也不例外。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次癸巳,黄景仁回抵家乡和亲友团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他却在暖意融融的团圆之后,独自伫立在街市的小桥上仰望夜空。
墨客一贯活得很复苏,他透过“千家笑语”的盛世表象,已模糊觉察其背后潜伏的巨大忧患。在这清冷的夜里,怅惘和忧虑陡然袭来,于是《癸巳除夕偶成》两首从笔尖流出:
(其一)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其二)
年年此夕费吟呻,儿女灯前窃笑频。
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墨客。
06
乾隆四十年(1775),27岁的黄景仁远赴北京,次年夏,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以二等充四库誊录生。在京师,他与当时的京城名流如王昶(chǎng)、翁方纲、纪昀等人密切交往。
他天真地以为可在京城立足了,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迎母移家来京,不料俸薄口众,未支撑多久,生存又成问题。百口陷入更困顿的田地,不得不依赖好友们的帮助聊以度日。
“百口都在风声里,玄月衣裳未剪裁”一语就足以见得他的生活多么捉襟见肘,我们都能想象出流落异域的一家人,玄月的深秋里,因没有御寒的衣物而在萧瑟的秋风中颤栗颤动的悲惨场景。
其余,黄景仁在京都参加的几次乡试都以失落败告终,此时他已负债累累,仕途无望。困顿潦倒、贫病交加、梦想破灭,现实的各类让墨客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备受煎熬,终致心力交瘁。
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被授武英殿书签官,依例应得主簿,由朋侪帮助,捐为县丞,在京候铨选。
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35岁的黄景仁被债主所逼,乃北走太行,抱病赴西安,此程千里有余,他行至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时,病情恶化,不幸病故。
这个诗心纯洁、行吟生平的落拓墨客,短暂的生命就此草草地画上凄凉的句号。来这人间一趟,他就像一位孤独的乘客,并未享受盛世应有的富余和美满,反而在仕途困顿、生活窘迫中走完了愁苦的生平。
“颠狂落拓休相笑,各任天机遣世情。”再回顾,他还是那个特立独行的墨客,昔时夜部分人皓首穷经,沉迷故纸堆中之时,他依然武断地执着于诗歌创作。
他的诗歌独树一帜,“以情取胜”,是内心深处的呼唤,是为底层士子的叫嚣。他用悲天悯人的作品,深情诉说着落寞的心境和阴郁的现实。
他生平奔波劳苦,久试不遇,四方游幕,只能在世事无常的漩涡中进退维谷,夹缝求生。行走于那个时期,他始终都在边缘徘徊,至去世都未能真正靠近过鼓噪。
“添君风雪三更梦,老我江湖十载灯。”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彷佛看得见他江湖夜雨的落魄生平,看得见他风雪之夜别老母的那次远行。
-作者-
溪月弯弯,愿用厚重作纸,清淡作笔,书写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