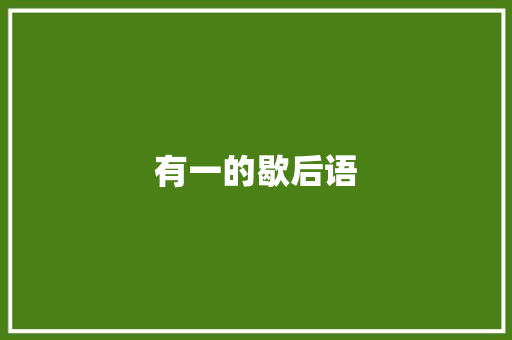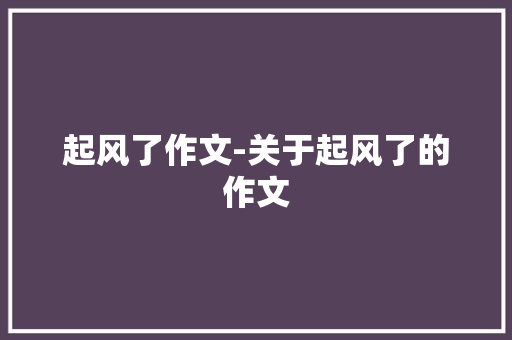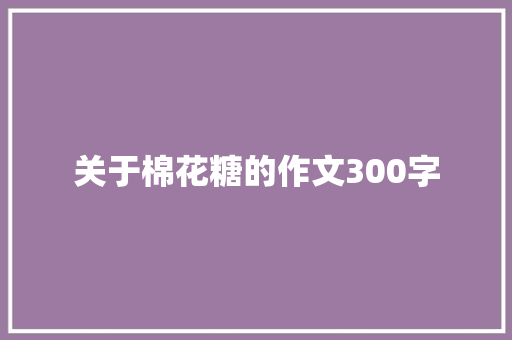过了十九年,我终于以为纽约这个大名鼎鼎的城市,或许真的是个有趣的地方。对我而言,纽约就像一个我暗恋了良久却不理我的男生,在我决定放弃时,他却表示对我有好感,有点像是这样。
——角田光代《在全天下迷路》

考试测验先容纽约城的行为本身就没故意义,由于祂的故事这个天下无人不知。祂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都邑,纽约在1950年就有了1300万人,帝国大厦的方尖碑在二战后的当代秩序中奠定了城市的意义。
我所认识的纽约,是一个拥有统统的城市(A city has everything)。在这片从电池公园到哥伦比亚大学足球场的狭长岛屿上坐落着统统人类文明所能创造的工具。这里有全天下最好的博物馆、画廊、剧院、大学、拍卖行。每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每一家银行律所与顶级公司、每一个组织的秘密情报网都在这座圣城有自己的据点。
而我更感念的是生活在这个城里的角斗士,正是这座新耶路撒冷城永不枯竭的能量来源。有在上东区打通四套公寓蜗居、致力于自己的精英圈生活,却无法从公开路子得到其任何照片的亿万富豪;有挤在WeWork里一边打电话兜售,一边在墙上写记录,连办公室都是靠coupon沽来的半年time window,却不放弃演奏未来的梦想家;有说英法阿三国措辞、打那种帮希腊政府追讨英国抢夺文物的官司、娶顶级钻石王老五的白富美智大状师。
纽约授予来此冒险的勇士三件瑰宝:“无尽机遇”之剑、“惜时理性”之甲、“朕即天下”之驹。每一个NewYorker的故事和理解各有不同, 但城里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生活在这个昂贵的城市所希望收成的是每次networking认识的新联系人、带来的全新机会;每一秒的韶光都精确利用,确保不为愚蠢所废,乃至舍不得抽韶光出来吃午餐,仅能草草办理。
我的专业是data science,如果我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该当是一副清晨挤地铁去办公室写程序的状态。以是我也不明白哪个蝴蝶效应让我在纽约认识了Leafy这个小妖精。
带有东方儒教文明色彩的集体行为办法,大部分的中国学生第一次去美国时总喜好结伴坐飞机。那一年夏天,我们一行凑了6个人,坐了一趟广州转多哈到纽约的航班。如那种第一次到帝国主义大本营的愉快和不安,此生该当不会再能体会了。 下了飞机入关的时候,排完了贪食蛇一样的队,入境处的看门人核对了我的资料一遍,举头瞄了一眼我眼镜后的表情,像去世鱼一样又重新看回屏幕,没有问一个问题。终于,他拿起我的资料,推开了小门,示意我跟上他一起去小黑屋。
走过一条不长的走廊,邪恶的看门人把我交给等待区的座椅,扔下材料给同事,自己回去连续猎杀其他晦气蛋。冰冷长椅上的我等了好久好久,紧张和不安让我连刷微信的力气都没有。飘忽的把稳力创造前面的姑娘眼熟,彷佛之前在入境时有站我前面。也不记得是我先说话还是Leafy先说话,后来我的微信里就多了一个联系人。
不记得这家伙是哪家学校召唤出来的怪物,反正她的朋友圈里每隔几周就会鬼马地发一波她拍摄的表现主义果照,大多是表现一些青年人的不安分和女权主义的一些思潮。比起我自己同学发的无趣的知识类科普文,Leafy的作品在我万花筒的阅读清单中也算是值得highlight的佳构。而model无非便是她的朋友们,个中也包括了东京小姐Kanae。
机会的来源,无非等与要。我常吵着Leafy要带我拍电影(她学这个),然而直到去年夏天才第一次有机会互助。她发微信来问要不要一起拍记录片, 而Kanae酱便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一个夜总会的女招待。Kanae酱是一个特殊范例的三次元日本姑娘,会像东亚女孩一样说话,只有吸烟的时候才会出卖她自己薄弱的内心。现在彷佛是leafy的同学,在走演出方向。
剧本是一个很老套的日本姑娘纽约追梦的故事。由于金钱堕落酒色,又由于发展重新振作的大团圆结局。当然我所关心的只是拍照运镜,能拍到厉害的东西最主要(我都跟leafy说没有黄赌毒的情节不要找我)。第一幕的拍摄状况频出,Kanae家的访问有一个狭长无比还有楼梯须要爬的走廊。每一个纽飘都明白,那种为了分摊房租,不断把客厅改成房间后留下的狭长隧道。导致我纵然利用了稳定器的画面,看起来都像在地震,而且拖慢了全体叙事节奏。下一幕静态采访的镜头中,我就只须要借助三脚架,于是省力了很多。反倒是我们的vocal小哥Collin要适应Kanae生疏的独白,得一次次调试重录。不过这个比我们3个东方人还腼腆的美国小哥彷佛乐在个中。
在纽约,每一个Job Description都哀求Candidat是quick-learner。自由女神摆荡着皮鞭让每个奴隶以最快速地学会如何事情。随着项目的发展,我们几个人的能力也不再那么生硬。大家一起找拍摄园地、扛器材、用饭饮酒、我不吸烟。相互之间也会互换各自位置的操作,我会跟Collin学玩Tascum做音频视频合拍,研究什么场合须要用deadcat(收音棒上毛茸茸的降噪);也会和Shun谈论要不要在暗环境用Raw拍摄提高后期空间;再后来我们在KTV里拍摄Kanae酱和客人调情的一幕时Ben搬了两台灯过来补光。
Kanae一贯奇怪我和Leafy竟然是在机场认识的朋友。这便是纽约的魔力,这个天下上最劳碌的陌生人之间会乐意停下来花一分钟彼此谈天。不论是在熙来攘往的SoHo试衣间旁、永久等不到下一趟车的6号线地铁月台还是已经和回形针一样绕到入口的Trade Joe的排队,也不论你是梵蒂冈教皇还是造孽墨西哥民工。这座城市没有凡人,你在Park Ave或者第七大道擦肩而过的甲乙丙可能是商界殷商,42街地下隧道里卖艺的乐手可能是拿奖得手软的大师。 在帝国大厦的光辉之下每个人都变得谦卑承认须要效忠这座城市的自由精神。
纽约客让人倾慕的残酷生活是靠自己放弃一次次偷
路易十四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朕即国家” L’Etat, C’est Moi. 久居纽约的人都有这种富有四海的优胜感,Canal St的中国城、拉瓜迪亚的埃及城、7号线70街旁边的拉美城、梅西百货旁32街的韩国城。这座城市浓缩了全体天下,但富有天下的纽约人忘却了真正的天下,还活着界。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仍旧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等待着朝拜法老的子民。代价连城的宣德炉在帝都的国博只能于过道里陪展。
善于权衡利弊的纽约人,有的会选择留在城里的1st tier league连续搏杀,享受这片土壤带给他们的荣光;有的会选择登上JFK的阶梯,动身去全天下讨伐化外蛮夷。就像Empire State of Minds的歌词写的一样,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这些肆无忌惮的野心家,纽约的生态系统能给予的养料还不敷以喂饱他们的欲壑深渊。乘着皮萨罗的黄金帆船,安第斯山脉的悠哉国公民啊,纽约野蛮人的枪已上膛, 请奉献上你们珍藏的金银,我们要用财宝去迢遥的东方交流中国人的珍奇异宝。
有一次我坐红眼航班去冰岛的时候,在JFK的AirTrain station被人拍肩叫住,原来是大学期间的石友果子。“好巧在机场碰到你,叫你好多次也禁绝许我。”。像这种天下十字路口的情节,纽约便是这样一个你会遇见所有人和所有机会的地方呀。
在纽约生活了一千天,每当有海内的朋友问我美国和中国比较起来若何。抱歉我没有答案, 纽约不属于美国,纽约属于全天下。Le monde, c’est moi.
免责声明:转载自网络 不用于商业宣扬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侵权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