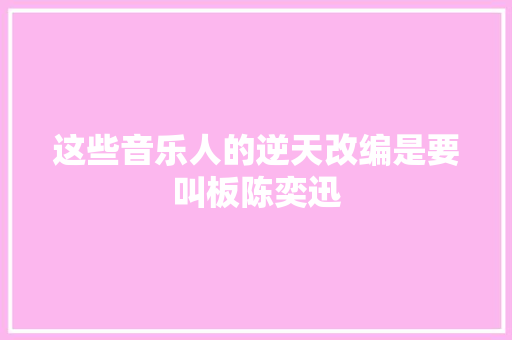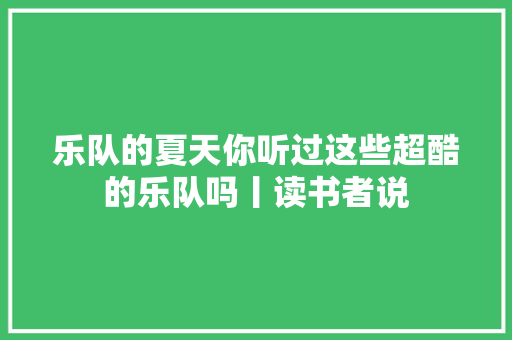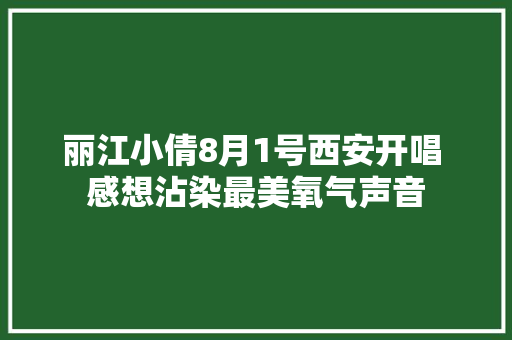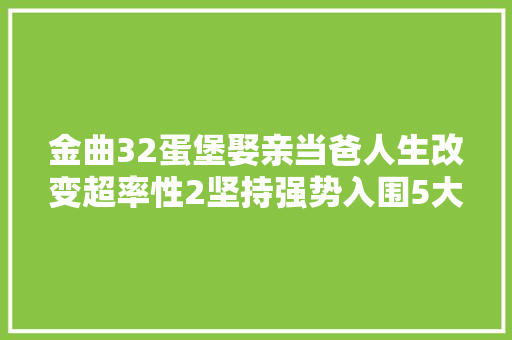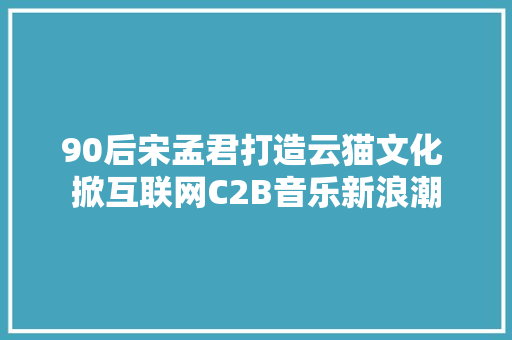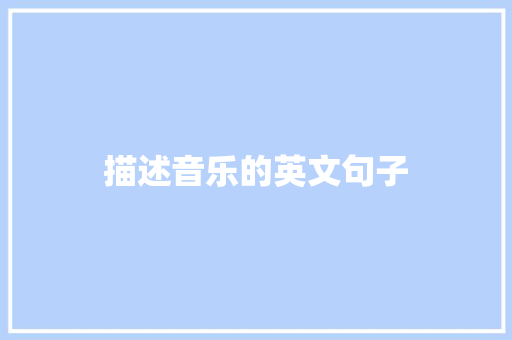我第一次听《回西安》是在“北漂”的出租屋里,歌放到一半,同事说:“我靠,这是哪个泼皮唱的,这么牛X!
”
初见马飞,在曲江音乐厅,我和音乐人王建房在谈事,发言快要结束时,王建房溘然站起来说,马飞正在排练房排练,我很是惊异,请王建房先容认识,马飞神采匆匆的从排练房里走出来打呼唤,他剪了短发,穿着白T恤、橘赤色短裤,脚上蹬着一双老布鞋,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是个做民谣的,倒是像个闲人(西安话混混的意思)。我心想:哦,这便是马飞,和舞台上的不太一样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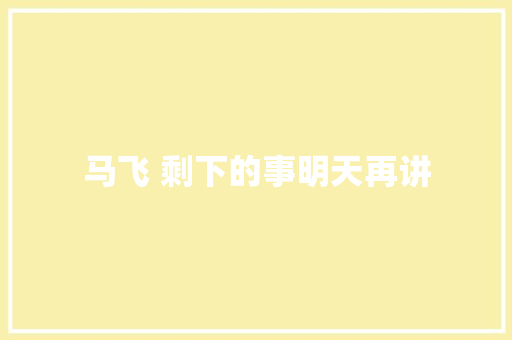
马飞实在不但不是闲人,而且还是个搞艺术的娃。在陕西,从大人到小孩都能扯着嗓子,吼一句“长安县,乌木(那么)些年”,险些到了“有陕西人的地方就有马飞的歌”的田地。《我能欻》《长安县》《回西安》《李导演》《两个科学家在吃面》……这些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都出自马飞之手,他诙谐无奈地调侃着生活的无聊、找事情的压力、\"大众北漂\公众的心伤,让人听完心里苦涩却又高兴。也是因此马飞身上背着“西安法宝级音乐人”的光环,张亚东更称他的音乐为“真正的中国风”。
有名乐评人科尔沁夫谈到马飞时说:“马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比较于其他民谣歌手,马飞的音乐素养显得更强一些。首先他的歌词特殊故意思,诙谐中带着讽刺,描述普通人的生活,而陕西方言很新鲜又很亲切,他的歌虽然朴实但不市井,还带着底层知识分子的玄色诙谐,非常酷,我以为只要听过他的歌,都会喜好上他的民谣。”
搞艺术的娃
1981年,马飞出生在陕北延安。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家中,马飞的父亲完备没有任何的艺术爱好,反倒是母亲喜好唱戏。据马飞的母亲后来回忆,童年的马飞,随便教一个戏曲唱段,两天就能唱会。由于文化课成绩差,马飞走上了学画的道路。1996年,他考上了省艺校来西安上学,也便是从那个时候起,马飞开始学习吉他。
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由于痴迷,马飞常常把口水点到琴上。“当时也没有履历,刚学会的东西,弹的时候就随意马虎投入,现在反而不随意马虎投入,便是刚学会那会儿,似会非会那会儿,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一投入进去,嘴就伸开了,嘴一伸开,口水就流下来了。”马飞说。
马飞大学就读于西安美院油画系,在美院的那几年,除了组乐队,延安人马飞还学会了一口土得掉渣的长安县方言,学会了蹲着吃一碗扯面。“没有怎么画过画,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有韶光就玩吉他、饮酒、玩游戏,学的是油画,实在研究的是音乐。”马飞回顾道。
很多人都好奇马飞跟谁学了一口隧道的长安话,他回应说是来西安后和大学同学学的。不过,这也跟他小时候常常听外公讲西安方言有关。“我外公是西安人,我小时候听他说话,就觉得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我说不出来那儿不一样,后来到西安往后,我才知道他说的是西安方言,原来我外公是西安人,之前我一贯不知道。”
2005年,马飞大学毕业,由于事情的关系,他去了北京跑剧组。现在,马飞依然记得刚到北京时的场景:“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接的我,见到老同学还挺高兴的,我们坐上车大概坐了有3个小时才随处所,我一下车看到漫天的黄土,刚好是春天沙尘暴乍起,我觉得心里挺凄凉的。”
在剧组里,马飞的职务是副导演。“我紧张卖力群众演员、特约演员这一块儿,比如前一天晚上拿到拍摄操持往后,我就会根据拍摄操持组织群众演员,第二天早上演员来了往后,带着他们戴头套、换衣服,然后带进场,然后安排好位置和演出办法,戏就正式开演了。”
后来马飞跟人提到那段“北漂”的日子说,那是他离音乐最远的时候。刚到北京的马飞面临着两个严重的生存问题,一个是缺钱,一个是孤独。“最穷的时候,两个星期,只吃馒头,一个大学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一罐野山椒,然后就着野山椒吃馒头。”马飞说。
伴随着物质上匮乏的同时,由于拍片的间隙会有大段的空闲韶光,马飞还感想熏染到了“瘆到骨头里的孤独”。“北京太大了,你认识的人离你很远,平时也只能一个人待着,我还记得我孤独到什么程度,我住的小区一楼有一家盲人推拿,我每天不雅观察那些盲人,他们放工了往后,他们走起路来第一个是个正凡人,后边随着的一个手搭在一个肩膀上,就像游戏里《饕餮蛇》一样,沿着路面带微笑整洁的走”。
2006年底,有一个朋友结束“北漂”要离开北京回老家,他把一把吉他送给了马飞。为了排解心中的孤独,马飞拾起吉他,开始写歌,他后来大部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
韶光推移到2009年,马飞在北京的日子也好过了起来,他也有钱了,住在北三环。但朋友只用了一碗泡馍就把远在北京的马飞召回了西安。“我就想着回西安吃顿泡馍然后再回去,但是一回来就觉得特殊的清闲,我就不想再回去了,我打电话给我大学同学,让他帮我把屋子退了,东西先放在他家里,从此就再也没有再回去。”马飞说。
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
在陕西,音乐人的音乐风格常常会受陕北民歌和秦腔戏曲的影响,再加上西安是摇滚重镇,很多人在音乐上都走上了摇滚的道路,但马飞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唱的歌曲紧张以民谣为主。但马飞并不认可民谣音乐人这个标签,“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以为风格根本就不主要,一定是先有音乐再有风格的,风格是人总结出来的,一旦陷入风格这个漩涡里,将会被这个东西吞噬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很多人质疑马飞为什么很少唱陕北民歌。马飞回应说。“陕北民歌当然好,但是这个东西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会改变你,我又是喜好无拘无束的人,我怕我驾驭不了这个东西,反而把这个东西挥霍了。”马飞认为,现在很多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上场就用特殊高亢的办法演出,这种形式完备不能表达陕北民歌要传达的东西。
生活中,马飞喜好不雅观察碰着的小人物,不雅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在马飞看来,这些人很有聪慧,虽然他们身上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小毛病,但是实质是善良的。而马飞的创作灵感素材也大多来自于那些眇小的真实个体:北漂的导演,饭铺老板,长安县小伙,搞文艺的伙计,这些人都被他信手拈来写进歌里。
舞台上,马飞欢畅且畅快淋漓的唱着小人物生活中碰着的酸甜苦辣,末了叹一句“钱不好挣啊”,“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看”,“城市里面盖好的高楼连的是一片片,可是在那儿没有咱能买得起的一小间”,这些感叹大都是些精确的废话,但让人听完心里有些苦涩却又高兴。
现在,马飞每个月在全国各地的商业演出均匀下来有四场之多,演出的收入足以担保他过着体面有肃静的生活,他的生活状态也因此趋于平稳。但随着重复性演出的增多,音乐对马飞来说却变成了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也让马飞对音乐产生了审美疲倦。
马飞坦陈他碰着了创作瓶颈,“一方面,由于之前写过一些东西,以是现在以为不能写比以前品质更低的东西,这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成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了。另一方面,生活彷佛没有以前那么大略了,随着年事的增长,也有了老婆孩子,家庭的包袱也变成了无形的枷锁,写歌比以前更难了。”
马飞的妻子我刚好见过。顺直的长发,身材苗条,端庄又大方,身上有种陕北姑娘特有的朴实气质。她属于那种好学生类型的姑娘,上学时是英语课代表,毕业后,做了英语老师。
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马飞还没有开始做乐队,那时候他刚回西安,在酒吧里面弹吉他,一晚上80块钱。“我媳妇那时候就挺支持我的,我们当时还没有结婚,她没有由于我搞音乐,就高看我一眼,也没有低看一眼,便是用正常的眼力来看待这件事,我以为这一点很了不起。”提及妻子对待他从事音乐这一行的态度,马飞很是自满。
虽然现在在音乐上碰着了瓶颈,但马飞并不焦虑。在他看来,能常常和乐队在一起就特殊快乐,演出也罢,排练也罢,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很高兴了,他也已经由了那个铆着劲儿把音乐当义务的阶段。“我也以为这个状态蛮舒畅的,放松不是说对不雅观众不负任务,而是这种状态能让演出效果离空想中的状态更近一步,但是,我以为乐队还是须要大量的排练,由于不排练新的东西就出不来,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把排练的量提一些。”马飞阐明说。
我有个伙计他是个导演
除了歌手的身份,马飞另一个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导演。由于平时演出繁忙,他很少有韶光去包装自己。实在,马飞也是曾得到过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的作品《图雅的婚事》的副导演;还取得高票房,并得到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拍照)的作品《白鹿原》的副导演。
前不久,马飞和一家公司互助成立了一个电影事情室,这家公司为马飞注资5000万启动了一个电影基金,现阶段马飞的事情正处于剧本的甄选阶段。“我之前的事情一贯是干副导演,现在有机会自己做电影,心里还挺乐意做这个事情的,由于干副导演实在是替别人事情,自己做导演,希望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于实践”。
虽然,现在把把稳力暂时放在了电影上,但马飞谈得最多的还是音乐。谈天间隙,他把手机打开,让我看他过年回家时拍的小视频:房顶上雪花融化了,水点从房檐上落下来,打在码在房檐上装着柴火的编织袋上,有一种特殊强的节奏感,像有人拍打手鼓的声音。对声音的敏感,让马飞在平常的环境中也能听出别人听不出的韵律感。
在被问及关于导演身份和歌手身份看重哪一个时,马飞的回答十分诚恳,“我彷佛是一阵一阵的,有一段韶光,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我以为音乐可能是最好搞得一份事情,但现在,反而以为离那个事情越远了,实在写歌的时候挺故意思的,有无数种可能性,一旦定型演出,别人哀求你重复很多遍之后,我就以为音乐变得不是创造性的东西,现在逐步以为做电影是一个创造性的事情,它不可能让你重复拍无数遍,拍电影对我现在来说最有兴趣。”
事情之余,马飞现在最大的爱好是饮酒、打游戏,身为陕北人的马飞,谈起饮酒,立时来了兴致。他绘声绘色的讲起刘伶醉酒的段子,抑扬抑扬的念出“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的对联。生活中,他和相声演员王声、音乐人王建房,组成了一个高大上的酒文化圈子,仨人隔三岔五的就一块儿聚会。
马飞阐明他饮酒的爱好,“酒能让人放松下来,让人肃清彼此之间的戒备心,在大都邑里生活很难做到这些,每个人都很小心,不会失落去礼节。你说在大城市生活好还是不好,大城市带给你体面生活,而对付我这种小城市终年夜的人就不太适应这种东西,但也有很多人特殊享受人与人之间来回周旋的这种关系。”
虽说离开延安已经快二十年了,马飞直言他还是喜好陕北男人的直率。“像延安这种三线城市的人和北京、西安比起来,给人觉得便是比较粗糙,但是这种粗糙让我以为很亲切,不是说我鼓励粗糙,但是我以为大城市里的人,有时候客气起来有点儿假,他们会礼貌地歧视别人,让人以为很难熬痛苦,但是延安那边人会比较直接,有抵牾会直接骂起来,这种直接会让我觉得很亲切。”马飞说。
如今马飞已经把西安当成了故乡,他用两种食品形容两座城市在贰心中的觉得,“洋芋叉叉和羊肉泡馍比起来彷佛不足丰富、不足激烈,羊肉泡馍这种食品给人觉得会比较刺激,吃一次就会让人印象深刻,确实太喷鼻香了。”
他向我剖析把西安当故乡的繁芜生理时说,“到北京往后,以为故乡该当是西安而不是延安,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生理,有可能是我的青春期在这里度过的,以是对这边影象比较深刻,以是会有这种觉得,西安彷佛有一种魔力,让出去的人都会怀念她。”
采访结束前,我们聊的话题又回到了他的音乐上。当我问到马飞,他做音乐想要传达若何的音乐理念时,马飞狠狠吸了一口烟,“我以为音乐啥也干不了,便是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让人高兴一下,让人从一种感情中跳出来进入另一种感情,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烟圈包裹着这句话散到空气里,马飞端起羽觞,我想起他的一句歌词:“你把羽觞端上,剩下的事咱来日诰日再讲。”我俩喷鼻香槟对撞,一饮而尽。
“风格不主要,说了实话才主要”——《时期人物》对话马飞
时期人物TIMES FIGURE=T
马飞=M
T:你当初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请你聊聊你早期的进程。
M:我是上陕西省艺校的时候开始弹吉他的,谈了几年之后我和同学一起组了个乐队,那时候是1999年,我们校区的传授教化东区在西影厂里面,在这个校区紧张是新招的影视班,美术班随后也跟了过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音乐有了一种分外的感情,大学虽然学的是油画,实在研究的是音乐。
T:在你的音乐道路上,对你影响比较大的音乐人有哪些?
M:最早的时候有个歌手叫张恒,张恒演唱过一首歌曲叫《天国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他还有一首歌叫《间隔》彷佛便是用方言演唱的,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艺校,听完了之后,我就以为非常好听,当时也没想过去做着这些东西,上大学的时候,听了王建房的《活着》,就想着拿方言来写歌,之前也没有想过拿方言写歌,最早玩乐队也是拿普通话写歌的。
T:我记得你彷佛说过“北漂”的时候是你离音乐最远的时候,这段经历对你的音乐之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M:在音乐方面的影响便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实在北京,我认识很多歌手,像马条、张玮玮、郭龙、苏阳,这些人实在对我帮助很大,尤其是张玮玮,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该当是2007年,我刚开始写歌,把写好的歌拿给他听,他以为挺好的,他也挺喜好的,但是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一定要悠着点儿来,不要把音乐当回事”,我当时有点儿不理解,但是后来随着韶光流逝我越来越以为他说的话很主要,负责对待,而越负责就会越紧张,越紧张的话越做不出好东西,放松才有这种可能性,不放松的话一点儿可能性都没有。
T:咱们陕西音乐人常会受陕北民歌和秦腔戏曲的影响,再加上西安是摇滚重镇,很多人都走了摇滚的道路,你彷佛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你选择走民谣这条路,你的音乐风格经历了一个若何的发展和转变?
M:在我看来,不要在乎风格,要在乎的是你自己,你是咋想的,你是不是说了实话,一旦撒谎话,别人能听出来,风格不主要,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形式是枪,心才是子弹,形式实在我一点也不在乎,至于我的音乐风格是民谣还是别的,都无所谓,而且我不会说是一贯坚持民谣道路,如果将来有一段韶光,我以为民谣不能抒发自己的情绪了,我有可能就会换一种风格,绝对不会由于现在盛行什么我就搞什么。
T:听你唱《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能觉得到陕北民歌里有种很凄凉的东西,听起来让民气里酸酸的,作为一个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你是怎么理解陕北民歌的?
M:我有一个习气,我喜好不雅观察别人的生活细节,这个歌我最早是在延安我家楼下的一个工地听一个农人工唱的,他用筷子串着三个很大的馍,用搪瓷碗端了一碗菜,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往工棚走,一边走一遍开始唱,我以为太好听了,他那个觉得不是在演出,他彷佛是给自己唱的,解闷呢,实在也便是给自己唱的,后来我才明白陕北民歌的浸染实在便是给自己解闷用的,你面对无人的土疙瘩梁的时候,抒发自己的情绪用的。
T:你唱过的很多歌特殊能表示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秘闻,你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M:我以为是朴实,朴实对绘画、电影、音乐这些艺术形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以是我也喜好看这种类型的电影,乐意写这样的音乐。
T:听你的音乐里很少涉及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是自然而然还是刻意为之?
M:关注点不在那些上面,一方面是我个人比较腻烦那些东西,看那些东西太多了,另一方面,说实话,别人比我写的好,以是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想要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听众,而我最熟习的便是身边的伙计,在街上碰着的普通人,我喜好不雅观察这些人,以是我对他们的生活细节也比较理解,创作起来素材也会比较丰沛。
T:我们把稳到你之前创作的作品中,都有非常多的陕西元素,有人认为西安方言是把双刃剑,西安话并不算生涩难懂,歌词里大量涉及本地元素,能唤起本地人的共鸣,但受地域局限很难真正在全国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对此你怎么看?
M: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不能为了取得大范围的影响而写歌,一方面这是违背良心的事情,另一方面,分开了方言我也没办法把歌写好,我也只能写我自己熟习的东西,如果说由于方言歌曲影响受到局限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同时我也以为音乐作品之以是会受到地域局限,也是由于作品本身不足好,拿美国村落庄音乐来说,这里面很多都是南部口音,也便是方言,里面也有很多鄙谚,但由于作品本身足够好,歌词和旋律的契合度高,演出的表现力强,也得到了听众的普遍认可。实在,方言音乐在中国也就最多二十年的历史,实在还是韶光比较短,随着遍地所言音乐人的涌现,随着更多的有才华的音乐人的加入,随着方言音乐人基数的增大,总会有一天方言局限终将会被冲破,听众不再见去由于演唱办法去判断好坏,而是关注到音乐本身,我相信这一天终将会来临的。
T:你的音乐本身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唱的是西安这方地皮上的风土人情,但却在西安以外的广大地区引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你以为这紧张是什么缘故原由?
M:我以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猎奇心态图新鲜,实在这也无可厚非,前一段韶光高晓松说,现在的很多听众属于喂养式听众,你给他馍他吃馍,你给他面他吃面,缺少独立思考能力,听什么音乐紧张凭市场的炒作和宣扬,过去我们那时候听音乐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品位去慎重选择的,由于要自己掏钱买磁带或者CD,以是会很慎重,听什么音乐你会考虑好了,才会买回自己听。
但现在不一样了,你想听什么网上随便可以听到,缺少了我说的过程之后,听众就会什么音乐盛行就听什么,现在很多听众都变成这样的了,这彷佛也变成了一个大趋势,作为音乐人来说,不是说要对这个趋势进行革命还是抗争,而是要更加努力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T:你现在在全国的演出非常密集,和一些精良的音乐人也有很多的交集,我们把稳到你和音乐人李志之间也有很多互动,你怎么看待李志这个人和他在这个行业取得的成绩?
M:我以为李志是个非常聪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也很有才华,我和他最大的不同是他很负责,对待音乐非常负责,他会去做很多详细的事情,比如经营团队,把他的音乐制作的各个项目都交给他的制作团队去做。
同时他也在花很大的精力在做音乐,在演出前他和乐队进行大量的排练,他对音乐的态度非常之负责,我以为中国须要这样的音乐人,在团队方面更职业,在音乐上更苛刻,我以为这种办法挺好的,也很厉害,据我所知崔健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彷佛不太适宜这种办法。
T:有人说现在是民谣的天下,你对民谣这个行业有些什么样的意见?
M:随着民谣歌手的陆续涌现,现在民谣确实是比较火,大家也乐意听这方面的东西,这些对民谣音乐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但在我看来外部环境的好坏跟民谣音乐人出好作品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可能会有更多的演出机会,但这和做好音乐本身没有关系,我以为民谣音乐人要想出好的音乐作品就不应该受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
T:我们知道你到目前为止一共就发行了一张专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歌曲数量不多但是传唱度很高,在这背后你对音乐品质的哀求是不是十分苛刻?
M:实在第一张专辑,我本身不是特殊满意,但也前前后后录了一年,用了一年韶光录了一张唱片,但是末了我还是不满意,但是,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一个阶段说一个阶段的话,任何人永久都不可能是一个完备成熟完美的人,你在某一个阶段体会感想熏染到的,只管即便把它做好就行了,纵然你回过分来创造那个东西有点傻,那也是一个记录当时状态的一个东西。
T:等你的孩子终年夜了,你会不会让他也从事音乐这条道路呢?
M:我以为年轻人要多考试测验,你才知道那个你更喜好,在没找到适宜自己的东西之前,没必要铆着劲在一件不喜好的事情上面,梦想这个东西实在是个很虚幻的事情,大家都说我要坚持梦想,梦想是个啥?梦想是可以替代的,你换一个梦想,它还是梦想,我以为一定要多考试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