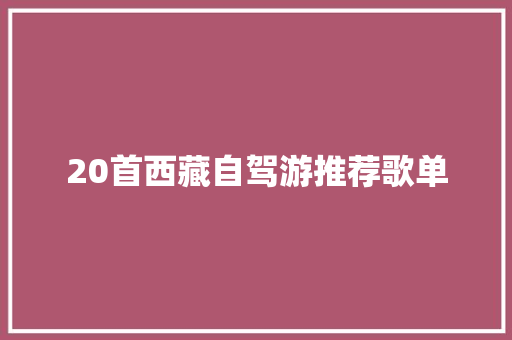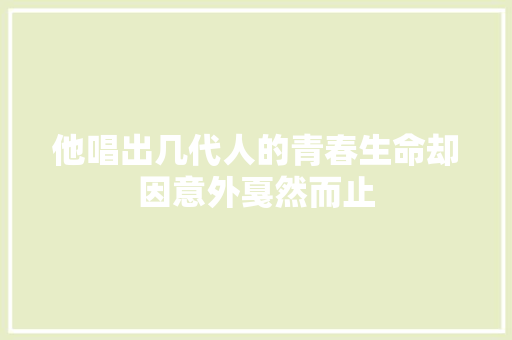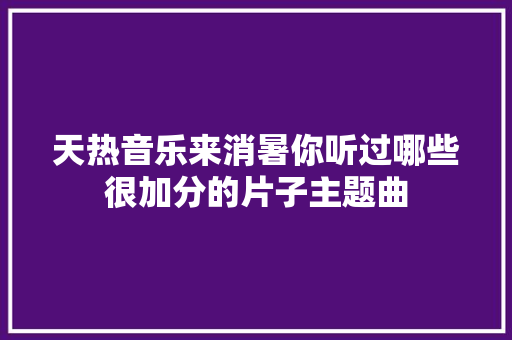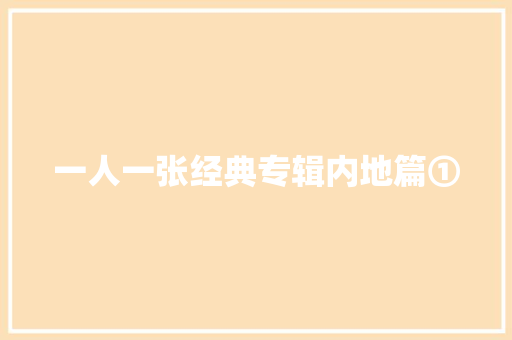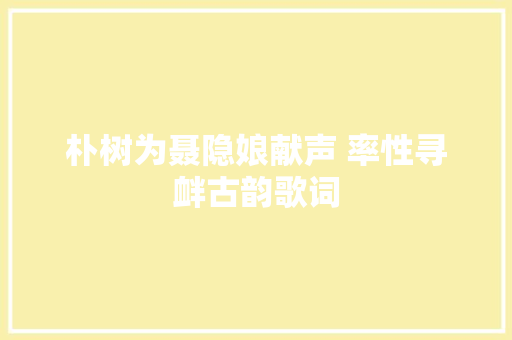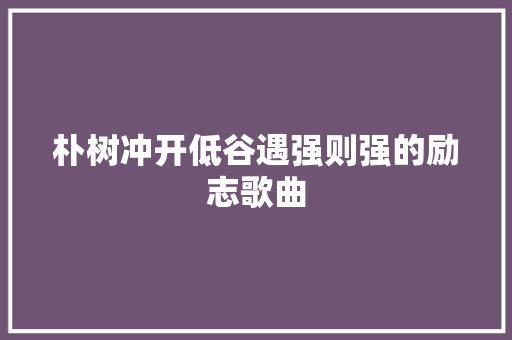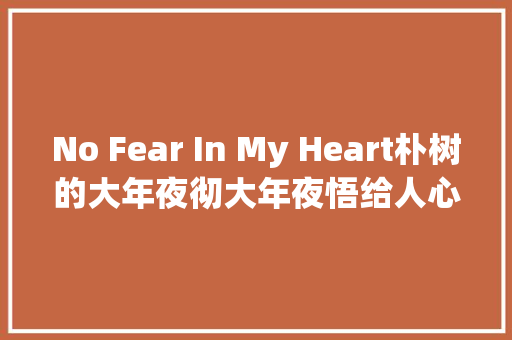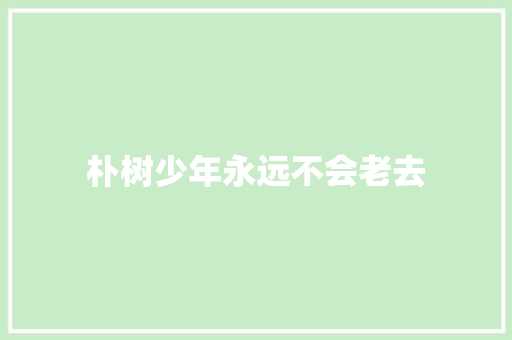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周开山。
上期内容,咱们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海峡对岸的民歌运动,它对后来的民谣、摇滚、乃至是全体华语音乐市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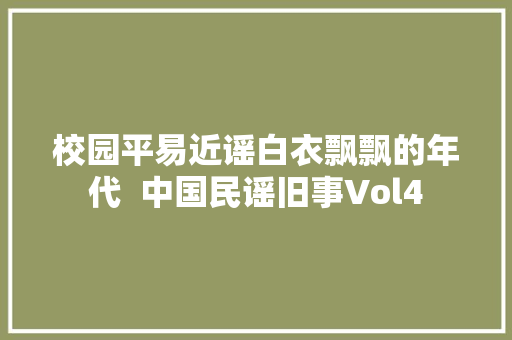
现在回望那个时期,实在也出身了三个不同流派:以陈达为代表的本土民谣,你依然能从林生祥、苏阳或者五条人、野孩子等乐队的音乐中寻到蛛丝马迹。而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等人所通报下来的空想主义火把,在周云蓬、小河、万晓利、张玮玮,以及更多人的身上得以延续。至于我们最为熟习的校园民歌,则在90年代的大陆迎来了复活。
上个世纪,早在邓丽君打开盛行音乐天窗的80年代,校园民歌就已随着海风飘向了大陆。通过一个弹着吉他,名为成周遭的女孩儿,人们听到了《童年》、《我的未来不是梦》等翻唱歌曲。
而得益于文化环境的松动,一些创作于上世纪中期的歌谣得以再度流传开来,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童谣。
此外,还有大量精良作品也于此时出身,例如《歌声与微笑》、《弯弯的玉轮》等,严格来说,它们都属于民谣。
只不过,在那个不知盛行音乐为何物的年代,没有人在意一首歌是什么风格。直到某天,一系列名为“校园民谣”的合辑发布,那些与青春紧密相连的歌曲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而这统统,都与一家名为“大地”的唱片公司有关。
大地唱片成立于1990年,名字源于Beyond的同名歌曲《大地》,由来自喷鼻香港的刘卓辉创办。可能有人不知道,《农人》、《情人》、《灰色轨迹》、《逝去日子》,乃至《交情岁月》、《甘心替代你》、《只想生平跟你走》等经典歌曲的歌词都出自他手。实在,前些年火热的“城市民谣”也出身于那个年代,乃至早于“校园民谣”。
刘卓辉(右一)
1993年,艾敬在大地唱片发行了专辑《我的1997》,其制作阵容在本日看来依然豪华:艾迪、张岭、臧天朔、刘效松、鼓三儿、王勇、何勇、陈劲等人都参与了录制。制作人黄小茂将其命名为城市民谣,与后来的校园民谣作了区分。
其直白大略,乃至有些流水账般的叙事风格,在当时却显得格外清新脱俗。就拿《我的1997》来说,一个脸庞姣美、笑靥如花的女孩儿,抱起木吉他絮叨着自己的经历和憧憬:从沈阳到北京,从上海到广州,还想早些去看看喷鼻香港这个十丈软红。时期年夜水中的少女心思,就这样朴素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科普两个小知识,Beyond的《情人》,便是当年的刘卓辉写给艾敬的。而所谓城市民谣的代表作,还有马格演唱,丁薇创作的《女孩儿与四重奏》,以及李春波的《小芳》。
言归正传,当改革的东风垂垂吹过,诗歌开始复兴,校园中的音乐氛围也逐渐浓厚。
80年代末期,“串校园”开始盛行起来,各个高校的学生聚在草地上,一唱便是一夜。而在黄小茂的推动下,大地唱片开始面向全国高校征集歌曲,并收到了极好的反馈。听说,大量的信件从各地涌来,歌曲小样则堆满了办公桌。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很愉快,也没有人乐意放工。在铺天盖地的信件和小样中,一个声音吸引了黄小茂,又打动了所有人。而这声音,来自一个名为王阳的青年,你也可以叫他老狼。
黄小茂
1989年,21岁的老狼参与了一支乐队,叫“青铜器”,高晓松是鼓手。在摇滚乐迅速抽芽的年代,他们很快便小有名气,乃至成了崔健、唐朝以及黑豹等乐队的暖场高朋。
青铜器
但和大多校园乐队的命运一样,毕业后,青铜器终结,主唱老狼则成为了一颗螺丝钉,混迹于朝九晚五的城市人流之中。当重复的生活一望无际,他创造自己还是喜好唱歌。于是,工程师王阳又成为了无业游民。直到在甘南待了一个月后,高晓松对黄小茂说:我的歌,必须老狼来唱。
1994年,《校园民谣1》发行,老狼贡献了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以及《流浪歌手的情人》。
由于这些歌,他开始频繁出入各大颁奖仪式,《校园民谣1》更是创下销量记录,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火了。第二年,老狼站上春晚舞台,还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只用20天便达到23万张的销量,成为当年在大陆发行量最高的专辑,没有之一。
只不过,老狼彷佛并不愿意就这么红下去,他阔别了唱片市场,直到七年之后才发行了新专辑《晴朗》。个中收录了许巍的《晴朗》、高晓松的《麦克》,以及郁冬的《虎口脱险》。
再后来,他又认识了一帮朋友,开始玩乐队,并成为在舞台下、照片中和蔼可亲的狼哥与狼师傅。前些年,狼师傅在一干人等的鞭策下上了综艺,拉着一堆摇滚老炮儿唱了首礼物,场面动听。
黄小茂说:“歌手有两类,一种是创作型的,也便是现在的唱作人;另一类是职业歌手,技能很完美,自己不写歌。老狼跟别人不同的是,险些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像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唱的歌都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的确,老狼并不是一个创作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像一个比较成功的“角色扮演者”。只管如此,他依然代表了一个时期,代表了几代人难以被复刻的青春。那些风花雪月却又朴拙细腻的歌谣,不仅影响了我的全体青年时期,也会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这个天下上,还有诗意和美好。
《校园民谣1》的出身,捧红了老狼和《同桌的你》。但还有一首歌,它并没有被那样广泛传唱,却也是很多人对校园民谣的宝贵回顾,这便是浩瀚吉他初学者绕不开的名字——《青春》。
沈庆的嗓音谈不上好,唱功也不算精良,站在唱片公司的角度来看,估计永久也成不了职业歌手。但回过分来,与宝岛的校园民歌一样,如果没有他们略显瑕疵却又朴素朴拙的声音,那些作品便也失落去了最动人的色彩。
在沈庆的作品中,弥漫着一股青春期特有的、少年老成的忧伤。这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同类作品的基调,也与后来所谓的“转基因民谣”有着明显不同。除此之外,沈庆还是校园民谣的主要推手。作为大地唱片约请的音乐企划,他让那些自娱自乐的学生投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音像制品。而他的文案和宣扬,也为校园民谣的厚积薄发起到了相称主要的推广浸染。
遗憾的是,2022年5月,由于不能打车,沈庆在骑行外出时发生意外,在转院就医的过程中不幸离世。他预备了多年的音乐剧《苏东坡》,也由于某些缘故原由未能登场。
人生有的时候便是这么荒谬,面对死活,那些你曾琐屑较量和念念不忘的东西都不再主要。不论如何,沈庆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回顾,那些美好而又忧伤的旋律也会连续流传下去,祝他在天国快乐。
除了前文提到的几位之外,若要追忆那个梦幻一样平常的年代,还有一个名字也无法绕过,他叫郁冬。
如果说高晓松和沈庆替我们描述出一段青春洋溢、白衣飘飘的岁月,那么郁冬的音乐则是阳光下的阴影。
《露天电影院》、《赤色天空》、《虎口脱险》、《在劫难逃》,以及《来自我心》。你能从入耳到难以化开的忧伤、绝望和当仁不让,它从校园蔓延到了象牙塔外,比同期间大略明快的怀念和感伤又要深刻一些。虽然年事最小,但郁冬的才华是那么刺目耀眼,以至于多年之后,校园民谣时期的亲历者们仍不谋而合地将其视为天才。
1995年,郁冬因《露天电影院》而得到最佳创作歌手奖,同名的主打歌也成为了年度金曲。但他复苏、疏离而又自得其乐般的性情也让这张专辑成为了绝响。在极少的宣扬照中,郁冬基本不笑,安静而又孤独。
是的,天才总会感到孤独,但没有人会想到,他终极会以那样断交的姿态走进了孤独。
2001年,郁冬的人生迎来了过山车般的转变。在工人体育馆外,他驾车掉头,意外撞倒了一位老人,当医护职员赶到时,老人已然断气。郁冬因交通闹事罪被判了刑,自责、腼腆和后悔也让他为自己的音乐生涯画上了句点。
此后,郁冬选择偃旗息鼓,而他生平的石友老狼则始终等待着他的复出。那些熟习的旋律依然悦耳,老狼的歌声也愈发沉稳。只不过,在唱到郁冬的歌时,他还是偶尔哽咽。
在《校园民谣1》发行之后,由于盗版的专横獗以及职员出走,大地唱片陷入困境。于是找来一些商业歌手,在余热未消之前又推出了部分续集。但歌曲的同质化,乃至是质量下滑,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疲倦使得校园民谣迅速归于沉寂。
不过,在这群专业歌手中,还是有一个名字带来过久远的冲动,他叫李晓东。
上世纪80年代,李晓东还是个爱在桥下弹琴唱歌的少年。直到某天,一个人对他说:想不想录磁带?
于是,在1988年,年仅十九岁的李晓东成为歌手,还持续发了3张名为《星座》的合辑,名声大噪。
不过,真正的转变则是在1994年。李晓东被推举到大地试唱,一开嗓便被定为《校园民谣2》的紧张歌手。唱片发行后,其反响之热烈竟丝毫不亚于第一张合辑。
毫无疑问,这离不开李晓东对高晓松作品的演绎。在他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真的身处冬季校园,看到了俊秀的女生和白发的师长西席。而《关于空想的教室作文》也早已成为了无数民气底最宝贵的影象。它不只是关于空想与教室,更关于交情和人生。
那些空想实现了吗,那些人又在哪儿呢?当年的我不得而知,如今却又说不出话来。
幸运的是,当李晓东再次唱起这些歌谣,它们所带来的冲动竟没有丝毫变革。他在三里屯开了酒吧,和驻唱歌手一起出了张名为《男孩女孩》的合辑。再后来,又改了名字(李丰溢),办了自己的专场,还在前几年登上了综艺的舞台。
光阴流逝,虽然李晓东从来都不是所谓的民谣歌手,但他的涌现,毫无疑问是校园民谣期间浓墨重彩的一笔。
实在,就在校园民谣风起云涌的同一韶光,有一个名字也不该被遗忘。他是极具思想的空想主义者,也是游走于摇滚、民谣、戏剧与电影之间的先锋艺术家。
他叫张广天,由郝蕾所唱的《氧气》便是他的作品。
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同样经历了光芒万丈和戛然而止的另一边,崔健、张楚、许巍等人也为民谣找到了不同的方向。
插句题外话,如果你看过本人前几期节目乃至更早的内容,大概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在说,摇滚乐和民谣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而单独做这个系列,实在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厘清它们之间的联系。
说到底,如果民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么摇滚便是它们身上五颜六色的衣裳。
言归正传,1996年,宋柯从美国回到北京,和高晓松一同创办了麦田音乐。年轻的叶蓓成为了麦田旗下第一位女歌手,并和刘欢、老狼、小柯、零点乐队等人共同录制了一张合辑——由高晓松卖力全部词曲创作的《青春无悔》。
那一年,叶蓓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家里播放着肖邦、舒伯特以及柴可夫斯基,位于左家胡同的百灵Pub,则是她勤工俭学的驻唱地点。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她遇见了还没发福的高晓松——一个正在四处寻觅歌手的创作者。
在找了一大堆女歌手试唱之后,在老狼的建议下,叶蓓成为了《青春无悔》中的女主角,也成为了校园民谣期间的代表人物。
此后,大三学生叶蓓就算正式出道了,并且顺风顺水。她整天跟老狼、高晓松、郑钧、朴树、宋柯等人混在一起,像个跟屁虫。1998年,在这群貌似极不靠谱的青年的帮助下,叶蓓发行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纯洁年代》,收录了高晓松、郁冬,以及朴树等人的部分作品。如你所见,这张专辑的名字,也是对那段岁月最好的表明。
1999年,由于对电影《红白蓝三部曲》的喜好,高晓松灵机一动,便有了著名的“麦田三原色”。白是朴树,红是尹吾,而由叶蓓自己创作、写给初恋的《蓝色》,收录在2001年的专辑《双鱼》中。制作人许巍,鼓手窦唯。也是在叶蓓所有作品里,我个人最喜好的一首,她的创作才华,毫无疑问是被歌手的身份粉饰了。
前不久,狼师傅搞了场直播,场面温馨动听。当所有人团坐在一起,叶蓓依然像个小姑娘。从她身上,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蓝色,也回到了那个久违的纯洁年代。
说到女歌手,那么还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于我而言,她的歌声曾带来过难以形容的震荡和冲动,但对这个天下来说,却是巨大的遗憾,她叫筠子。
筠子本名武雅筠,94年毕业后便去了新加坡学习工商管理。1997年,她拿着自己存下的钱,返国成为一名自费歌手。也是在这一年,小柯为她写了《一起做吧》,获奖无数。在小柯的引荐下,筠子认识了高晓松,他们相互欣赏,对方说要给她做一张专辑。
小柯
2000年春天,筠子身边的人换成了汪峰。终于,在辗转几家唱片公司之后,一张名为《春分立秋冬至》的专辑在京文旗下发行了,收录了由高晓松、朴树、汪峰、沈庆,以及小柯等人创作的10首作品。绝不夸年夜地说,如果那一年有四季,一定都在筠子的歌声里。但令人惋惜的是,那一年的春夏秋冬,也被她一同带走了。
2000年9月,27岁的筠子去世在了她未曾歌唱过的夏天,烦闷症的折磨以及情绪上的接连打击让她选择离开。而就在10天之前,她还琢磨着让许巍帮自己写歌。斯人已逝,留下关于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和谣言八卦。当原形被淹没在声讨中,鲜少有人把稳到,悲剧的首恶还是烦闷症。在之前关于尹吾的内容里,我已经表达过一些肤浅的不雅观点,就不再多说了。
二十年弹指一挥,那个唱着“春天如此短,一去不再来”的筠子也早就被大众遗忘。《冬至》里那些问题的答案找到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真有天国,她一定在那儿放声歌唱。
如果说筠子的离开带走了四季,也带走了校园民谣末了的荣光,那么水木年华便是那段岁月的守墓人。
1989年,18岁的卢庚戌以辽宁省营口市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受大明星宋柯的影响,小卢拿起了吉他,在琢磨一年之后,便得到了校吉他大奖赛的第二名。此后,卢庚戌便成为了一名创作歌手,在十年韶光里,他组了乐队、辞了职,终于在世纪之交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未来的未来》。
专辑反响不错,但卢庚戌的高音一贯不太空想,于是,他找到正在某部门混日子的校友李健。李健的父母都是京剧演员,以是他从小就在艺校读书,在学习京剧之外,还练了一手古典吉他。
高三那年,少年李健又学了几个月民族唱法,顺手拿了个全国中学生汇演的第一名。在保送清华的同时,还省去了高考和选学校的烦恼。但在之后的韶光里,不管是所谓的摇滚盛世,还是白衣飘飘的年代,他都只是个察看犹豫者。
直到那天,歌手卢庚戌找到了闲得蛋疼的李健同道,水木年华出身了。2001年,他们发行了专辑《生平有你》。
个中,由卢庚戌创作的同名歌曲火遍了大江南北,水木年华也成为了唯一能和羽泉相提并论的华语组合。但对我个人来说,相较于大家耳熟能详的《生平有你》和后来的《在他乡》,还是《中学时期》中那股绝不造作的校园情怀更加动人。
在两张专辑之后,由于创作上的不合,李健离开了。他要去往更大的舞台,去才华横溢,去光彩夺目。卢庚戌依然守着水木年华,身边的队友交往来交往去,只有他还在歌颂青春。
前两年,当卢庚戌和缪杰的水木年华站上综艺舞台时,他们不出意外地背上了骂名。有人在笑,有人在喷,可我笑不出来,哪怕青春在成年人的天下里,不过是一段荒诞青涩的光阴,哪怕在这样的年纪歌唱青春,彷佛是一件多么稚子的事情。但我们彷佛忘了一个问题:等到同样的年纪,大家还敢为了青春歌唱吗?
末了,来聊聊朴树。
1996年,当卢庚戌还在某设计院熬夜画图时,麦田音乐成立了,老板是曾和他一起茬琴的宋柯与高晓松。
某天,一个长发遮面,看上去极其内向的青年找到了他们。与其他来推销自己的歌手不同,他没录demo,只抱了一把吉他。更怪的是,当这二位听完朴树的作品,并没有要买歌的意思,而是直接把他签了。
听说,宋柯哭了,梨花带雨。而朴树的才华,也让心比天高的高晓松自愧不如。后来,唱哭了宋柯的白桦林和那些花儿霸占了各大排行榜。但我真正开始听朴树,却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2003年,朴树发行《生如夏花》,火得一塌糊涂,也被那个省出饭钱去淘磁带的小孩带回了寝室。
遗憾的是,对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来说,他只是个在电视上打扮怪异、略显笨拙、并且每次都在唱白桦林的盛行歌手。既然如此,就免不了比较。
对当时的我来说,抛开那些传说中的名字,哪怕与同期间的周杰伦、羽泉、谢霆锋、孙燕姿、乃至林肯公园的专辑相较,充斥着广告味儿的《生如夏花》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乏善可陈,直到我听见了那张更早的《我去2000年》。
90年代末期,当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压力也就席卷而来。年轻人对新世纪的焦虑和迷茫,逐渐取代了青春感伤和风花雪月。在摇滚乐陷入长久沉寂的同时,校园民谣彷佛也陷入了不同的窘境。
不过,就在二十世纪的末了一年,朴树带着《我去2000年》涌现了。这是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专辑,也是一张无法用风格定义的唱片。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无数做梦的青年。很难想象,一个看上去与天下扞格难入的人,竟然将忧伤、憧憬、愤怒、绝望等感情抵牾而又完美地融入音乐,还将时期的阵痛与社会的明暗通通写进诗篇。
这所有的东西汇成一张伟大的唱片,向着世纪之交发出恢弘的声响。
请体谅我无法向你详细推举某一首曲目,由于整张专辑都是宝藏。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朴树的涌现,也如二十年前的罗大佑一样平常,革了校园民谣的命。
可惜的是,也仅仅是校园民谣。与同期间精美的港台盛行音乐比较,他的思考还是太多,声音还是太小。在恶俗的网络歌曲席卷至每一辆大巴之前,那些极具诗意和自省,充斥着诚挚与割裂的作品,终极,还是被淹没在他自己的成名作下面。
二十多年过去了,朴树统共只发了三张专辑。值得光彩的是,他没变,彷佛还走出了阴霾,不再纠结世俗与空想之间的巨大落差。他也终于创造,音乐并不是生命的全部:缺钱就上综艺,到点儿就回家。可能只有这样的生活办法,才能让自己回归大略。
遗憾的是,那些经历过期期剧变的青年,大多成为了朴树笔下面无表情的“植物人流”。或许,在菜市场里,在人行道上,在他们冷漠的脸庞之下,也曾有一段白衣胜雪的无悔青春。
我是周开山,感谢你的不雅观看,咱们下期再见。
参考资料:
我们唱 - 叶三
知中4:民谣啊民谣 - 苏静
沙沙成长 - 郭小寒
迢遥的乡愁 - 重返61号公路
校园民谣志 - 李鹰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