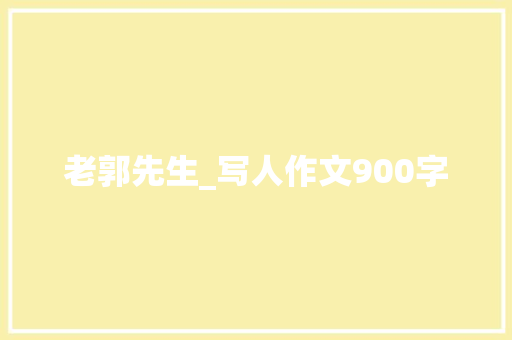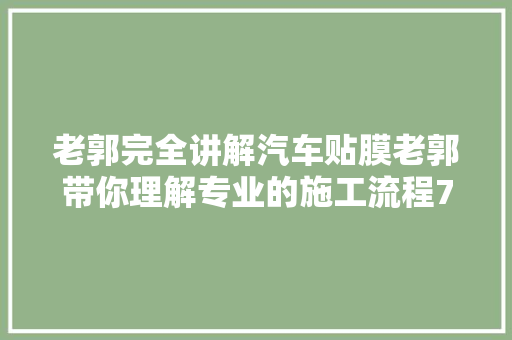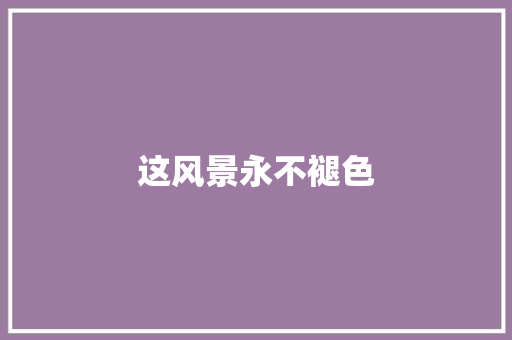《夜行记》这段相声中塑造并讽刺的是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物形象,侯宝林与郭荣起在各自演出中都融入了独占的风格。
侯宝林在与郭启儒差错使这段活的时候节奏紧凑、抓人,在描述画面感方面尤为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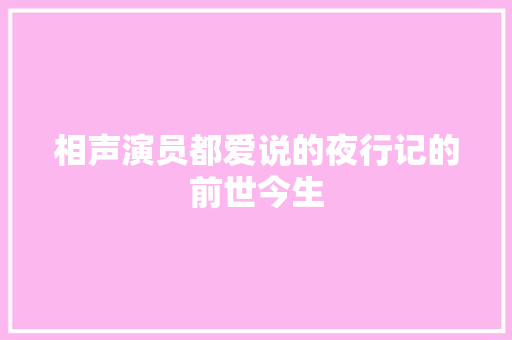
郭荣起与李寿增两位寿字辈艺人使这段时,则带有浓郁的津派相声特点,措辞普通,铺垫细致,刻画人物形象细腻丰满,可谓各有千秋。两个不同版本的演绎在当年首演即大得胜利,并由此引发了版权之争。要知道在相声界中“要活”和“捋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子。
“要活”是指某位演员的某个段子深受不雅观众喜好,同行也想演的话就须要主动请示对方是否可以让我也使这块活,两人有交情的话不但欣然赞许,还能把使活时须要把稳的点和整段的“册子”都毫无保留的供应。
“捋活”截然相反,在没有征得原演出者赞许的情形下,擅自演出其“把杆儿活”,这种行为在旧社会相声行内最为不耻,也是同行所不能容忍的。而这两位名家前辈之间既不存在“要活”也不存在“捋活”,但究竟《夜行记》这个段子该归谁所有,或许很多老相声不雅观众都很难说清......
事实上,《夜行记》这个段子的版权并不完备属于侯宝林或郭荣起。事情缘由是这样的,1955年随着《城市交通规则》的履行,在北京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业余文艺宣扬队中由朗德沣、陈文海、蒋清奎、贾鸿彬、侯伯照、李培基等交警联合创作出了《夜行记》,目的在于宣扬遍及《城市交通规则》。作品在1956年的一次庙会演出中被一位创造,随后全文刊登在《北京》上,刊登后大受读者欢迎,后又被其他报社相继转载。险些是在同一时候,侯宝林和郭荣起都看到了这个段子,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两位名家前辈对《夜行记》进行了二度创作,并加入个人理解。侯宝林的版本是在原来作品上的精雕细琢,而郭荣起师长西席则是借用了传统活《怯拉车》的技巧,做了重新改编。也险些是在同一时候,两人将这个段子带上了舞台。当时信息不是很畅通,两人就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形下都改编上演了这段节目,形成了不同的风格。随着节目空前火爆的演出效果,也就产生了所谓的版权之争。这也给相声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两位名家前辈都认为这个段子所有权该当归自己。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在相声界行内照样以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时至今日,相声界行内对《夜行记》这个作品的所有权仍旧不明,只能说属于当年那几位业余文艺宣扬队的交警们。实际上,相声段子都是老祖宗留下来,再融入一代代艺人创作演出的精华。传统段子也好创编段子也罢,该当属于全体行业,而非被一己独占。
喜好老郭相声的不雅观众基本都听过《夜行记》。相声是前辈们创作并且在磨合中不断变革的,郭版的《夜行记》脱胎于传统相声《夜行记》,不过只保留了原来段子的主线框架, 在内容上与时俱进的做了大篇幅的编削,得到了不雅观众的认可。老和@卧龙残雪龙残雪 评道:
老郭真敢改,险些把全体段子翻了一遍,包括底也动了,现在说老郭对这个段子的改编算成功还为时尚早,但至少在过几十年,提起《夜行记》,还会有不雅观众记得郭德纲也改过一版,并且挺可乐的,这便是一个作品成功了一半。
说这个段子老郭改的好并不一定就说他引入了当代的一些东西,关键是他把作品深深的打上了郭式烙印,一上来先把不雅观众们的感情完备调动起来,直接进入了正活,接下来大胆的抛弃了原作品中买自行车以及看电影的场景,而把一个没有钱,但却想开汽车;开摩托耍酷的人塑造的淋漓尽致,把老郭最善于塑造的“小市民”形象完完备全的展现在不雅观众的面前,原作品中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啥地方都响,而老郭则改成了一堆废铁攒了个摩托,显然比原作品的车子更破,还加上了侯震那个口头禅“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给作品又增色不少,而关于驾驶执照那一部分更是完备符合现状,足见老郭对这个段子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也足见老郭比前面演员的功力深厚许多,最经典的还是底,原来的包袱是我掉沟里了,而现在,掉沟里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人们也听了太多遍这个段子,用这样的底很难引起不雅观众的共鸣,于是他大胆的把原来的包袱改为老头把盖子盖上了,相声中的底只有出人意料才能让不雅观众笑出来,老郭深谙此道,末了的底可以说是一个很响的包袱,希望老郭将来能在演出几次这个段子,我相信,他这个段子一定会被更多人所认同,也会让更多的人记住郭版《夜行记》的。
七年过去了,《夜行记》仍旧是老郭所有作品里经典中的经典,可以和《我这一辈子》,《西征梦》相媲美了。不过既然本日先容这个段子,就一定会说说它的其它版本,当年这段随处颂扬的《夜行记》还引发了侯宝林与郭荣起两位名家前辈的版权之争。
《夜行记》这段相声中塑造并讽刺的是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物形象,侯宝林与郭荣起在各自演出中都融入了独占的风格。
侯宝林在与郭启儒差错使这段活的时候节奏紧凑、抓人,在描述画面感方面尤为真切。
郭荣起与李寿增两位寿字辈艺人使这段时,则带有浓郁的津派相声特点,措辞普通,铺垫细致,刻画人物形象细腻丰满,可谓各有千秋。两个不同版本的演绎在当年首演即大得胜利,并由此引发了版权之争。要知道在相声界中“要活”和“捋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子。
“要活”是指某位演员的某个段子深受不雅观众喜好,同行也想演的话就须要主动请示对方是否可以让我也使这块活,两人有交情的话不但欣然赞许,还能把使活时须要把稳的点和整段的“册子”都毫无保留的供应。
“捋活”截然相反,在没有征得原演出者赞许的情形下,擅自演出其“把杆儿活”,这种行为在旧社会相声行内最为不耻,也是同行所不能容忍的。而这两位名家前辈之间既不存在“要活”也不存在“捋活”,但究竟《夜行记》这个段子该归谁所有,或许很多老相声不雅观众都很难说清......
事实上,《夜行记》这个段子的版权并不完备属于侯宝林或郭荣起。事情缘由是这样的,1955年随着《城市交通规则》的履行,在北京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业余文艺宣扬队中由朗德沣、陈文海、蒋清奎、贾鸿彬、侯伯照、李培基等交警联合创作出了《夜行记》,目的在于宣扬遍及《城市交通规则》。作品在1956年的一次庙会演出中被一位创造,随后全文刊登在《北京》上,刊登后大受读者欢迎,后又被其他报社相继转载。险些是在同一时候,侯宝林和郭荣起都看到了这个段子,并对它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两位名家前辈对《夜行记》进行了二度创作,并加入个人理解。侯宝林的版本是在原来作品上的精雕细琢,而郭荣起师长西席则是借用了传统活《怯拉车》的技巧,做了重新改编。也险些是在同一时候,两人将这个段子带上了舞台。当时信息不是很畅通,两人就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形下都改编上演了这段节目,形成了不同的风格。随着节目空前火爆的演出效果,也就产生了所谓的版权之争。这也给相声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两位名家前辈都认为这个段子所有权该当归自己。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在相声界行内照样以闹出了不小的风波。
时至今日,相声界行内对《夜行记》这个作品的所有权仍旧不明,只能说属于当年那几位业余文艺宣扬队的交警们。实际上,相声段子都是老祖宗留下来,再融入一代代艺人创作演出的精华。传统段子也好创编段子也罢,该当属于全体行业,而非被一己独占。
老郭真敢改,险些把全体段子翻了一遍,包括底也动了,现在说老郭对这个段子的改编算成功还为时尚早,但至少在过几十年,提起《夜行记》,还会有不雅观众记得郭德纲也改过一版,并且挺可乐的,这便是一个作品成功了一半。
说这个段子老郭改的好并不一定就说他引入了当代的一些东西,关键是他把作品深深的打上了郭式烙印,一上来先把不雅观众们的感情完备调动起来,直接进入了正活,接下来大胆的抛弃了原作品中买自行车以及看电影的场景,而把一个没有钱,但却想开汽车;开摩托耍酷的人塑造的淋漓尽致,把老郭最善于塑造的“小市民”形象完完备全的展现在不雅观众的面前,原作品中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啥地方都响,而老郭则改成了一堆废铁攒了个摩托,显然比原作品的车子更破,还加上了侯震那个口头禅“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给作品又增色不少,而关于驾驶执照那一部分更是完备符合现状,足见老郭对这个段子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也足见老郭比前面演员的功力深厚许多,最经典的还是底,原来的包袱是我掉沟里了,而现在,掉沟里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且人们也听了太多遍这个段子,用这样的底很难引起不雅观众的共鸣,于是他大胆的把原来的包袱改为老头把盖子盖上了,相声中的底只有出人意料才能让不雅观众笑出来,老郭深谙此道,末了的底可以说是一个很响的包袱,希望老郭将来能在演出几次这个段子,我相信,他这个段子一定会被更多人所认同,也会让更多的人记住郭版《夜行记》的。
七年过去了,《夜行记》仍旧是老郭所有作品里经典中的经典,可以和《我这一辈子》,《西征梦》相媲美了。不过既然本日先容这个段子,就一定会说说它的其它版本,当年这段随处颂扬的《夜行记》还引发了侯宝林与郭荣起两位名家前辈的版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