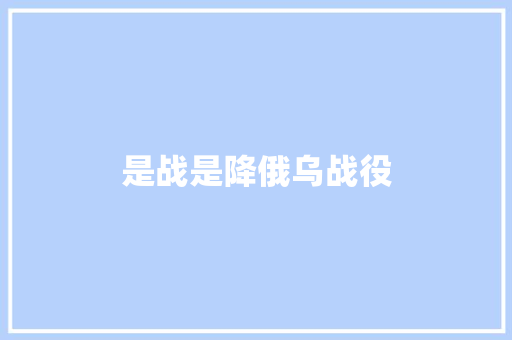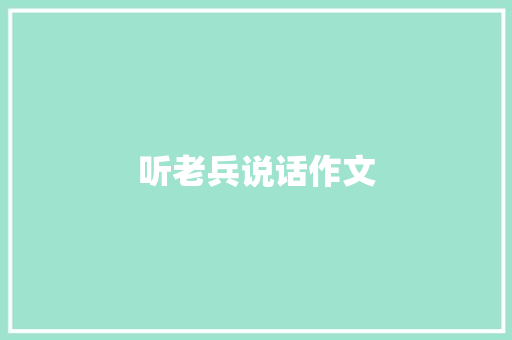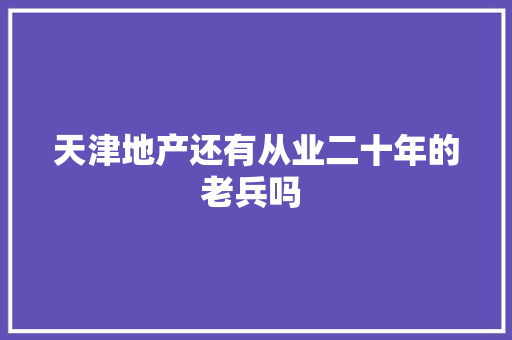这些老兵中,有人戴着帽子,上面写着“中国印度远征军”的字样;有人胸前挂着“抗日英雄”的纪念章;还有人穿着印有“抗降服利70周年”的纪念衫。一出场,不少人就围着他们问东问西。
不多时,广州这个放映大厅就要首映一部名叫《战魂》的记录片。这部时长86分钟的电影,记录了广州、云浮等地7名国军老兵的抗战历史和当下生活。个中两名主角就在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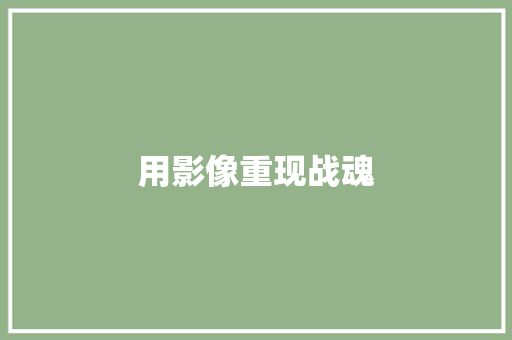
“国破山河之际,他们以血肉之躯迎上去。这便是战魂。”记录片的主创蒋能杰说,“抗降服利70年,他们还是被遗忘的一群。”
参加首映的人授予该记录片更多意义。有人评价道:“这是抢救老兵,也是抢救历史。”
这部电影便是让抗战老兵自己说话
7月4日下午3点一过,灯光暗下来,歌声环抱大厅。
“石榴花顶上石榴开,打到仇敌开了花……”屏幕上,抗战老兵黄浪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起来。
迎着射来的光,中等身材的蒋能杰站起身,面对众人,说了几句开场白:“我不是导演,记录片不导也不演,便是记录,让人瞥见。我要回归个人,记录老兵的家庭,记录他的过往、现在。”
这是蒋能杰拍摄《战魂》的初衷。这位1986年出生的拍照师,操持制作一系列关于老兵的记录片,《战魂》是第一部。
蒋能杰讲完,影片中黄浪的《石榴歌》也唱完了。这首歌是黄浪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学会的。那是1939年年底,他还只是个少年。而今,他已经90岁了,牙没剩几颗。
“第一次粤北会战,满眼都是尸体,那些尸体,国军的尸体,老百姓的尸体,猪牛羊的那些尸体,我们4个团只剩下两个团。”在片中,老人不敢直视镜头,“当年一起参加少年队的10多个同乡再也没回来”。
镜头不断切换。片中的7名老兵,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的抗战史。
“双髻山顶被仇敌封锁了,溘然我脑后嘭地震了钢盔一下,原来是钢盔被打凹了一个大洞,防雪帽也被铲去了,我伸手往头一摸,枪声又响起了,周围到处子弹乱飞……”17岁替哥哥当兵的黄配铭在镜头里摸着头,声音洪亮,模拟着当时的场景,脸上的皱纹随着抖动。
然而,在一个个悲壮的故事后面,镜头还切换到漆黑的小房子、破旧的棉袄、中风的腿脚、自己做饭自己吃的孤单。
这些镜头里的老兵,头发花白,老人斑比眼袋还大,与一样平常老人并没什么差异。只有在提到抗日胜利的少焉,才能从布满皱纹的眉宇间,依稀创造麦克阿瑟说的那种“老兵不去世”的气质。
蒋能杰正是被老兵的现状打动。5年前,他在湖南老家拍摄空巢老人时,有时创造了一群“国军抗战老兵”。这些老兵不仅缺少经济来源,乃至很多是90多岁的高龄空巢老人,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冲击,更让他们在精神上充满恐怖与自卑。
“活得没有肃静!
”蒋能杰脸涨得通红,双手往前一划,手微微颤动。
这位关注社会现实的拍照师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大鸣大放”时,身为西席的爷爷站出来说了自己不认同大跃进的不雅观点,接着,就被打为右派,关进牛棚,末了自尽。不过,这位倔强的老人始终不改口。蒋能杰从爷爷身上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
从2010年开始,打仗了近百名抗战老兵后,蒋能杰及其团队陆续呈现《战魂》《龙老生平》《我的河山我抗战》一系列关于抗战老兵的记录片。只管时时时有关部门要“看看他在做什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部电影便是让抗战老兵自己说话。”他不止一次说。
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太少了
枪炮声中,1945年9月3日到了。这一天,是中国公民抗降服利的日子。电影中的每一位老兵,都讲到这个日子。险些每一位老兵,在讲述胜利的一刻时,脸上都洋溢着光彩。
一讲到胜利的场景,电影中一位老兵伸开仅剩3颗牙的嘴哈哈大笑起来,纯白的长髯毛随着一上一下抖动。“到处都燃着鞭炮,我们每个人都有15斤糯米,这是最高兴的事了。”老兵比划着,原来坐在那一动不动的身体溘然就有了活力。
还有一位老兵笑眯了眼讲道:“日本仔屈膝降服佩服了,每个人都以为欢畅啊。我们就不用上沙场喽,不用上沙场就不用去世喽。”
不过,台下不雅观影的老兵,并未像电影中那么动容。老兵梁振奋,只有在传来飞机轰炸声时,才抬开始,张着嘴,去世去世盯着画面。71年前,这位老兵是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38师谍报队中尉,参加了1944年滇缅反攻。在战役中,老人的很多战友,被敌机炸去世。不过,他的故事并没有涌如今《战魂》中。
记录片中,“胜利”不属于这些老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一度被遗忘。就像梁振奋,在全体不雅观影过程中,一贯戴着一顶印有“中国印度远征军”的帽子。仿佛一摘下,大家就不知道他的历史。
10年前,为欢迎抗降服利60周年,南京航空联谊会理事陈功拍摄了记录片《血捍长空》。该片播出后,不雅观众很震荡:“国民党竟然还有空军,还参加过抗战?”陈功当时听了这种话,恨不得找到这人打一架。
“我们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太少了。”影片放映到一半,一名志愿者嘀咕道。
蒋能杰在偶遇抗战老兵之前,对这一段历史也不熟习。当打仗一位位老兵后,他在抗战老兵记录片的策划书里写道:“去世亡大概并不是最恐怖的事情,比去世亡更恐怖的是冷漠和遗忘。”
“这是一场与韶光赛跑的抢救工程。”他曾这样交代拍摄团队。这些老兵年纪已经很大了,剩下的不多了,留给他们的日子已经很少。
然而,记录并不顺利。
一位老兵一见摄制组的人问起当年的历史,便立即遐想到“政治审查”,一下子惶恐起来,反复地说“当年都已经交代了,你怎么还来问这个?我都已经交代好多遍了”。这让蒋能杰有种难以名状的愤懑。
一位95岁的老兵,总是会说“过去就过去了”。这位18岁就参加抗战的老兵,对着镜头,谈到被劳改30年时,紧张地双手抱头说:“如果你提及旧时的事,就认为你还是那时的反动思想,这些东西不要讲了,提都不要提”。
有志愿者得到一位老兵的线索,就找到家中,“结果怎么问老人都不回话”。
不过,有些镜头,始终未涌如今《战魂》中。蒋能杰也故意回避1945年9月3日往后的一段历史,更多放在老兵抗战的讲述上,以让人不要“忘了老兵曾流的血”,“从来没做过亡国奴”。
他们须要物质救助,更须要精神上的认可
镜头拉近,放大的“抗日英雄”纪念章定格在荧幕上。
老兵何焕九握着木棍,“嚯嚯”地喊出声,纪念章随着抖动的衣服随着一上一下地起伏。他在模拟当年班长教他们若何拼刺刀。
他今年98岁,20岁参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93师,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现在帮儿子看竹器店。“台儿庄太惨了,拉锯战,一拉一退……”话还没说完,老人开始叹气,拉近的镜头里,浑浊的眼睛充满着泪水。
这枚“抗日英雄”纪念章,是志愿者送给他的。每逢参加主要活动,或每次出镜,他就将纪念章别在胸前,只管这枚纪念章并非官方付与。蒋能杰回顾说,有些抗战老兵戴着志愿者送的纪念章,在村落口一遍一各处走,“曾经的‘兵痞’终于扬眉吐气”。还有一位老兵,直至去世时,仍在床头柜子中藏着一枚“抗日英雄”纪念章。
曾有媒体宣布,200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役胜利60周年,国家颁发60周年纪念章,共发行60万枚,甚少有国军抗战老兵得到纪念章。广州财政局退休官员张润进,在该市纪念大会上领到了纪念章。第二天,干系单位找到他并收回了纪念章,情由是他虽参与抗日,但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队,不在八路军、新四军。张润进是1949年才叛逆成为解放军的。
2013年,民政部颁发《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的文件。这份文件,被部分媒体及志愿者称为“人性关怀的阳光,终于照进了这个长期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蒋能杰用镜头记录了老兵龙运松对此的反应。
记录片中,龙运松的儿子握着文件,一字一字地读给父亲听。被中风病痛折磨的老兵,身子努力前倾,听儿子讲。可当他没有听到一贯关注的报酬时,立即低下头,默不作声。这时,镜头放空。
有志愿者表示,这些老兵很在意为自己“正名”。因此,他们也会纠结于叫“国军抗战老兵”,还是“国民党抗战老兵”。
“他们须要物质救助,更须要精神上的认可。”一名志愿者说,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抖动,“救赎才刚开始”。
86分钟的记录片即将结束,老兵的照片一张张在片中滚动。随后,片尾曲响起。“向前走,别退却撤退,死活已到末了关头。同胞被屠杀,地皮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的歌声在这个新媒体大厅内回荡。
一贯沉默的老兵合着曲子,表情严明,脚上打着拍子,随着唱起来,声音越来越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