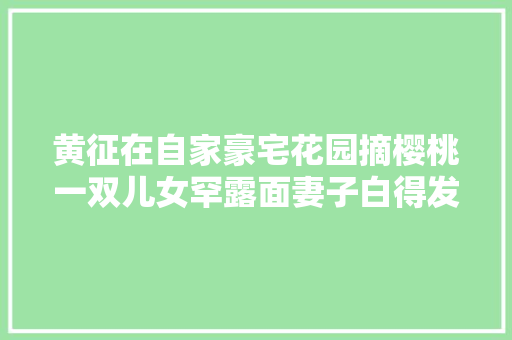我想说的不是这种游戏的跳屋子,是真的从房顶上跳过去的那种跳屋子。
豫北屯子为了晾晒方便,房顶都是平的,而且一家挨着一家,中间只隔着窄仄的一个小胡同。顽皮胆大的孩子们便顺着梯子,爬上屋顶,从这家的屋顶跳到那家屋顶,惊险刺激。我家的屋子和二堂哥家的挨得紧,中间间隔很小,一岔就过去了(岔,辉县方言,迈步之意,我们还有一种游戏叫“岔”大步),这个小妹都能岔过去。后院二堂哥家和大外家,大外家和二大外家的屋子就有点远了,我和红伟、建福、建双几个男孩才能玩,由于这里的“岔”便是跳了。二大娘和六大外家的就更远了,我从来没敢岔过。二姐说,她能“岔”过去,我信。由于二姐是出了名的“假小子”,实在是比小子更小子。我们都叫这种玩法为“跳屋子”。

现在,女儿每周都要做安全教诲作业。依现在的教诲标准,我们当时那种“跳屋子”行为肯定是高危动作,是极不屈安的。但并没有一个人掉下来过。相反,熟能生巧,我们在房顶腾挪跳跃,一个个小朋友像小猴子般,这家跳那家,追逐欢笑,如履平地,步履生风,风风火火,以为好玩极了。
但也并不是没人管教。后院大娘听到房顶“咚咚咚咚”地响,她能根据跑的节奏和轻重判断出都有谁在跳,等我们交往返回地从我家的梯子上房顶,从她家的梯子出溜下去。正玩得兴起时,忽听到炸雷般的喊声在她家院子里传来:
“小保国,快下来!我都瞧见你了,看我不见告你妈!
”她先这样喊。
“红伟,快下来!
我一下子上去剥了你的皮!
”她又这样恫吓。
我们知道这是大娘站在他家院子里喊,赶忙鹜伏在房顶的另一侧,大气也不敢出。我们知道,这样做大娘既看不见,又上不来。她家那梯子是用一个人字形的柳树杈制作的,中间胡乱定了几根木条,中间那根木条被我们踩久了,已经掉了,空间很大,我们爬上爬下都很费劲,她不可能上来。但心里还是很害怕,血管里“登登登登”地血往上涌,我们像是埋伏在战壕里准备冲锋的士兵,在经历敌方的侦查、轰炸!
回到家里,果真:
“野去哪儿了?”母亲严厉地问
我用瓢舀了缸里的水往嘴里灌,不回答。
“野去哪儿了”母亲加重了语气,语速放慢,问第二遍。
我知道问过第三遍后便是笤帚疙瘩奉养了。
“上房了。”我毕恭毕敬,诚笃并怯怯地回答,犹如顽皮的学生在做错事后回答严厉的老师的问话。
母亲瞟了我一眼,停了好一下子,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吧。然后说:“下次从咱家梯子下来,你看大外家的梯子都给你们霍霍成啥了。”
真是这样的。母亲一没打,二没骂,三没说不准这样玩,太危险。要不人们说母亲伟大,如果女儿现在和我小时候那么淘,敢上房顶,我一定是:“劳资蜀道山(老子数到三)…… ”
前天去辉县平岭,女儿让我帮着摘那路边的红梨。我顺着石头墙爬上屋顶,呀!
竟然是和我小时候千篇一律的白石灰做的屋顶,我都四十多年没上过这样的房顶了,我以为瞬间穿越了。我试探着在那满是青苔的屋顶走了两步,怯怯的迈不开脚,我怕屋顶邃古老了溘然塌下来,更怕“岔”不过屋子之间的那道小时候常常跳的小胡同。
不远处便是刘家祖坟,后院大娘已在那里入土为安,我彷佛又听到她在喊:
“小保国,快下来!
”
我赶紧下来了。
今生现代,恐怕没法再玩真的“跳屋子”的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