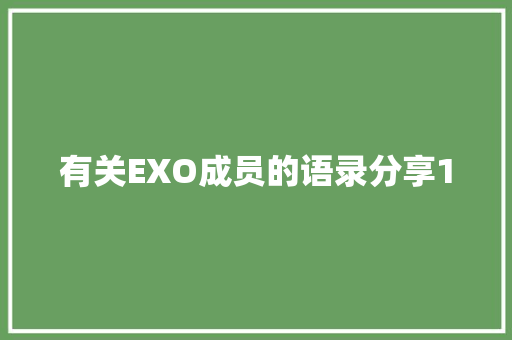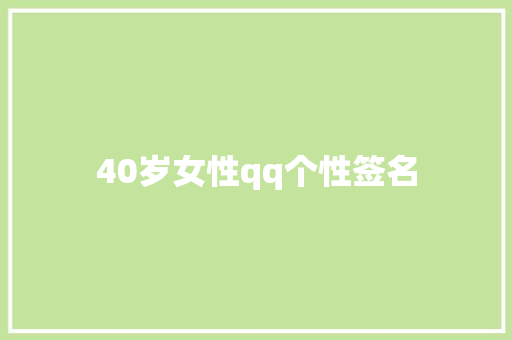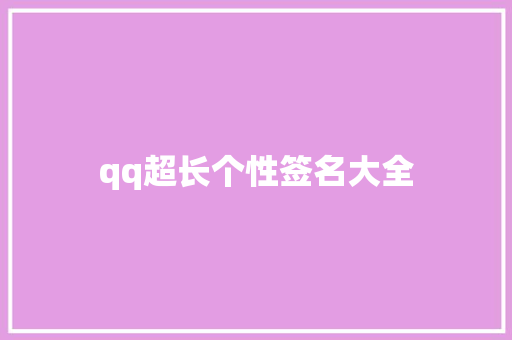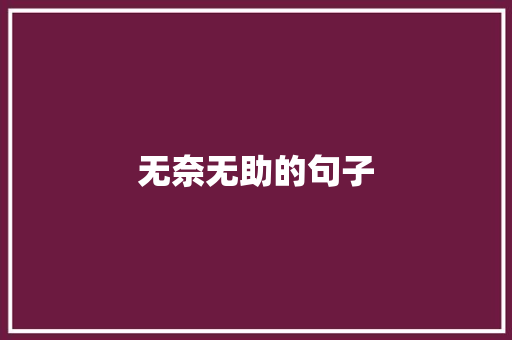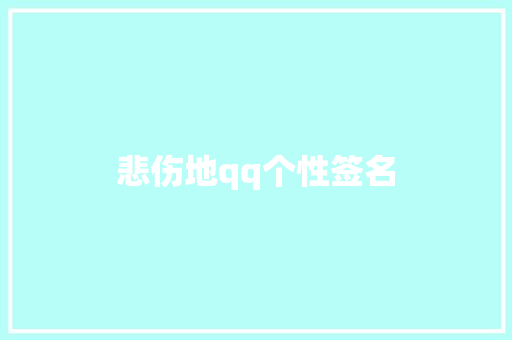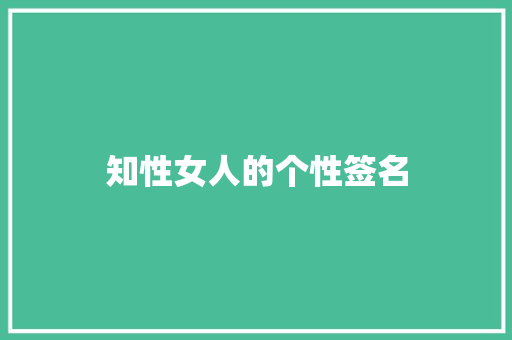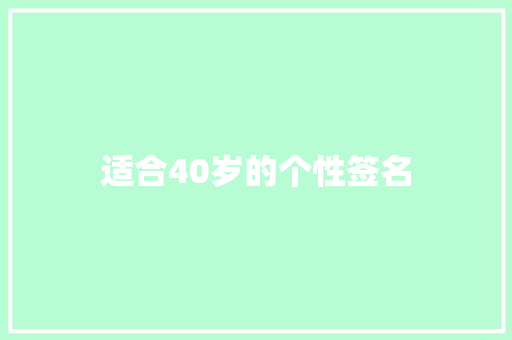大约一个月前,朴树发了新歌,《Baby,Досвидания(达尼亚)》。对无数朴树的歌迷而言,任何一首新歌都是生命中的惊喜。无论自己是否喜好,音符顺着电流跑进耳朵的时候,内心的欢畅让人无处开释。
是的,收到新歌推送的那个午后,温暖的阳光
《Baby,Досвидания(达尼亚)》,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朴树个人风格的歌。如果把它混在十几年前的《生如夏花》和《我去2000年》里,不理解朴树的人,不仔细听,大概无法分辨出来,这是朴树最新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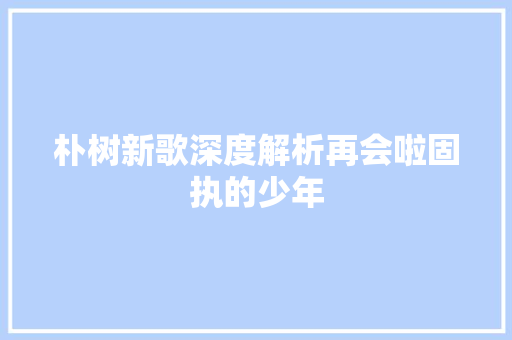
这并不是一种因循守旧,也不是一种后进的审美,这正好便是朴树的魅力。在他的音乐里,在每个音符和词句上,都深深地烙印着只属于朴树的气息。难以言说更难以描述,但静下心来沉浸在音乐中,就像置身辽阔的海洋,每一个细胞都在水流里舒适地呼吸。这种气息,便是那清凉的海水。
这首歌的旋律特殊简朴,编曲并不华美,乃至有些粗糙的觉得,但充满他乡情调。缺少关联和逻辑性的歌词,纯粹意识流的用词,倒是朴树一向的风格。随着歌声哼唱,却猜想之外地上口。从头到尾碎拨一直的吉他,和朴树颓废的歌声相映成趣。
这些元素构建在一起,让听者仿佛正在不雅观赏一部电影,许多一闪而逝的画面涌如今面前,缭乱的蒙太奇再把这些画面串在一起。
后来看了MV,非常惊异自己的遐想居然得到了具象化。这首歌在蛮横地昭告天下,自己诱人的神秘,又在暴露与掩蔽之间,流露了无限风情。
感慨之余,我也在思虑,朴树到底在试图表达什么?
思前想后,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彷佛是被一向的教诲模式给洗脑了,我们总试图探求一种所谓的“意义”。
为什么一首歌的歌词一定要顺理成章,一定要表达某种中央思想?
为什么音乐人的作品,不可以通过音符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思考?
为什么我们可以欣赏没有措辞的画作,存心灵去触摸和感想熏染那些剧烈的色彩,却不能静下心来,只是大略地听听歌?
在这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时期里,我们变得繁芜,我们失落去了走在路上溘然心血来潮,停下来在路边看风景的闲适。我并不是在鞭笞当下的精神贫瘠,抑或嘲讽物欲横流的野蛮,只是有些可惜,我们失落去的,实在不止是闲适淡雅的心境。
14年的时候,《平凡之路》横空出世,朴师傅曾说,音乐是无与伦比的乐趣。15年的时候,随着新歌《好好地》的发布,师傅又写了一篇随笔《与屎共舞》。他说,他创造这个国家的音乐在倒退,太多人拘泥于过去的审美和意见意义中,无法自拔却安之若素。而他自己也是,被自我的拘泥束缚,感想熏染抵牾的痛楚。
而今年,新歌发布后,师傅的妻子吴晓敏在微博上说,“朴树做一首歌,能搭半条命。”为了新歌,朴师傅从英国到内地,不断探求得当的制作伙伴,却一贯未能如愿。末了,还是找来了老朋友张亚东。前后奔波,少说也有一年多吧。
他一贯这样,特殊认去世理,固执地坚持自我拷问,像个仍旧处在青春期里的倔强少年,纵然嘴角流血,也不愿意低头。
但大概也只有这样固执的少年,才能在当下这个快速而轻浅的时期里,把对音乐的坚持视作乐趣,内化整天然而然的生活。
几个月前,朴树曾经参加一档音乐节目,他在舞台上坦诚地见告不雅观众,自己参加节目的缘故原由是“这一段韶光真的须要钱。”那时候很多人以为惊异、不解。错愕之余,还有些“偶像崩塌”的心痛感。
可让我们静下来仔细想想,这统统却又通情达理。
彷佛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朴树便是那个《生如夏花》专辑封面的长发青年,弹着吉他,眼神忧郁地唱着只有他自己懂的歌。他们说,朴树是孤独的,是感性的,也是自由的。他们把朴树包装成一个符号,一个迢遥的光源。他们在仰望朴树的同时,在追忆青春的幌子下聆听音乐的罅隙里,不断地被虚幻的光芒自我冲动,在过度解读的浪潮后精神狂欢。
可是朴树真的是这样的吗?他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妥协。他为了坚持,乐意妥协,乐意离群索居,乐意过的平面而软弱,但他很清楚,自己是为了什么。由于他的复苏,抵牾的对立得到了统一。
朴树说,“跟行业保持间隔的这些年,我的头脑更清楚了,也知道了我要什么,要做什么样的人。到底还要不要做音乐,我以为我想清楚了,可以再回来。”
他还说,“但我一贯在提醒自己,去理解和感想熏染那些我所不理解的。我不要勾留在一个让自己感到安全的地方。我不要作一个狭隘的人。”
他抽着中南海,用老掉牙的诺基亚手机,一日三餐,闲步遛狗,过着老年人的生活。他为了独立音乐的追求,从中国跑到英国,又回到内地,辗转四方。他在自我否定和自我解构中,苦苦寻求沉着和知足。他说,做音乐这件事,让他感到痛楚,也让他快乐。
朴树一贯是个特殊坦诚的人,对生活如此,对音乐更是如此。
他以为自己没有做音乐的状态,那就安歇,直到状态来临。
他以为这个环境很混沌,统统令他作呕,仿佛与屎共舞,那就离开,直到自己可以接管。
他说我现在没有钱,音乐难以为继,那就去参加电视节目,坦然地拿着过去自己看不起的钱,然后用耕耘音乐的热爱,忘怀这些骚动。
我记得朴树每次在演唱会上,唱那首《别,千万别》的时候,都会说这样一段话,“如果全天下都丧心病狂,如果所有人都去抢银行。如果成功便是高高在上,把别人践踏,打去世我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像是在例行公事,又像在得到自我认同。
朴树从未渴望成为某个光辉的文化符号,他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在做自己认可的事。只是像他这样,虔诚地,犹如苦行僧一样平常地,把一件事坚持到堪比修行的程度的人,太少了。我们被这个时期同质化,我们逐渐失落去了耐心和羞辱,也失落去了天真的固执。
请体谅我的妄加预测,《Baby,Досвидания(达尼亚)》,其实在表达一种对自我的作别。
我们带着某种稚嫩的憧憬,走进生活。年纪渐长,我们在希望和奢华中走马不雅观花,在混乱与放肆中迷失落自我。后来有些人逐渐忘怀了那份憧憬,一个不慎,摔进了五颜六色的尘世里。从此喜笑颜开,如鱼得水,就像在污浊中重生了一个自己,彻底判若两人。
但还有些人,咬着牙忍受着迷茫,孤独,怠倦,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他们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冰冷的夜里以梦取暖和。乍眼望去,他们彷佛失落去了自我,和大街上的每个人一样,游走在高楼大厦间,乞求着生活的权利。可是他们自己知道,苟且的噜苏里还存在某种值得坚持的意义。
朴树这首歌,实在便是在描述这些人。他们和过去固执的自己作别,在外界与自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游走在痛楚与欢愉的边缘。
如果固执的少年永久不低头,那他大概不是在坚持自我,他要么迂腐又屈曲,要么便是在别有用心地作秀了。以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心里那个固执的少年离开了,这并不一定是终年夜成人必经的溃烂,很有可能,是终于明白生命追求之后,乐意用妥协交流坚持的成熟。
再见啦,固执的少年,我要到生活里去了。我们的坚持,我一贯都没忘。
——本文为果酱音乐(www.jammyfm.com)三方作者稿件,未经许可,回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