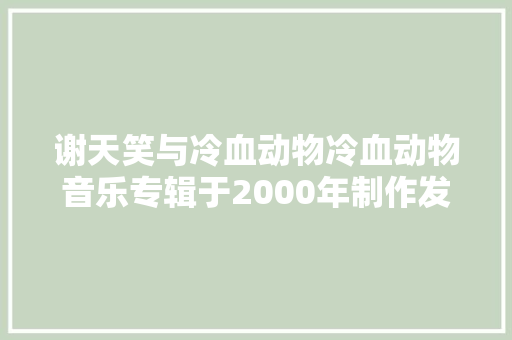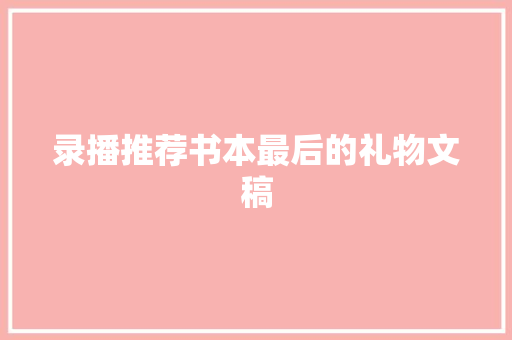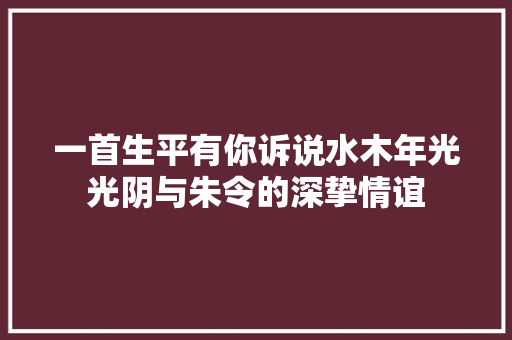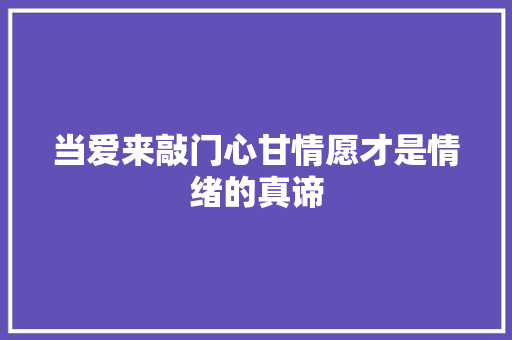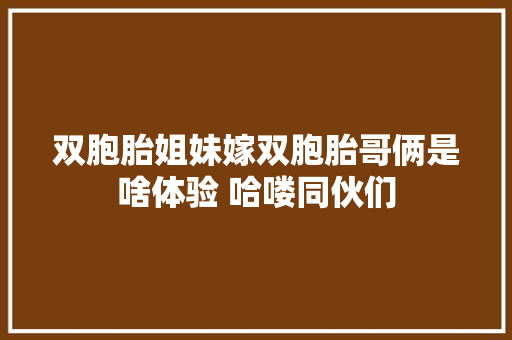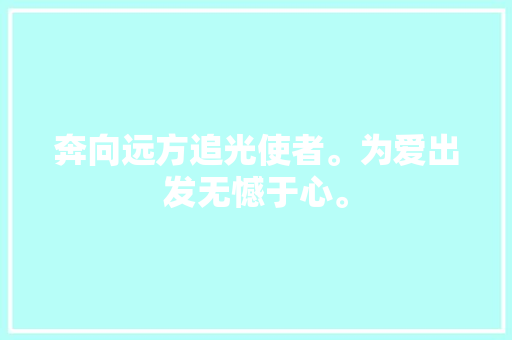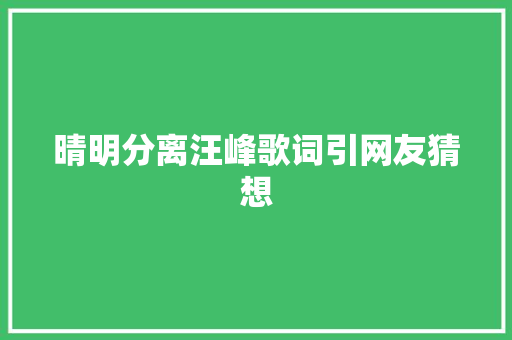圣历二年正月(即698年12月),武则天为张易之置控鹤监,以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薛稷等为控鹤监内供奉。同时,武则天又命张昌宗和李峤为修书使,召张说、徐坚、阎朝隐、沈佺期、刘知幾等二十六人在内殿修《三教珠英》。控鹤监在久视元年(700)改名奉宸府,张易之依前为奉宸令。设置这个机构是为安置幸臣,召修《三教珠英》则有掩饰笼罩荒淫生活的目的。但是,控鹤监“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修书又“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可知武则天采纳这两项方法另有用意。
武则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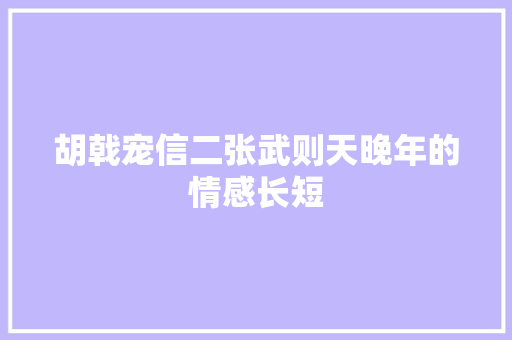
三十年前,她就曾以修撰为名,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一批文学之士召入禁中,让他们参决政事,“以分宰相之权”。现在的做法和过去类似,是想以二张为核心再调集起一批文士,形成一个新的亲信的政治力量。在控鹤监供奉和修《三教珠英》的人当中,确实也有一些,如吉顼、李迥秀、李峤、阎朝隐、沈侄期、宋之问等,成为张易之、张昌宗党人。
这批人之外,还有不少人为政治投契而先后寄托二张,他们是“以文才降节事之”的崔融、苏味道、王绍宗,“前托俊臣、后附张易”的郑愔,“专以谀媚取容”的杨再思,为张昌宗脱罪的韦承庆、崔神庆。武则天末年用的另一宰相房融也是二张一党。这都是些趋炎附势的人,想依赖这两个“贵宠逾分”的权臣,钻营自己的政治地位。
有了同党,二张的势力便膨胀起来。他们“势倾朝野”,“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当时“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人们“窃言二张专政”。显然,这时的二张集团和过去的薛怀义、沈南璆不同,他们不是一两个“嬖宠之人”,而是一股政治势力。像武则天复立庐陵王为太子这样的大事,也是经二张及其党人吉顼策划说项办成的。由此可见他们干预政事之深,绝非等闲之辈。
二张得势,引起与朝臣争权的抵牾。他俩常常打击不屈服自己的大臣乃至王公贵戚,弄得关系十分紧张。久视元年(700)闰七月杨元禧兄弟三人被贬,便是由于“尝忤张易之”;长安元年(701)玄月邵王李重润等三人被杀,也是由于“窃议”张易之兄弟;特殊是长安三年(703)玄月的魏元忠案,更是闹得“长安城内,街谈巷议……民气不安”。事情的起因是魏元忠屡挫张氏兄弟,斥之为“小人得在君侧”,使武则天不悦,被二张衔恨诬告有反言。这场官司震撼朝廷,从宰相朱敬则到宋璟、张说、张廷珪、刘知幾和武邑人苏安恒都奋起为魏元忠辩解,可武则天还是“以昌宗之故”,将魏元忠贬为高要尉,张说等人也受牵连流岭表。
官员们愤愤不平,“抚髀于私室而闭口于公朝”。二张不仅夺走了许多权力,还使人感到当年滥刑下的恶运彷佛又临头了,攸关身家性命的短长迫使一批朝臣起往返击二张。
除了王及善、韦安石等个人的行动外,在五王政变前的半年内,反二张派的朝臣们曾两次群起而攻之。
第一次是张氏兄弟的贪赃案。张易之兄弟五人,生活腐败,处事霸道,个个是贪污好手。长安四年(704)七月,他们贪赃不法的事败露,兄弟五人一齐下狱。御史大夫李承嘉和中丞桓彦范奏张昌宗应免官,武则天却用杨再思说,借口张昌宗合药有功,将他赦免,并令复职。宰相韦安石又举奏张易之等罪,武则天只好敕付韦安石、唐休璟再行鞫问。可是她立时又变了卦,在八月里把韦、唐二相放为外官,草草了却这桩公案。
第二次是当年十仲春张昌宗引术士占相被告发的案件。张昌宗下狱后,御史中丞宋璟和封全祯、李邕、桓彦范、崔玄暐、崔昪等以张昌宗“图天分,是为逆臣”,坚持问罪。特殊是宋璟几次再三执言“法当处斩破家”,“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武则天还想利用对付韦安石、唐休璟的办法,三次下敕要宋璟赴外差,宋璟以“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为情由不走。武则天不得已,只好责令对昌宗审讯议罪,但末了还是“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宋璟怒气冲天,说:“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
可是武则天在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掩护二张,为他们杀孙子(太子的宗子)、孙女、孙半子,贬走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多年重用的大臣,将部分政务交给这两个秽声载道的家伙,四次命令审鞫二张之后又四次下敕赦免,在二张几次再三被人告为谋反,乃至像苏安恒警告的那样,不除二张将“逐鹿之党叩关而至,乱阶之徒从中相应,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结怨,不怕引火烧身,去世去世掩护二张。显然,仅以二张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的男宠是阐明不清的。答案只能从政治方面去找,武则天须要一支亲信可靠的力量作为坚持自己统治的工具。
最初在废王立武之争期间,武则天靠的是许敬宗、李义府一伙,可是他们在7世纪70年代就或去世或杀,被淘汰了。
往后,武则天依赖过北门学士和废中宗时用的裴炎那批人。可是他们有的老去世了,别的险些都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胆怯政治中被武则天消灭了。
文明往后酷吏们在政治斗争中起了不小浸染,但他们的活动只局限于节制法律机器一个方面,而且在90年代中便已大多被杀了。
佛道二教的僧侣和在京城的数目可不雅观的少数民族大小首领,在武则天称帝时也起过突出的支持浸染,但究竟是不能靠他们实现政治统治的。
武则天临朝称制往后,宰相大臣们或因专权用事,或因被罗织,有的被杀,有的被贬,变迁频仍,武则天部下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核心。自己同族诸武,本来是可以相信的,但武承嗣等大闹争当太子的事非常不得民气。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在继续人问题上于母子姑侄之间做了末了决议,用“为誓文,告天地”和联姻之类办法调节李武两姓的抵牾,诸武的权势和气焰被适当地压抑了,也便是说,她对武氏诸王确实“非所属意”,不再把大权交给同族,不能以诸武为自己核心的政治力量了。
武则天找来找去,找到二张头上。二张是可靠的,他们出身平平,除了有一个在永徽初年做过宰相的族祖张行成,再没有可以挂齿的政治背景。他们因此幸臣身份进用的,张昌宗说的是诚笃话,武则天在,他们是“千人推我不能倒”,离开了武则天,就变成“万人擎我不能起”了。这也是武则天用他们为亲信的主要缘故原由。
为什么武则天不能再从朝臣中选拔一批人,像过去提拔许敬宗、李义府及北门学士时那样做呢?武则天的统治代表着全体地主阶级的利益,特殊有利于新兴普通地主的发展,是有相称的阶级根本的,但为什么这时她不能从普通地主及在政治上转向推戴武则天的出身于旧门阀的官僚中组织起一个新的权力中央呢?这是武则天过去十几年中实施了滥刑的缘故。
一方面,武则天不信赖他们,“疑天下人多图己”和“乱臣贼子,日犯天诛”引起的八面受敌的忧虑,不可能肃清干净。特殊是刘祎之和李昭德二人,曾是她“甚见亲委”的大臣,可后来他们竟“专权赌气”,公然顶撞自己。武则天得了这些教训,不能不疏远一样平常文武大臣。
另一方面,文武大臣们对武则天也存有戒心,当年的酷吏和诏狱,他们一定是影象犹新的。当时人无固志,认为武则天同他们“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过去利用滥刑使武则天失落掉了臣僚们对自己的信赖,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成为武则天太亲信的人,反倒有不少人越来越对唐室怀旧,即所谓“唐之名臣,难忘复兴之计”。
当年的武则天起来反对现在的武则天了。她究竟自食其果。那把曾经得心应手的刑刀在武则天的君臣关系中刻下一道深深的缝隙,表面上融洽的君臣关系下面埋伏着危急,武则天晚年实际上是非常伶仃的。内心的空虚寂寞使她不得不在政治上乞助于二张,而这样做又使她更加伶仃,末了二张为她招来了政变。
(本文摘自胡戟著《女主临朝:武则天的权力之路》,岳麓书社,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