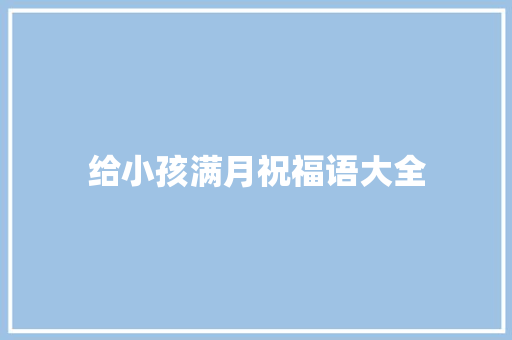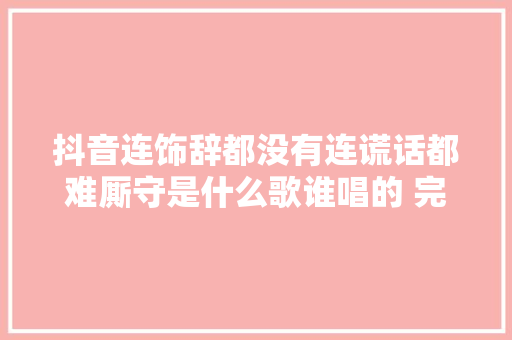人们常这么说:去,上北大街,把东北角那边,找有个大钥匙幌的那个棚子,让锁师傅来,把咱这锁打开。
白老太太今儿可是碰了钉子,嘴皮子磨破,那孩子捧着小人书,装傻充愣便是不动窝。还贫嘴嘟嘟囔囔地说:“哪个索师傅?他是姓索呀,还是你们叫白了,说人家是锁师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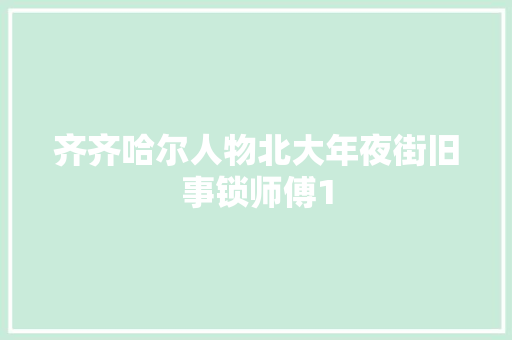
老太太一听就冒了火,再看着宝贝孙子盘腿,大模大样地在热炕上看闲书,一股邪魔气,立马钻进脑壳。刚想张口开骂,竟又换成了笑脸,骗腿挨在大孙子身边说:孙子,你这书是谁给你租借的?
“那我也不去。”这孩子心里惦记着《渔岛怒潮》的何占鳌,到底被谁捉住的。哪有心思管老太太的闲事。
老太太可就上了火,一拧身从炕边出溜到地上,撩围裙擦手,再顺手今后腰上摸围裙带儿,瘪着嘴就骂:“小王八羔子,我给你钱租书,我是犯贱。你这啥也不帮我,去北大街一趟,找个人都弗成啊?我这还给你做饭?屁。得了,饭你也甭吃,我可不求你,我自己个儿去。哼,等你爹家来的,我不见告他扒你的皮,我算是白说!
”
老太太气的一门劲儿叨咕,越焦急还越摸不到围裙带儿的活绳,把个带儿楞弄成了去世结。她气的直抖动,不得不把围裙的后面转到前边,好眼见着这结的活绳,把扣解开。嘴上还是在骂:“我房梁吊颈着的筐里,槽子糕本来是5块,咋就没一个?这我都没稀得跟你算账,你可倒好,不识好歹,指使你跑个腿儿的小事,不动力气的活儿也不干。哼,下回你二大爷来,拿来啥东西我都力可量地吃利索,我撑去世都不让你,我让你白看着、干瞪眼儿。”
“老太太!
这自己个气囔囔地叨咕啥呢?”索师傅或是锁师傅来了。
“呀,老锁呀,你咋来了呢?我正吆喝这孙子去找你来,他看小人书不动弹,我这个气呀。”老白太太边说边从锅台边站起身,转头让师傅里边坐。还问呢:“那你咋来的呢?在北大街都听到我这儿骂人了?”
“你可说的呢,你家孩子找我去啦呗!
”锁师傅边说便把他的干活家什放地上。搓着大手拿眼神问老太太,坏锁在哪?想修个啥东西。
这时候,老太太才回过神,往炕上撒眸。嘿,那盘腿大坐看书的孙子,不知道啥时候跑了。心想起刚才的事,自己是对着空屋子骂了半天儿,心里也乐了。忙呼唤锁师傅道:“忙啥,我先给你倒水去,活儿不急,不整也没啥事,我是做饭的功夫想起来的,有个旧箱子,锁钥匙没了,我拽了几下那锁,还挺紧,端起小箱子晃晃,里面花楞花楞地还有东西。”
老太太还在往下讲故事。锁师傅笑着说:“快拿来,我看看吧”
“不急,哎,俺家孩子找你没跟回来?”老太太放下箱子不说,她想起孙子来了。
锁师傅只好捧着水碗,接她的话茬。“你家孩子丢不了,在我那儿,又看上小人书了。”
“啊,他那书不是在炕上么,哪儿又新租书了?没给他钱哪!
”老太太急速明明白白的了,眼神中透着抓个蟊贼似的愤怒。“这孩子,这可弗成,我得找他去,哪儿来的钱?这怎么行?!
”老太太边说边怒气冲天地往外走。
锁师傅忙笑着拦着说:“你这老太太,糊涂了。我能看着他干坏事不管哪。那书是我给他租的。我看他满脸不高兴,噘着嘴嘀嘀咕咕地说看书呢,让你给指使着心里不高兴,就给他又租一本《刘胡兰》。让他给我看摊子,边看书。”
听到这儿,老太太乐了,瘪的腮帮子呼哒呼哒地动。心扑噔一下子撂到了底儿,拉着锁师傅道:“有姆那孙子给你看摊子,那就更不急了。你说这几天哈,我……”
咋地?竟瞎写。你看看哪有骂自己大孙子的?好吃好喝地哄着,还不足呢,哪能骂?
闹归齐是由于这个,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北大街往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年孩子多,甭说当奶奶的骂孩子,便是打孩子那有什么不可。甭说打自己家孩子,便是别人家的孩子,也照打不误。不让打?你试试?惯孩子的名声可不好听,顶风能臭到解放门还往前,兴许就到了小黄楼,再拐弯没准可以臭到黄沙滩。不怕?你可别吹,整不好你家二哥哥的喜事、浓眉大眼三姐的婚事,有可能就吹了。那年头,骑自行车上班,路上也没有手机啥的,也没有啥苦处老愁眉不展的。老长的路都是自行车驮着,王姨和李婶儿,叽叽嘎嘎地便是唠嗑。说道你家像老母鸡似的惯孩子,谁家好小子、俊丫头的非钻你家被窝。黄,就在一句话,乃至一个感叹词上。当问到:老钱家那户人家怎么样?被问的人,只要一打喯,说话间卡壳了那么一下,问话的就明白了。这户人家不咋地,不然,磕巴啥?人家不好意思说呗!
(预知后事如何,请关注公众号,看下期)
文章来源于卜奎艺站 ,作者孙鹏
齐齐哈尔市新闻传媒中央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