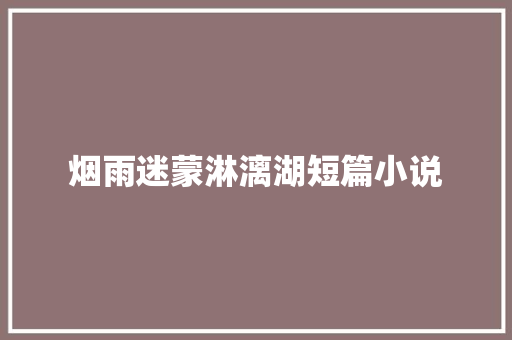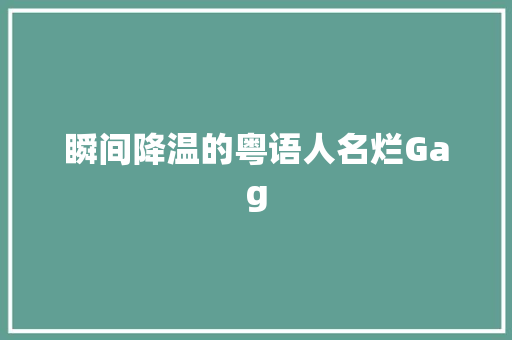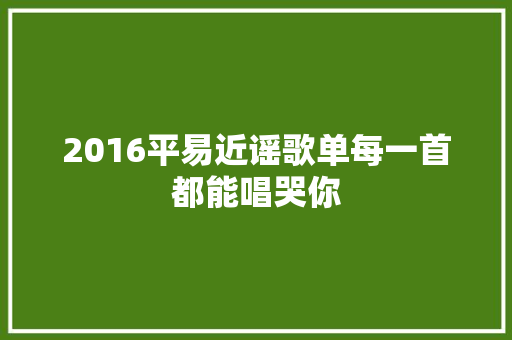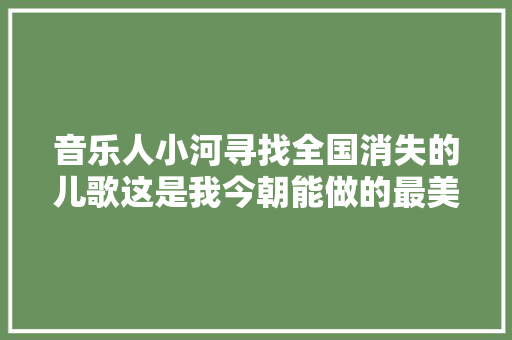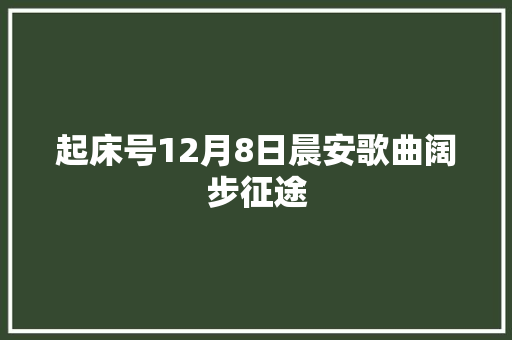“问问那个白人,要不要我召唤这条河。”
这是达邦狄王妃的原话。我不敢翻译给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上尉。他正忙着号令林波波河河滩上泡在水里的部下,不会听这么奇怪的问话。我们坐的船在沙滩上搁浅,几个小时以来葡萄牙士兵都在试图脱困。个中最大胆的几个在舷侧推船,险些没进水中。那场景极为罕见:白人在烈日下筋疲力尽,而黑人坐在宜人的凉荫里察看犹豫。莫西尼奥命士兵返回甲板:那片水域有鳄鱼栖居。

莫西尼奥所不安的并非耽搁。我们从奇玛卡泽出发后一起疾行,未曾勾留。他担心的是附近丛林里潜伏的危险,里面不见活物,却传来声响,还有黑影鬼鬼祟祟地移动。大概立时会有一场伏击,补救他船上的俘虏。
达邦狄王妃便是个中一名俘虏。对付这场耽搁,她比上尉还要紧张。她溘然举起双臂,让所有人安静。一阵战栗席卷全体船员:一群像是从地里长出来似的男女老少在岸边现身。莫西尼奥命令士兵武装戒备。一阵冷寂袭来,河流也沉默了。
“我能去召唤河水吗?”达邦狄王妃又问。然后她问我:“你有没有见告那白人,我懂河流的措辞?”
只要她一句话,林波波河就会像温驯的小狗,到她掌中讨饭。莫西尼奥咬牙低吼:“叫这女人闭嘴!
”场合排场一触即发。达邦狄王妃忽然跳下船,走向岸边一直涌出的沉默人群。
所有目光都聚拢在王妃身上,看她穿过沉着的河水。达邦狄的双脚既没碰到水面,也不打仗地皮。实际上她并非在行走,她在演绎一支舞蹈。臀部的摇摆令踝上的铜环叮当作响。
到了岸边,王妃和向她围拥而来的人群热烈交谈起来。我们什么也听不见,只知道她一贯指着我们。溘然,那群人发了狂地冲向船边。葡萄牙人吓住了,还在把枪往肩上扛。但已经来不及了。几百个男男女女已超越河滩冲上来,用肩膀、腿、胳膊撞上船体。船身剧烈晃动,船员大喊大叫,马也胡踢乱蹬。
船很快重新浮起。确认了双方和蔼、用意同等,黑人与白人都欢呼起来。人们帮达邦狄回到甲板上。王妃气喘吁吁,但十分愉悦。我问她为什么要帮助囚禁她的人。
“有人在这一程的终点等我。”她说。
两天前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沙伊米特,莫西尼奥上尉抓了恩昆昆哈内国王,把他绑到了奇玛卡泽码头。与被囚的国王一道的还有他选来做伴的七位王妃。那次挑选是他末了一次行使王权。随行的还有我,伊玛尼·恩桑贝,葡萄牙人选来的译员。末了,在奇玛卡泽,姆弗莫人首领恩瓦马蒂比亚内·齐沙沙也加入了俘虏之列。与这位乱党同行的是他的三个妻子。
从沙伊米特到奇玛卡泽,同样的惊奇几次再三涌现:加扎王国的子民不可置信地看着国王恩昆昆哈内含泪被拖曳前行。葡萄牙士兵人数之寡,令围不雅观奇特游行的人群更加不解。
葡萄牙人展示的不但是个被擒的国王。在那儿光着脚游街,被征服、遭羞辱的,是全体非洲。葡萄牙须要那场展出,挫伤非洲人中兴叛乱的勇气。但他们更需震慑那些争相瓜分非洲的欧洲国家。
莫西尼奥上尉骄傲地看向路边聚拢的人群,有些入迷。人群一如既往地爆发出欢庆的呼喊。
“拜耶特!
”他们齐声高呼。
上尉让我翻译人们喊的话。我低声见告他,他们在为他这个白人上尉叫好。他得意地笑了。他们赞颂他时的激情亲切,莫西尼奥说,连他最忠实的同胞都比不上。他未曾想到,像对待解放者一样为他欢呼的非洲人比葡萄牙人还多。他骄傲地向我承认了这点。他还说:
“黑人在这儿为我塑像,说不定会比我的同胞在里斯本还快。”
再次动身后,达邦狄王妃就一贯在我身边。去奇玛卡泽的路上,是她为我洗去了被士兵砍去脑袋的鹭的血。“你有身了,”她为我洗濯时说,“不能再让任何血碰到你了。”
此时,王妃凝望天空,从云上看出乱势。她晃晃我的胳膊,提醒我一场风暴正在逼近。我们一起去找船长,一位穿浅蓝色制服的军官,叫阿尔瓦罗·苏亚雷斯·德·安德烈亚。那高大魁梧的男人盯着我,目光意味不明。他是个航海家,却有着海上罹难者般的目光。
但我们没能与船长说上话,由于恩昆昆哈内之子戈迪多走过来,命令王妃回到国王身边属于她的地方。达邦狄假作未闻。戈迪多更强硬地坚持道:
“回你丈夫身边去,王妃!
”
“王妃?”达邦狄回嘴,“我用婆婆的锅做饭,算什么王妃?”她的手指示在戈迪多的胸膛上:“别再这么叫我了。我是个寡妇。那才是我。”
戈迪多王子回到俘虏中,不知道怎么阐明此行无功而返。
“你怎么了?”我问达邦狄,“为什么违反恩科西?”
“我不是王妃。我是个尼雅穆索罗,听亡者说话,与河流交谈。” 船减速了。我们即将抵达兰格内哨所,林波波河入海前的末了一个葡萄牙军事据点。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向等在岸边的梢公存问。等船靠了岸,我就向莫西尼奥转达了达邦狄的担忧:一场狂风雨从林波波河河口生出。不是天上形成的那种风,我阐明道。是一场人为招致的风暴。
“上帝啊,这群人愚蠢到家了。”那军官如此点评,以手扶额,“黑人中女人比男人还差劲。”
他不知道这话对我有多搪突。我表达自若的葡萄牙语,让莫西尼奥不再看到我的种族。我保持沉默,闭口不说那侮辱我的人的措辞。
我们终于在兰格内哨所上岸。航行将短暂中止,装载武器和伤员。非洲俘虏被带到一处凉荫。他们分到几块饼干和一杯葡萄酒,待在那里,精疲力竭。达邦狄又离开人群,坐到我阁下。她在杯底留了些酒,倒了几滴在滚烫的沙地上,平息天下出身以来的逝者的干渴。
“知道我怎么学会与河流交谈的吗?”她问。
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她说。在她当选为国王的妻子之前。那时,她每天早上都会不雅观察一只蜘蛛在她家院子里的一个洞穴进进出出。蜘蛛把腿上的露水运到地底,像高下颠倒的矿工一样平常事情:取自天上,堆在地下。那劳作持续了良久,洞穴深处乃至逐渐形成宽阔的地下湖。
王妃想在这湿润的矿上助蜘蛛一臂之力。一个没有露水的清晨,她取了杯水倒进洞口。但蜘蛛谢绝了她的美意,笑道:“我做的这些并非劳作,只是交谈。”还说:“我明白你有多痛楚,只有极致的孤独才能让人把稳到我这样眇小的生物。”为表感激,蜘蛛教会了她水的措辞。
“现在我与河流交谈,无论大河还是小溪,”达邦狄末了说,“我会用只有我知道的名字称呼每条河流。”
我们被穆扎木西打断,她是此行最年长的女眷。她绝不客气地捉住达邦狄的手腕,拽着她回到俘虏中间。然后,她年夜声宣告恩昆昆哈内要我觐见。我急速前去。
在国王面前,我遵照规矩跪下击掌。国王要知道我和达邦狄说的话。我没来得及回答。“我听不见。”国王说。我提高音量。他摇头:问题不在于我的声音。他听不见,是由于我穿了鞋。“你的鞋说话太吵,”恩昆昆哈内说,“从现在起,你只能光着脚靠近我。”
我本该知道:国王踩过的地面变得神圣不容陵犯。我的鞋触犯了这则崇高的规约。众王妃听了他的话,放声大笑。她们的笑声令我的鞋不复存在。
不合不止在我们非洲人之间涌现。那群葡萄牙军官没有一天不在相互责怪。所有人,无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都找我抱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信赖我。我不但是翻译,还是桥梁。大概我是达邦狄家院子里的蜘蛛,用腿上运载的语词,织成联结不同种族的网。
闲步时,莫西尼奥已会熟稔地与我搭讪。此时,他坐在我身旁,一动不动,目光少焉不离阿尔瓦罗·安德烈亚。
“那家伙怨恨我,”莫西尼奥断言,“我可以见告你,没有哪个黑人像他那么不尊重我。”
上尉把帽子放在膝盖上的动作很慢,表明他打算聊谈天。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他开口,“你也知道我们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翻译只会是一部分明面上的事情。”
他停了一下子,摸摸胡子。“加扎王朝统治得太久了,”他说。“知道为什么吗?”他问。他兀自答道:“这个贡古尼亚内知道我们的统统,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那群缚动手坐在一边的黑人,不仅仅是俘虏。莫西尼奥这样说。他们是宝贵秘密的主人,而我将把那些秘密交给葡萄牙军队。这是我涌如今那段旅途中的真正目的。我小心地清清嗓子:
“我明白,上尉。”
莫西尼奥卷了根烟,没点火,叼在嘴上。我侧目看他。他是个好看的男人,难怪比安卡为他爱慕。
“那么,您许可的话,”我小声要求,“我就回我的族人那边了……”
“我希望,”莫西尼奥说,“你留在白人这边。他们之中寓居着最大的背叛。”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