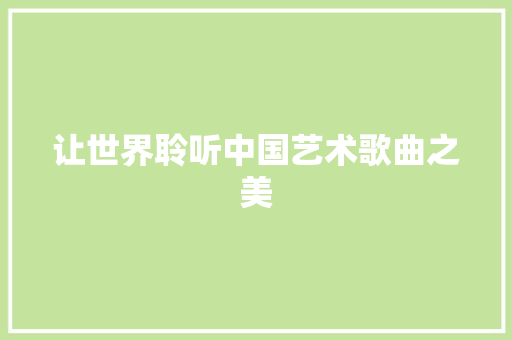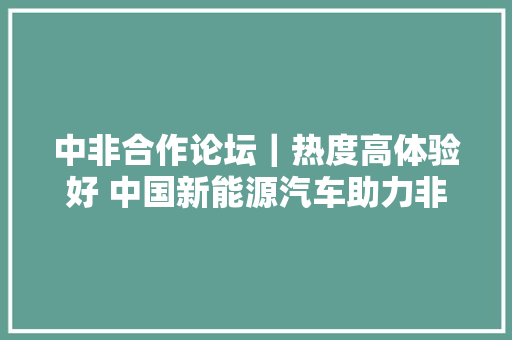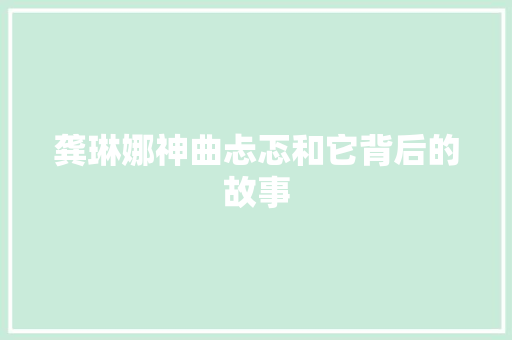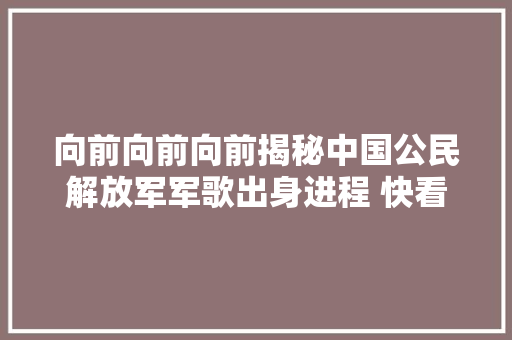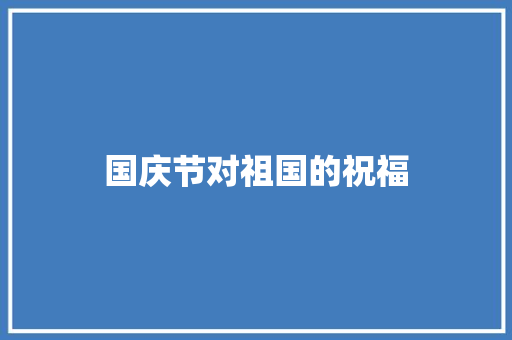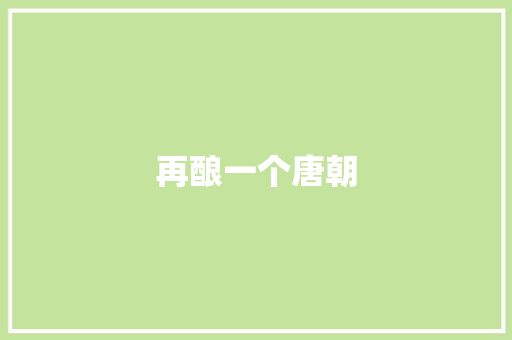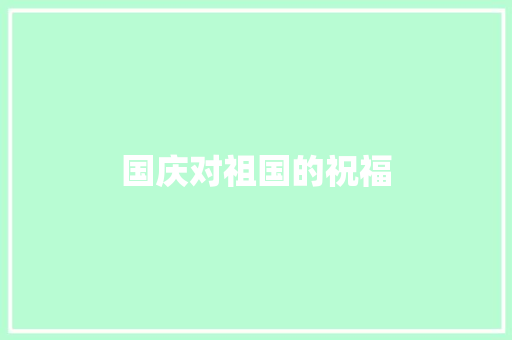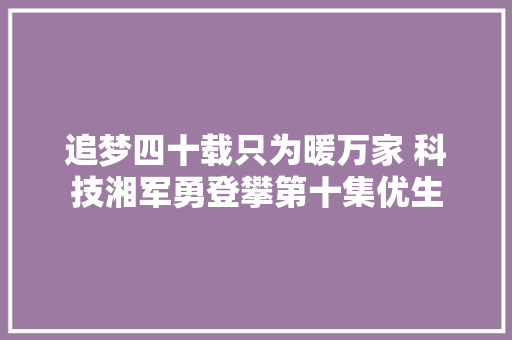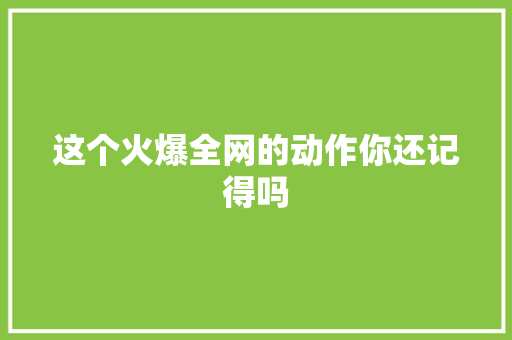1920年,一首《大江东去》开启了中国艺术歌曲100年的进程。 作为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诗词结合的产物,中国艺术歌曲是让天下理解汉语之美的一扇窗。 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多年来一贯在演唱并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在接管专访时,他讲述了心中那份“艺术歌曲情结”的来由。 用一首小诗,唱一个故事 2008年11月,廖昌永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在有名歌剧选段之外,他演唱了中国歌曲《望乡词》:“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想起不久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泪水不知不觉浸润了眼眶。 准确地说,《望乡词》是一首中国艺术歌曲。它的歌词源自于右任的诗,当代作曲家陆在易用西方作曲技法为之谱曲。 “艺术歌曲”一词是上世纪20年代由萧友梅从德语直译而来。如果说,西方的艺术歌曲是优雅的代名词,那中国艺术歌曲便是中国诗词与西方当代作曲技法的结合。它用一首首小诗,唱出一个个内涵深刻的故事,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 1920年,一位名为廖尚果的赴德留学生用西方作曲技法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成了一首歌,取名为《大江东去》。这首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其思想内涵、音乐意境与声乐技巧,纵然以本日的标准来看,依然十分精彩。 1929年,改名为青主的廖尚果选用宋代文学家李之仪的词写下了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隽永的歌词与欧洲的复调音乐领悟在一起,传达出一种朴实、炽烈的情绪。 自《大江东去》之后,萧友梅、赵元任、黄自、刘雪庵、陈田鹤等一批作曲家纷纭将古典诗词名作谱成艺术歌曲。比如黄自的《花非花》《卜算子》《南乡子》《点绛唇》,刘雪庵的《枫桥夜泊》《春夜洛城闻笛》,陈田鹤的《江城子》《采桑曲》《春归何处》等。 除了古典诗词外,许多由新诗谱成的艺术歌曲也十分动听,比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玫瑰三愿》《思乡》《春思曲》、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刘雪庵的《长城谣》、冼星海的《老马》《断章》等。 到了当代,赵季平、陆在易等作曲家创作了《关雎》《我爱这地皮》等不少精良的艺术歌曲。 期待下一个百年 与有着悠久历史的西方艺术歌曲比较,中国艺术歌曲是年轻而小众的。只管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但始终缺少成系统、有规模的梳理、研究与传播。 十多年前,廖昌永就提出了创立一个中国艺术歌曲研究事情室的想法。在上海音乐学院,他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这些年来,热衷于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与传播的他录制过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精选专辑《海恋》《教我如何不想他》,也举办过《春思曲》《我爱这地皮》等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 在做这一系列音乐会的时候,他越来越感想熏染到中国艺术歌曲在不同历史期间的风格不尽相同,值得深入探究。2016年,廖昌永担当了中国艺术歌曲研究中央卖力人,梳理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的发展脉络并挖掘了如谭小麟等非常精良却不被大众所理解的艺术家。 今年,在中国艺术歌曲出身百年之际,上海音乐学院又将与德国著名的大熊出版社互助出版《中国艺术歌曲16首》,并组织专家编撰《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大系》《中外艺术歌曲大辞典》《中国艺术歌曲百年曲谱》。今年下半年,还将举办中外艺术歌曲国际论坛、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等。 “对艺术歌曲的挖掘、整理、出版以及推广,是为了让我们与国际同行能够平等地对话,让天下理解中国一代代音乐人在这100年中对天下音乐所作的贡献。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够促进中国艺术歌曲在第二个百年呈现出更多好的作品,将来在国际音乐舞台上享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廖昌永说,“期待在今后的对外交流中,不仅是我们唱外国的音乐作品,也有外国朋侪能用中文唱中国的艺术歌曲。” 每次演唱,内心都有一种亲近感 对话 解放周末:您多年来一贯致力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动力源自哪里? 廖昌永:早在上海音乐学院创立之初,蔡元培师长西席就定下了一手向西方学习、一手继续发展国乐的方向。整理国乐、传承经典,可以说是我们学校的基因。从周小燕老师起,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就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音乐会上如果唱两首作品,必须有一首中国作品;如果唱五首作品,不能少于两首中国作品。 就我自己来说,我心里一贯有一个遗憾:我参加过不少国际声乐比赛,比赛曲目一部分是歌剧、一部分是艺术歌曲。歌剧以意大利歌剧为主,而艺术歌曲则以法国及德奥歌曲为主,在规定曲目里从来没有中国艺术歌曲。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以为我有一种任务,让天下聆听中国艺术歌曲之美。 解放周末:要唱好中国艺术歌曲,难度在哪里? 廖昌永:首先不能只理解歌词表面的含义。艺术歌曲的歌词来源于诗词,演唱者对诗词的格律、文学史等都要有一定的研究。如果说西方艺术歌曲的情绪表达比较直接,那中国文人则常常咏物抒怀、托物言志。比如有些诗表面上写的是深宫闺怨,实在表达的是内心壮志未酬的感慨。只有理解隐蔽在笔墨背后的内涵,并用艺术手腕将其表现出来,这样唱出来的作品才更深邃,艺术性才更高。 解放周末:中国艺术歌曲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廖昌永:是的,中国音乐与绘画的关系是很深的,中国字画中所讲究的笔墨与音乐有共通之处。中国字画讲究线条,而中国音乐讲究旋律;中国绘画讲究位置经营,我们在演唱时也要“经营”,不能唱成一张白纸、一杯白水。音乐的强弱快慢、轻重缓急与用笔的迁移转变提顿是一样的。比较之下,西方绘画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中国绘画和音乐结合得那么紧。 解放周末:在演唱技巧上,中国艺术歌曲的咬字与韵味是否也大有讲究? 廖昌永:的确,要唱好中国艺术歌曲,除了要理解歌词的内涵之外,还要找到歌曲里的逻辑重音,从而更好地表达歌曲的内容。因此,我们在总结中国艺术歌曲这100年走过的进程时,要总结诗词的发展进程,也要研究若何根据诗词的格律来进行创作,并在咬字、吐字上总结出一套演出理论体系。 目前正在操持中的《中国艺术歌曲16首》将按国际标准以高中低音版本、4种笔墨对照、国际标准注音并合营中文标准朗读音频的办法出版。我想,如果全天下都能理解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中国艺术歌曲,那全天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对天下美好和平的渴望可能就会更加理解。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音乐的沟通能力有时候比措辞更强。我想尽自己的所能为传播好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热爱中国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周末:您曾经演唱过许多艺术歌曲,哪些作品曾经深深打动您? 廖昌永:每次演唱中国艺术歌曲,我内心都有一种亲近感。我从小就比较喜好古典诗词,在演唱这些作品的时候,情绪是从我内心流淌出来的。 我所选择的歌曲都是我很喜好的,只有当我自己被冲动了,我才有可能去打动不雅观众。1999年,我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当我唱起《老师,我总是想起你》时,溘然想起自己从四川来到上海,穿着布鞋走进上音的情景。那时候我完备是一个音乐上的“小白”,在几年的学习过程中,在周小燕等老师的帮助之下,我终于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取得了一点成绩,而个中的酸甜苦辣唯有自知。那一刻,一幕幕画面在我脑海里闪现,眼泪掌握不住地流了下来,有些不雅观众也流下了眼泪。我想,这便是音乐的力量。 解放周末:好的音乐能让听众从中探求到自己的影子。 廖昌永:是的,实在每一次在演唱和学习这些作品的时候,对我自己而言都是一种警觉,提醒自己该若何面对生活,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敬畏生活、敬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