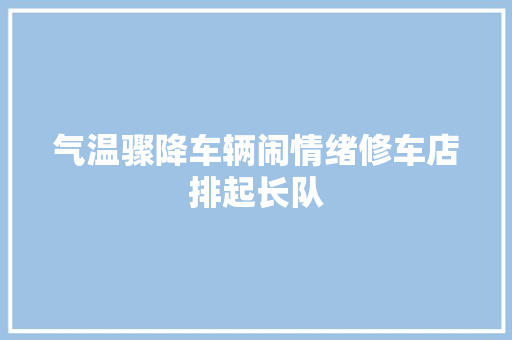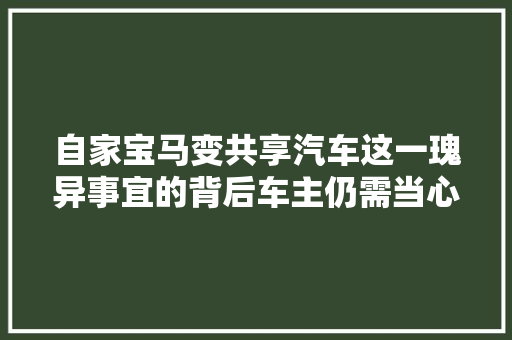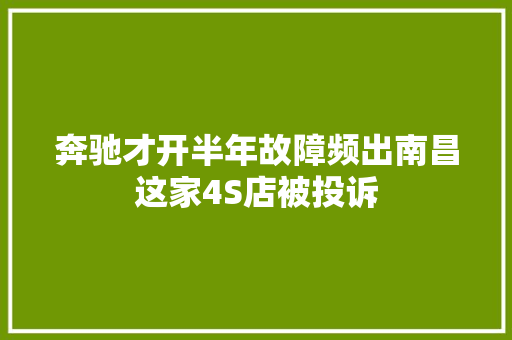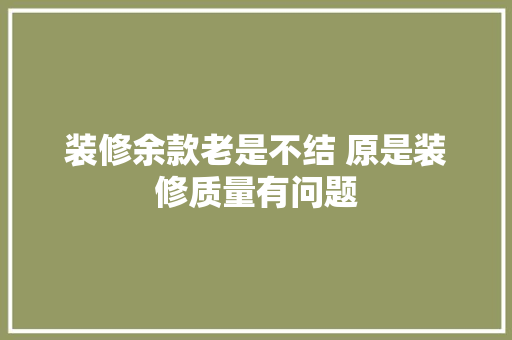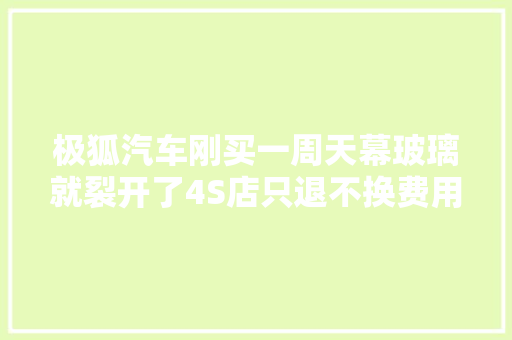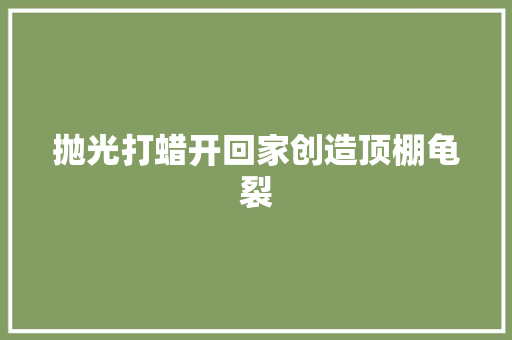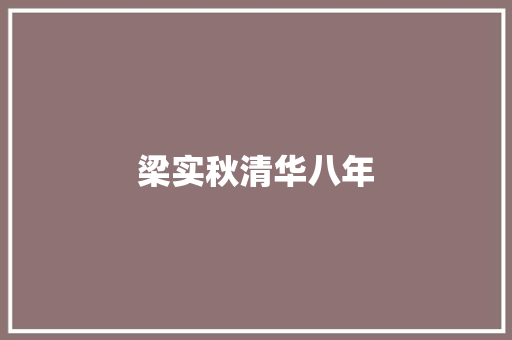2022年7月8日,祝总斌师长西席走了,享年九十二岁。是王铿兄见告我的,我并不以为溘然,毕竟这样的高龄,哪一天谢世,也说不上意外,但仍旧感到伤感。伴随伤感的,还有遗憾,由于自发生疫情后,我再也没有拜访过他。
初见祝师长西席,是研究生口试时。他身材不高,比较清瘦,戴一副浅白边框的眼镜,亲切温和、民平易近,这冲破了我对北大教授不苟言笑、严明端庄、令人陡生敬畏之感的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蓝色中山装上衣,与白、绿一样,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盛行色式。这种颜色、格局,在八十年代末已不多见,到我口试的九十年代初,可以算得上复古的“时髦”装了。在我的影象中,北大读书六年,能和祝师长西席撞衫的,只有季羡林师长西席。祝师长西席穿过其他色式的上衣,比如咖色夹克,也戴过玄色边框的眼镜,但于我而言,初见的印象却永久挥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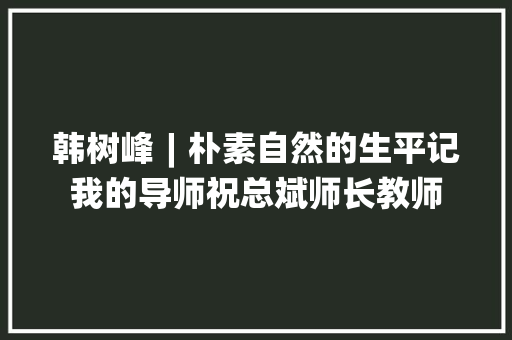
祝总斌师长西席授课中
祝师长西席待人温和亲切,生平与人为善,是大家公认的,孟彦弘兄曾有经典的评价:“祝师长西席的为人,可谓‘口碑载道’。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据祝师长西席回顾,他曾担当过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帮忙系主任邓广铭师长西席的事情,邓师长西席有时对他很“不满”,质问他:“小祝,怎么在你的眼里从来没有坏人?”他对人之好,于此可见一斑。在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1989年秋,我曾就考研一事写信向一些老师请教,有的老师一问一答,有的有问不答。祝师长西席复书及时,激情亲切严密,不仅有问必答,而且特意叮嘱,要翻阅一下《资治通鉴》,并提醒我加强外语学习,以避免多数偏僻地区考生的覆车之辙,信末叮嘱事情、备考期间,把稳保重身体。覆信字里行间充满殷殷关怀之意,令人倍感温暖。在我读书的年代,导师很少和学生一起用饭,在我的印象中,祝师长西席和田余庆师长西席从未特意宴请过学生们。不过,我事情往后,祝师长西席曾几次约请我与妻子用饭,而且见告我,这是他一定要做的。后来他和师母在中关园附近的郭林宴请了我们,当时这是一家相称有名的餐馆,分店遍布京城,可谓无处无郭林,可惜现在已经难以觅得一二了,不过温馨的场景却至今难忘。
祝总斌师长西席与作者的通信
祝师长西席作为硕、博士导师,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领路之人。但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止于学术,而是包括诸如传授教化、为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他是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少数人之一。
和对待其他人一样,祝师长西席对学生同样温和亲切。不过,温和亲切并不代表对学生放任自流,任其所为。九十年代初,剪刀加浆糊的纂书风气正浓,书商尤其瞩目于北大的师生。入学之初,祝师长西席对我殷殷叮嘱,大意是说,他作为老师,不会参与这种事,我作为学生,也同样不能参与,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否则必定影响学业。后来写硕士论文,找题目险些耗尽了我的精力,有次偶尔和祝师长西席谈及某方向的老师为学生确定题目,而且哀求学生必须照做的事情。他听后说,我们魏晋三位老师(另两位为周一良、田余庆师长西席)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魏晋南北朝方向的学生必须自己确定题目,否则就不要毕业。我倒没有向他讨要题目的意思,由于我早就从之前的学生那里听过这样的传闻。但他笑着说这番话时,语气相称武断,毫无转圜的余地,估计要也白要。在他的“逼迫”下,我来回翻书,苦思冥想,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当时还是往后,我对自己的硕士论文很不满意,不过于我而言,仍不无意义。在祝师长西席的鞭策和扶持下,我踉踉跄跄迈出了这一小步,但却是我今后独立从事历史学研究迈出的一大步。
那时读研,学分哀求不像现在这样高,历史系古代史专业所开课程不是很多。我所修的学分中,祝师长西席的课程最多,分别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国古代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占了几近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六个学分的《资治通鉴》课,那就将近一半了。
教室上的祝师长西席,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板书银钩铁画、浑雄遒劲,有时打动手势,颇有传染力,与课下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很难想象,他略嫌瘦弱的身躯中蕴藏着如此兴旺的精力。一堂课结束,他的眼镜边框以及袖子上常常沾满粉笔尘末,这时也常常有学生围着他,向他请教问题。这种场景总令我遐想到身穿工人蓝服装在车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事情的老工程师。我从事传授教化事情往后,仍旧受益良多,这既包括他的详细传授教化办法,也包括个中通报出的做人干事的态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讲授提要
开课之初,祝师长西席会给学生发一份油印资料,内容包括讲授提要、参考书、复习题,这在大学教诲程式化的本日,已成制度规定,但在当时,却并不多见。古代政治制度是祝师长西席用力最勤、贡献最多的研究领域,教室内容不雅观点新颖,胜义迭出,无论初学者还是有所阅读者,从他的详细考证以及宏不雅观见地中,均可以各得所需。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认知,便是从这门课开始的。史学史尤其是法制史对多数学生来说,相对而言比较陌生。讲授过程中,祝师长西席清晰有序地梳理线索、构筑框架,同时也将自己的诸多独到见地融入个中。往后我对法制史有所阅读,与这门课程有很大的关系。至于魏晋南北朝史,是祝师长西席最为善于的研究领域,课程的精彩纷呈自不待言,后来我开设此课,无论构造体例还是详细内容方面,都从这门课程中接管了不少养分。
周一良师长西席以“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形容陈寅恪师长西席上课之精彩。祝师长西席的课程内容充足丰富、逻辑谨严周密,极富人格魅力,听他的课,也相称过瘾,是一种极好的享受。
《资治通鉴》课并不在教室上讲授,而是一门读书课,地点在祝师长西席家中的书房。所读时段为自秦朝建立到隋朝统一,两周谈论一次,一次十卷,共三个学期。祝师长西席带我们读《通鉴》,相称程度上是师生之间自由而又平等的学术互换,学生可以自由提问,也可以自由评论,中间没有什么界线。对我们所提的任何问题,他有问必答,耐心细致,在他看来,只有有问题与没有问题之分,而问题本身却没有稚子与深刻、大略与繁芜之别。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会向我们提问。以他的心性,该当没有监督学生读书的想法,但这种办法对知识储备险些为零的我而言,颇有点像“照妖镜”,如果两周没阅读《通鉴》,很难不会现出原形。
问答中间,祝师长西席常常会从书架上抽出干系史乘,将史料展示给学生;有时所需之书在隔壁寝室,他会不辞辛劳,来回于书房寝室之间。历史研究的言之有据,无一字无来处,通过这样的不言而教,在学生心中扎下了根子。他所展示的史估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汉书·天文志》,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当时,对多数学生而言,《天文志》无异于天书,大都会略而不读,偶有阅读者,也难求甚解,而且当时的历史学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但祝师长西席给我们讲解《天文志》,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带有独到的见地。不仅是《天文志》,举凡史乘中其他偏僻冷门的知识,他大都能娓娓道来。在《我与中国古代史》中,祝师长西席谈治史心得,强调要懂一些笔墨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能、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实在,他对这些知识不仅仅是一样平常的理解,而是有很深的理解,这在他的文章中时有表示,有的乃至写成了专业论文。在我认识的学者中,论知识的丰富渊博,少有人能出祝师长西席之右。
祝师长西席固然早在我备考时,就提及《通鉴》的主要性,但当时我对历史学研究并不理解,没有太在意。读书课上,在他谆谆教导的勾引之下,对这部经典著作的主要性,我的领悟逐渐加深,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发展线索因此有了基本的理解与节制,此段历史的知识框架构造也由此得以建立。读书课对我的影响不止于基本历史知识的获取。祝师长西席的民平易近、亲切温和,对学生提问不厌其烦的逐一作答,师生间自由而平等的闲谈式学术谈论,对初学者是很大的鼓励。三个学期的读书求学,师生间的“坐而论道”,气氛自然而又温馨。经历这样的熏陶,我的提问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问题意识由此逐渐养成,对学术研究的自傲,也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郑板桥有诗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祝师长西席的学术境界和传授教化能力,我自然难以企及,但我的学术研究得以起步,能够步履蹒跚地前行,特殊有赖于他在《通鉴》读书课上的悉心扶持与自然熏陶。事情往后,我与学生相处的态度与办法受他的影响更大,方方面面留下了他的烙印。
祝总斌师长西席在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祝师长西席的课程或者是此前学术成果的积累,或者后来转化成了新的学术成果,因此,他的研究领域相称广阔,政治制度史、政治史、法制史、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险些无所不涉。令人折服的是,这些研究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是不落窠臼,推陈出新,个中也不乏有奠基开拓之功的作品。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祝师长西席的代表作,也是政治制度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书中对史实的校勘,抽丝剥茧,结论迎刃而解,其“论从史出”的深厚功力令人拍桌赞叹;至于见地的新颖独到,则给人线人一新之感。这里不拟对此书进行全面的评论,仅就孟彦弘“此书是近年学界所极力倡导的‘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方法”的评价,结合祝师长西席其他文章,略作补充解释。
就制度的发展变迁而论,从纵的方面,祝师长西席特殊看重追源溯流,在他的笔下,任何制度都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渊源有自,相互衔接,而且经由踏实细致的论证,自然而然地涌如今读者面前,决不突兀。从横的方面,他特殊看重剖析同一时空下诸种制度之间关系的繁芜性,这种关系从来不是僵化不变的,个中既有冲突与对立,更有折衷与合营,而制度就在这种流动不居的关系中有了变革与发展。比较范例的例子是,他在《西汉宰相制度变革的缘故原由》一文中对中朝官制度、领尚书事制度与丞相、三公关系的剖析与论证,读者可以从中充分认识到各种制度本身的弹性以及制度关系上存在的弹性。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伶仃的,而是与人事活动密切干系。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曾指出:“制度是去世的,人事是活的,去世的制度绝不能完备合营上活的人事。……中国历史上曩昔统统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合营?”言外之意,活的制度必定与活的人事相合营,制度因人事而变。祝师长西席的政治制度研究,与这一意见的契合之处比比皆是,乃至可以说,他的制度史研究在相称程度上是当时人际关系、政治活动、社会背景乃至人物性情的另一种表示。比如他对中朝官的剖析,指出汉武帝时期及其往后的差异性,个中时期背景、天子个人性情都在发挥着影响。又如,他创造《文馆词林》所载晋元帝诏书以“门下”开头,敏锐地认识到,这可能意味着从此时开始,出诏需经门下,门下省有审核诏令的权力。不过,史乘中没有详细案例可以印证,他将这一问题与王、马之间的政治抵牾以及王导担当录尚书事、中书监等职务奥妙地联系在一起稽核,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他没有僵化地看待这一审核权,而是特意指出其在东晋并没有固定下来,直到南朝方成为正式的制度,而且封驳权的性子从限定权臣变为决策精确的保障。类似这种制度的兴衰存废、浸染大小与人事、政治活动密切联动的稽核,险些贯穿《宰相制度研究》全书,而在《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子、浸染》《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等文章中也屡有表示。
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可能存在着差异,祝师长西席研究政治制度,固然关注机构组成、职官权能的干系规定,但更关注其实际运行情形。《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开宗明义对两者加以区分,指出对皇权形成制约的详细政治制度是经由历朝历代反复总结履历,终极固定下来的;君主实际行使权力时,则可以超越任何制度规定,不受任何约束。《宰相制度研究》对汉魏三公、尚书、中书、门下的剖析,终极都落实在了实行层面,并从实行情形的变革磋商制度的变迁。值得把稳的是,祝师长西席对文书的流转状况十分重视。《宋书·礼仪志》所载关事仪留神者少,他对这件仪注详加阐发,理清了行政文书在太常寺、尚书、门下、皇太子/天子之间流转的繁芜过程,刘宋中枢机构政务运行的实态得到了相称细致的揭示,而门下省平尚书奏事制度的固定化,也由此得到了充分有力的证明。《高昌官府文书杂考》就高昌国的政务文书进行深入剖析,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篇稽核高昌国文书的专文,而是将其与中原政权的政务文书比较,不仅阐明了前者对后者的仿效、摹拟以及其间存在的差异性,而且中原政权主要文书的运行流转状况也因此得以明晰。至于对文书名称及文书内容中晦涩难懂的诸多观点的考释和辨析,则对后世理解这些文书的内容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极具参考代价。几十年过去了,伴随简牍、文书等考古资料的源源不断出土,文书学以及与此密切干系的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但祝师长西席的研究成果放在当下,仍不失落其学术生命力,他对这一领域的贡献是无法令人忽略的。
通不雅观祝师长西席所有论著中涉及的政治制度,经由他的剖析,都不是生硬呆板、僵化不变的,而是具有灵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特性。制度有源有流,有兴有废,与政治事宜、人事变迁、人物性情、文书流转乃至包括思想不雅观念(可参《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关于儒学与两千年皇权变迁关系的剖析)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在他的笔下,政治制度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钱穆师长西席强调论制度应与人事活动合营,祝师长西席是这一倡导的践行者;现今学界盛行“活的制度史”不雅观,除人事而外,还强调其他诸多成分对制度的影响,祝师长西席从多层次、多角度不雅观察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无疑是“活的制度史”的先行者。
法制史研究是祝师长西席另一个取得精彩造诣的研究领域。《“律”字新释》首先回嘴了将“律”与音律相联,引申为法律之“律”的大略说法,然后从字形构成入手,指出“聿”字由手握笔以刻画甲骨器物之状,引申指刻画工具——笔,具有区分之义,并进一步考证以“聿”为字根的字或与“聿”同义,或蜕变指界线、规矩、行列等义,从而阐明了“律”为什么具有规范、准绳等义,乃至被用为法律之“律”的缘故原由。该文篇幅甚短,不过六千来字,但却办理了法制史上一个少有人留神而又十分根本的问题。在此文的根本上,《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一文通过严谨周详的考证,否定商鞅“改法为律”的定说,将其时间定于前260-前252之间;并通过剖析战国期间音乐调度社会功能的强化、度量衡的逐渐统一及推广、与“律”同音的“率”字早已用于政法领域等问题,深入阐明了“律”字得以取代其他诸多字词,从而成为古代成文法典专用字的缘故原由所在。两文展现的,不仅是祝师长西席令人惊叹的广博知识与史学考证功力,而且不具备笔墨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小学素养,是难以深入稽核并阐明清楚干系问题的。《略论晋律的“宽简”与“周备”》《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两篇长文作为祝师长西席法制史研究的代表作,阐释了《泰始律》两方面的重大变革。晋律的宽简、周备人所习知,但详细情形难解。祝师长西席考证了所省主要条文的某些详细内容及其针对的不同社会阶层,“周备”在律令之分、篇目体系完备及法律用语等方面的表现,并对晋律“宽简”的目的及何以能够做到“完备”提出了合理的阐明。晋律儒家化首先由陈寅恪师长西席概括提出,其后瞿同祖师长西席在系统谈论古代法律儒家化时,从制律诸人儒学素养的角度对晋律儒家化续有补充,但仍旧相称简单。祝师长西席的最大贡献在于,确定了儒家化的基本内涵即晋律对“礼”的精神与规范的接管。他将晋律置于从汉代礼、律两分到唐律“一准乎礼”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稽核,论证了晋律的承前启后性子及对唐律的形成所起的奠基性浸染。之后对“官吏得终三年丧”等六条晋律详细规定的剖析,是对晋律以礼入律的进一步解释。自此,“晋律儒家化”不再是一个笼统模糊的观点,而是有了详细的衡量标准,同时,儒家化的详细内容也得到了更为清晰深入的揭示。两篇文章的学术代价不言而喻,早已成为魏晋法制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范文。前几年我曾撰写《汉晋法律的清约化之路》一文,谈论魏晋法律与学术思潮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及晋律体例上的玄学化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两文的影响。
祝师长西席从事学术研究,有明确的目标而无固定的操持。所谓有明确目标,指其确定的生平完成百万字的成果;所谓无固定操持,指其并不会捉住某个几近题无剩义的专题不放,一定要写出系统、完全的专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共收论文三十六篇,这些研究涵盖的时段上自先秦下到明清,而且超过诸多领域,可以想象,论题之间欠缺紧密的联系是自然之事;纵然分量较重的政治制度史论文,也大多呈现出“各自为战”的特点。史学论著的系统性与独创性每每难以兼得,而“论从史出,追求新意”,是祝师长西席学术研究的宗旨,如果两者不可兼顾乃至存在抵牾,他宁肯舍弃系统性追求新意,而不是为追求系统性而捐躯新意。实在,他的课程讲义从来不缺少系统性,而且独到之见俯拾皆是,如果整理成专著,并不缺少学术代价,但他只是抽取了《政治制度史》讲义中有关宰相制度研究的内容,以专著的形式呈现给了学界,其他具有新意的内容则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揭橥。《宰相制度研究》固然系统、完全,但这并非他强力为之、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多年自然积淀的结晶,因此,与时下不少追求系统性但缺少新意的专著不同,该书无一处无心得,无一处无新意。实在,他磋商《史记》的几篇长文同样充满新意,如果与课程讲义相结合,稍加补充完善,即可成为一部较为系统的汉代史学史专著,不过要像《宰相制度研究》那样,做到全书皆是新意,对祝师长西席来讲,也不随意马虎做到。在这种情形下,他甘心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不少人做研究,特殊重视在某一个领域的“始终如一”,有时难免不免有为写而写的嫌疑;祝师长西席正好相反,对待研究工具,每每“喜新厌旧”,有感则发,无感则罢。或许由于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缘故,他从不画地为牢,将研究限定在一个固定的领域或时段内,像匠人一样反复制造毫无新意的作品,而是自若切换于不同领域、各个时段之间,不断奉献富有新意的佳作。他的多数研究主题相互之间短缺系统性、完全性,缘故原由即在于此;但他以“新意”为终极鹄的,担保了每篇作品独出心裁、新颖独到,而且绝不牵强附会,给人以瓜熟蒂落、迎刃而解的觉得,缘故原由也在于此。精良的史学经典论著从来不是为写而写、强力为之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在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人的研究中表示得尤其明显,而祝师长西席同样是个中精彩的代表。
文风朴素、简洁,是祝师长西席作品的另一个光鲜特色。他的论著不追求各段落之间的自然衔接,不追求措辞上的传染力,论述问题、缘故原由和表现时,常常以汉文数字、阿拉伯数字和天干表达,如俄罗斯套娃般层层叠叠,但层次极为清晰分明。他的作品如一束束钢丝扎成,精瘦干练,力感十足,几无一字可删。有人认为,这种风格与《宰相制度研究》脱胎于讲义有关,但他未在教室上讲授过的论文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想,他性情上的朴素自然或许起的浸染更大。记得我曾就论文的表达向他请教。他说:“前有翦伯赞,后有田余庆”,史学论文文笔流畅而且富有传染力的,非此二人莫属,但那不是刻意追求可以达到的;论文最主要的,在于说理透彻清晰,论据、论点表述清楚即可。实在,田师长西席同样重视文笔的简洁,表达也给人无一字可删的觉得。差异在于,田师长西席的无一字可删,是就阅读的美感而言的;祝师长西席的无一字可删,是就阐述的内容而言的。田师长西席文笔的文雅洗练,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祝师长西席文笔的朴素简洁,同样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祝师长西席将书房名为“材不材斋”,意思是自己在学术上不可能成“材”,但要以“材”为追求目标,这是他对自己学术上的定位,是自谦的说法。如果将他的为教、为学、为人综合在一起看,淡泊名利、朴素自然、心性善良对他是更为妥善的评价。
祝总斌师长西席(左)、田余庆师长西席(中)与作者
祝师长西席做研究,无名利之心,只是顺着学术的实质哀求和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然而然地读书写作。他不会撰写没有足够新意的文章,以为评职定等积累砝码。文章写出后,在哪里揭橥,他也并不看重,有的揭橥于现在看来级别并不高的刊物上;有的编入今人多以凑数之作应景的会议论文集中;较他年幼的研究者索稿以为自己祝寿,他也不会谢绝。《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一文长达七八万字,内容丰富厚重,对门阀制度的谈论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既可揭橥于期刊,也可以整理补充成专著,但他却将其放入了成于众人之手的上海公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第五卷中,这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难以做到的。不过,做到这点,于祝师长西席而言或许并不困难,所谓“文如其人”,对待学术的态度不过是他本性的移易罢了。
在现实中,祝师长西席则“人如其文”,生活办法极其大略朴实,不为追求物质生活勉力而为。他在外穿着朴素,家中则是水泥铺地,基本没有进行过任何装饰。住房名为三室一厅,实在客厅仅能容下一张不大的饭桌,寝室和书房也不很大,全体屋子的空间狭小逼仄。后来,北大在蓝旗营新建了一批住宅,大多数西席搬了进去,但祝师长西席仍住在中关园迂腐而且没有电梯的老房里,只是出于年纪已老上楼不便的考虑,从六楼搬到了别人腾空的二楼。他收入确实不算很高,如果勉力而为,未必无力购买,由于那时的房价也不算高。不过,为外物所累,有违他朴素淡然的本性,在勉强与自然之间,他宁肯选择后者。祝师长西席自己生活大略朴素,对别人却常常年夜方解囊。我毕业之初,他以为人为太低,一定要施以援手,我坚辞不受,却未获允准。对此,我无以回报,只能铭记师德,感念于心。
帮助他人,于祝师长西席纯属自然而然,不仅没有哀求回报之心,纵然对毕业后的学生登门看望这样的小事,也感到惴惴不安。只管高居六楼,告别之时,他仍会坚持将学生送至楼下。师母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八十多岁的祝师长西席亲自照顾,学生前往拜访,他会小心讯问待多永劫光,以便预作准备,彷佛很担心失落了礼节。祝师长西席总将学生视为同辈,这与田师长西席有所不同。记得有一次蒙田师长西席赠书,田师长西席以玩笑的口吻问在座的彦弘兄,题签是否可以题写“彦弘老兄”,后者连称“不敢不敢”,末了是“某某君存检”。祝师长西席却是实打实地把学生当成同辈看待的,给我的赠书题签永久是“树峰兄指疵”,个中包括我读研时的赠书。以是,祝师长西席的客气并非伪装,而是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我事情往后,一方面有时较忙,另一方面考虑到前往拜访,会给祝师长西席身心带去包袱,因此,看望他并不频繁。疫情发生往后,曾几次与彦弘兄相约一同拜访,终极却均未成行。就这样,机会几次再三错过,直至临终,再也未能见他一壁。
孔子评价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祝师长西席生平清寒而不觉其苦,于名利无丝毫争竞之心,得意其乐地畅游于传授教化与学术之中,确有颜回之风。他八十寿诞之际,田师长西席到场祝贺,说祝师长西席一定能写出《朝闻道集》这样的著作。《朝闻道集》是周有光师长西席一百零四岁高龄时所撰之作,祝辞奥妙借用此书,不落俗套且意境深远,个中既有对祝师长西席龟龄的祝福,也暗喻其对学术勤学不辍的追求,同时也暗含着对他高洁品性的赞赏。祝师长西席年事没有过百,没有写出这样的著作,但总结他生平的为人、为学、为教,确乎当得起“朝闻道”这样的评价。
7月19日,祝师长西席的家人与学生将他安葬在了昌平九里山公墓。全体义冢呈梯田形状,他的墓地在最上一层的末了一排,背倚山墙,其上布有一排黑白相间的琴键装饰,朴素而又自然。祝师长西席生前隐身于芸芸众生之中,不求卓然独立,而是通俗俗通、朴素自然地生活着,但本性之高洁又完备不同于流俗,可谓芸芸众生中的大隐士、真君子。他的墓地处于众墓之中,并不显赫,但又独立于众墓之外,恰与祝师长西席平素为人处世的风格契合。我相信,那排琴键奏出的,是宁静自然的乐曲,并永久伴随着天国里的祝师长西席。
祝总斌师长西席之墓
2022.08.07于时雨园
市价祝总斌师长西席逝世一月之际,撰写此文,以为纪念。
任务编辑:于淑娟
校正: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