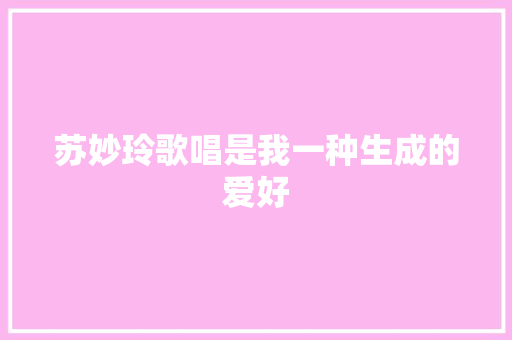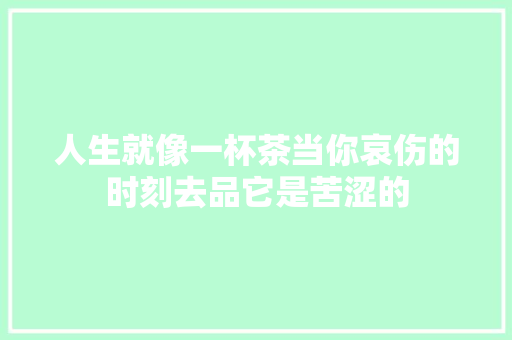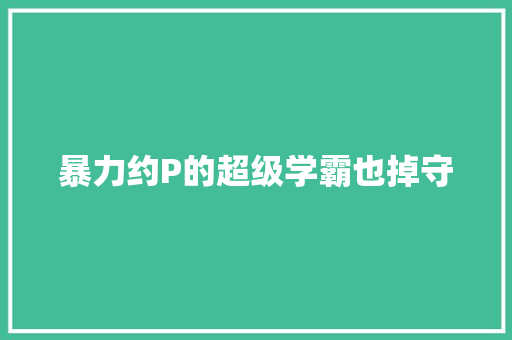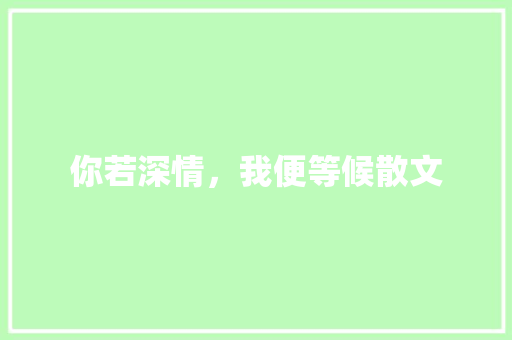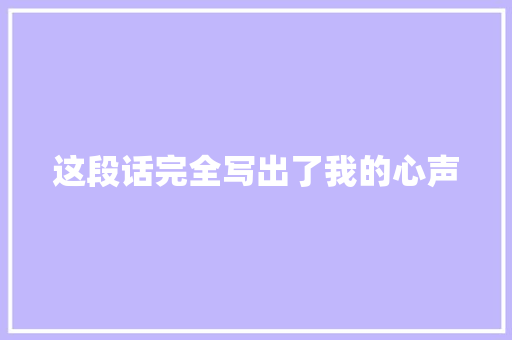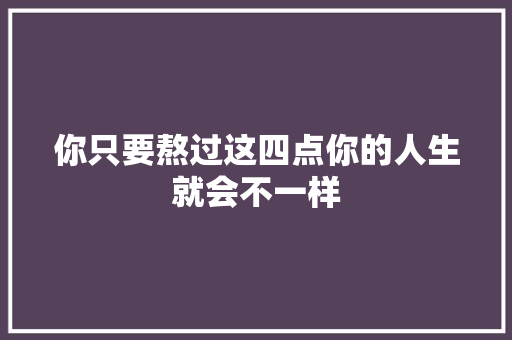她笑笑不答。不是不爱,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怦然心跳。她在心里说。
直到他涌现时,她的心才动了一下,只是微微地。他像一抹阳光拂过,令她的心不由自主地颤了一下,她想,这便是所谓的动心吗?

女友很八卦地说,情窦初开了吧,要不,我也做一回皮条客?
她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我没觉得,是你自己又犯花痴了吧!
你自己弃权的啊,我可要脱手了!
女友一脸女泼皮的样子。
她还是温婉地一笑:去吧,祝你成功,花痴。
又是月余,她在校门口偶遇他,阳光依旧。只是,身边多了一个女友,小鸟依人般的。是同室的那个花痴。她现在不仅是她的女友,还是他的女友。双重身份。
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心微微痛了一下。是痛,不是颤。很分明的。
他温和地一笑,和我们一起去吃大排档吧?
不了,我还有事。她找了个最庸俗的托辞,逃也似的走了。
怎么会这样?她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当初为何要把自己的幸福拱手送给别人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有些妒忌同室女友,她乃至期盼,她有一天会哭着跑回来说自己与他分离了。她以为自己有些变态,好好的一段爱情,为什么不能祝福?她想,可是她做不到。
她也没盼来那个她一贯期盼的,同室女友逐日带回来的,都是一脸掩不住的幸福。他们邀约她一起去嬉戏,她总是以各种借口婉拒。她怕,她怕看到女友和他在一起那幸福的样子容貌,入了她的眼,却变成了一根刺,扎在心里,模糊作痛。
她和他们刻意保持着间隔。乃至,有些生疏了。
没等来他们分离的,却等来另一个于她而言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女友远足时欠妥心从山上摔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命,下半身却失落去了知觉。
她的心里一团乱麻,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大家都说,他肯定会选择放手。
他依然像一抹阳光,带着微笑,细致入微地照料女友,并且,一毕业,他就和女友领了却婚证。这个传遍了校园,他急速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形象,好男人,这便是传说中的好男人。
是的,他的确是个好男人。她为之前自己的某些想法感到羞愧。
她连他们的婚礼都没有勇气参加,连夜去了另一个城市,裹起了自己。那一刻,她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实在自己是多么地爱他。可是,有些事情一旦错过,就无法再改变。
以是,她是哭着走的。为自己,也为他。这对他不公正,她知道这意味着他将把一辈子,献给那场无性的婚姻。
光阴荏苒,一晃十年,她从19岁变成了29岁。妈妈对她说,该嫁了。
她不知道自己还在等什么,还有什么好等的。这么多年,她再也没见过女友和他,只是间或听到关于他们的爱情——不离不弃的。
她愈来愈强烈地想见他一壁。
机会来了,去他的城市出差,办完公事后,尚有空隙,她按照别人供应的地址,找到他所在的单位。
她险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便是当年那位如一抹阳光般令民气动的少年。他正穿着工服在工厂里做工,汗水浸透了背心。她叫了他一声,他反应迟缓,木讷地转头四下张望。好半天才认出她来: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我们一贯都在找你。
哦!
他已苍老得不成样子,这还是他吗?她在心里问。
没办法,他说,几年前我就下岗了,她一贯不能康复,我兼职了好几份事情,你知道,药费什么都很贵的。他的光华已不复存在。
你结婚了吗?他问。
没有,我一贯一个人过。她说。
他的眼里燃起一些东西。实在……当年我很喜好你,只是,你太精良、太俊秀了,以是,我退居其次才和她……
嗨!
都过去的事了,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他又自嘲地说,望着青春依旧的她,他的喉结动了动!
他的表白让她加倍不自然起来,她能觉得到他体内彭湃澎湃的声音,彷佛要将自己淹没。这让她变得恐怖。
他说,你去传达室等我,晚高下班后我请你用饭……
那她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她问。
他一阵莫名地紧张,说,不碍事的……
在传达室等待他放工的间隙,她的内心忐忑慌乱不已。
她在心里问自己:这算什么?做一个拯救无性婚姻的志愿者,把自己献给他,用身体犒劳一下这个伟大的男人吗?她以为这有些可笑。她是在爱他,还是在可怜他——一个无性婚姻中的男主角。
末了,她逃了,不辞而别。仅留了返程的车费,她把剩余的钱装在信封里托传达室转交给他。
在回去的车上,她又一次泪雨滂沱,她知道,她做不了救赎无性婚姻的志愿者。乃至,连爱他的觉得也消逝了。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当初做了一个伟大而高尚的选择——和他的她不离不弃。
她溘然顿悟,这世间所谓的爱情,并不存在,归于现实只剩下婚姻,美满的、破碎的、残缺的,各种办法。遇上好的,便是一辈子,遇上不好的,大不了分道扬镳,只有好或不好,没有爱或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