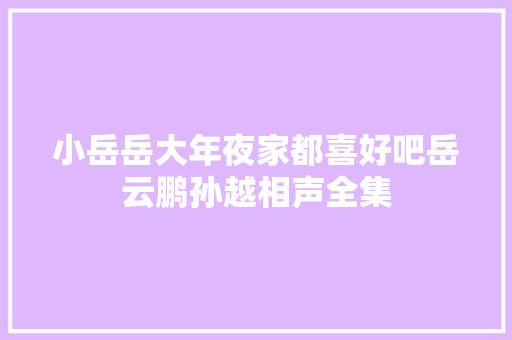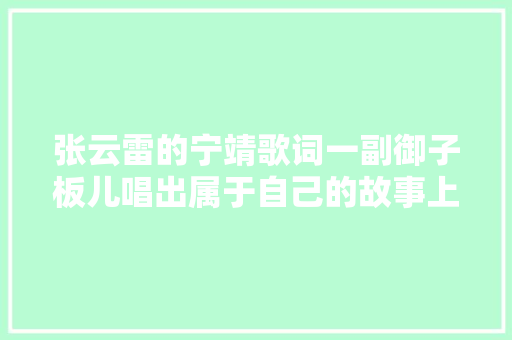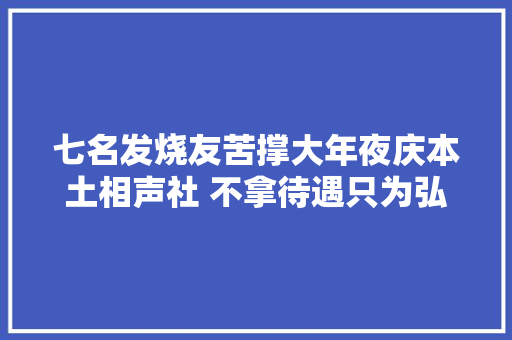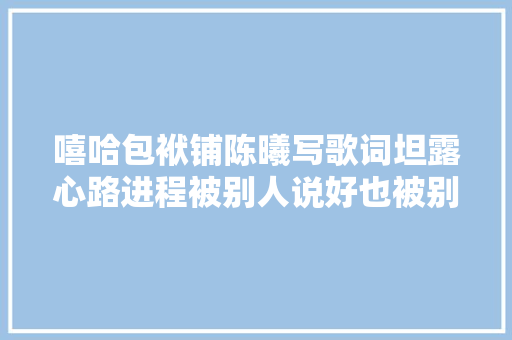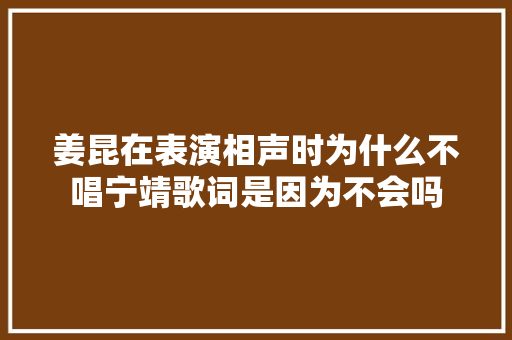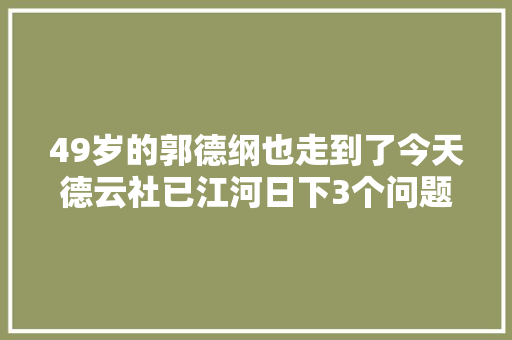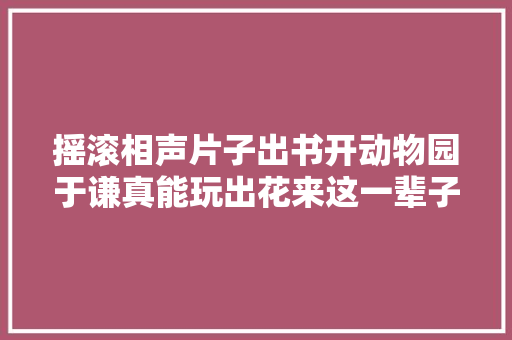德云社相声从海内火到国外,每次演出结尾郭德纲都会带着演员演唱太平歌词《大实话》,这是德云社已故创始人张文顺先生长西席留给德云社的宝贵文化遗产,如果是其他人带队也是必唱曲目。郭德纲常常在各种节目中通过现身说法的演出向不雅观众遍及相声基本知识,让不雅观众知道不是两个人在台上耍贫嘴、逗乐子便是说相声,而是和戏曲及其他舞台艺术一样都须要从小刻苦练习基本功。相声的基本功有说、学、逗、唱四门作业,这个唱就郭德纲常常强调的太平歌词,而正由于郭老师的不断“洗脑”,险些所有相声爱好者都已经接管了这个基本知识,乃至有些网友因此而得出了“不会唱太平歌词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的结论。此言一出,顿时扫倒了一大片有名相声演员,特殊是那些半路出家的主流相声演员,一句话分出了两个阵营,不知道郭德纲在反复宣扬太平歌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涌现这种局势?
郭德纲喜好传统曲艺,也善于各种传统曲艺,但为什么对太平歌词的地位就那么执着呢?
一、基本管理,太平歌词本来便是相声的基本功

喜好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相声的四门基本作业是“说学逗唱”,而个中的“唱”便是唱太平歌词,其他的唱戏曲、唱小调、唱盛行歌等都属于“学”的范畴。这在郭德纲出名以前知道的不雅观众并不多,直到德云社相声开始火起来之后,才被更多不雅观众知道并认可,现在险些成了金科玉律,如果哪个相声演员公开说不会唱太平歌词估计会被不雅观众看低一眼,就这么邪乎,谁也不会为此狡辩,那更显得无能。
最早的相声艺人张三禄、朱绍文本是八角鼓丑角儿艺人,离开后首创了以逗笑为紧张特色的相声行当,和别的民间杂耍一样都在街头、闹市露天演出(行话“撂地”,
这个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延续了上百年,每个相声艺人结合自
身情形或多或少都会学习,期间还出了不少精良的太平歌词大家,上世纪20年代的相声艺人汪兆麟和吉评三便是两个承上启下的主要人物。汪兆麟、吉评三在原有太平歌词的曲调、构造上进行大胆创新,常常根据时势新闻,即兴编成太平歌词演唱,比旧调婉转动听,新太平调从京津翼唱到上海滩,并分开相声成为独立曲种,他们乃至把演唱太平歌词作为主业。其后,善于新太平歌词的有名相声演员有很多,个中侯宝林自幼学京剧,嗓音清脆洪亮,在唱腔上别具一格,在天津首演更是一炮走红,倍受不雅观众喜好。
到40年代,相声艺人逐渐地走进了茶社、小戏院,已经不依赖太平歌词招揽顾客;建国后,相声艺人进入剧团成为公职演员,统一安排演出,更不须要去招揽顾客,太平歌词由此彻底从相声舞台上消逝。虽然政府也组织编写了一些新剧目演出,如《刘老汉过年》、《刘胡兰》等,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唱,和相声演出相去更远。
太平歌词的没落与相声的演出环境变革有直接关系。解放前的相声属于自由放养模式,有真本事的才能活下来,会吆喝的才能赢利,达尔文说这叫“良好劣汰、适者生存”。
二、继续与传承,不能让太平歌词变成濒危的“非遗”艺术
郭德纲是在相声曲艺窝子里面熏大的,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传统曲艺非常喜好,很小就开蒙、拜师,学习评书、相声、梆子、太平歌词、评剧等多种曲艺,为他往后的奇迹奠定了坚实的根本。8、90年代,相声借助电视重新走向繁荣,但太平歌词却由于没有实用性和白沙撒字一样濒临失落传了,当时还能演唱全本的相声演员百里挑一。天津的佟守本和北京武警文工团的王双福等相声演员深感太平歌词的濒危处境,挖掘、继续、整理了一批传统剧目,并报告非遗项目,分别成为天津和北京太平歌词的“非遗传承人”,为抢救太平歌词做出了贡献。
而从小跟随老艺人学习过太平歌词的郭老师,更是身体力行,各处搜集整理剧本、学习传授演出,在德云社舞台上展示着传统曲艺的文化魅力,努力让年轻不雅观众接管并喜好这些被丢到墙角旮旯的民间艺术。现在大家比较熟习的北京小调《探净水河》和太平歌词《白蛇传》、《大实话》、《送情郎》、《大西厢》等都深受年轻人喜好,并被网友传唱,从影响力来说,郭老师对太平歌词等濒危曲艺的贡献要远比佟、王二人更有效果,他让传统曲艺年轻化,更有生命力。
我们现在所传唱的太平歌词基本都来源于郭德纲、德云社演员,曲调婉转、简洁,很多唱段可以像民歌、盛行歌曲一样朗朗上口。而真正听过老版本太平歌词的朋友估计不会喜好,由于它不符合我们现在对音乐的审美,可以用“陈词旧调”来形容,
不仅是太平歌词,其他民间曲艺也得到了类似的报酬,个中最有名的便是北京小调《探净水河》。《探净水河》本是北京地区盛行的民间小调,但后来失落传或被某些人珍藏起来,郭德纲就从东北二人转版本改编成现在广为传唱的德云社版本,以及又被张云雷改编成万人大合唱的吉他伴奏版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北京某老艺人演唱的、听说是原版的《探净水河》,听完了你也就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传统民间曲艺会成为“濒危”艺术,抱残守缺、陈词旧调怎么能打动新时期的不雅观众?没有不雅观众欣赏的艺术早晚都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相声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吸引不雅观众、至心为不雅观众做事,而是想着教养不雅观众、等着成演出艺术家,早晚也要被某些人的一己私利折腾成为“濒危”的民间艺术。
三、差异化经营,把太平歌词等传统曲艺变成德云社的特色标签
郭老师进京创办德云社后,做了两件主要事,担保了德云社的成功。
1、给德云社找准市场定位,差异化经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相声已经被折腾的失落去了昔日的光彩。郭老师第三次北漂在走街串巷时创造不是老百姓抛弃了相声,而是主流相声抛弃了老百姓。1996年他和张文顺、李菁创办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前身),让相声回归小戏院,回到老百姓身边,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相声,唱老百姓爱听的小曲小调,充分发挥自己善于传统曲艺和传统相声的上风,以此差异不再受欢迎的主流电视相声。这个差异化定位让德云社有别于那些只会说电视相声的主流演员,让不雅观众在电视相声之外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德云社始终坚持以传统相声为特色,进一步履行差异化营销,郭德纲善于的各种传统曲艺有了用武之地,而太平歌词的浸染在这时候显得尤为突出。太平歌词作为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但很多演员完备不会,郭老师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想法拿太平歌词做起了文章,这文章做起来很陵暴人,就像海湾战役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完备是一场不对称战役!
“太平歌词才是相声的本门唱”说的是个大实话,让那些对手无可辩驳,但又短韶光学不会,只能按郭德纲的思路走。郭老师和他的徒弟们的太平歌词、小曲小调唱越好,贯口说的越溜,不雅观众们的认可度越高,那些曾经的相声大腕儿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大名鼎鼎的姜主席在天津被不雅观众盘出了汗,就由于不会传统相声的贯口活,如果让他唱太平歌词怎么办?这个难度可比贯口还难,与他同代的相声演员又有多少会这些传统活呢?流冷汗的恐怕不止姜主席吧!
2、给传统相声定标准,打击假冒伪劣演员,净化相声环境。郭老师借太平歌词通报了这样一个逻辑:真正的相声演员得会太平歌词,会太平歌词才可能有传统相声功底,有传统相声功底的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这个逻辑随着德云社的发展壮大已经深入民气,逼得年轻一代相声演员重新学习传统相声技艺,包括传统戏曲、太平歌词、小曲小调、贯口、打竹板等,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青曲社班主苗阜唱的《送情郎》、《探净水河》,如果听过请给大家分享一下感想熏染。
这个逻辑也让一批学业有成的年轻相声演员走上了充满荆棘的创新之路,如张康贾旭明、高晓攀尤宪超、李丁董建春等高举创新大旗,现在就被卡在“新”字上进退维谷,张康贾旭明也难有佳作了,高晓攀在台上只剩下卖脸,李丁董建春的校园相声还要走多远?创新相声比较成功确当属“相声新势力”,他们的创新与别人不同,他们是在继续传统的根本上大胆创新,卢鑫玉浩如此,最近在《在相声有新人》舞台号称锦鲤附体的窦晨光常鹏旭便是受益者。
新派相声对郭德纲、对德云社其他演员来说是个弱点,对别人来说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想从坑里爬起来谈何随意马虎,创新对演员的基本功和知识面哀求太高了。青曲社的班主苗阜在这方面故意思,既想说传统相声,但基本功又有欠缺,能拿脱手的传统相声有限,创作的《满腹经纶》《登时书柜》等相声作品很成功,但这算是传统相声吗?不过是用传统文化包装起来的有自己特色的“传统相声”,也算有新意,取得了意外的收成。从此往后,苗班主就爱上了这种套娃游戏,把错字游戏搬上了流水线,也真是辛劳王声了。如果想凭这样的伪传统相声寻衅德云社,只能说充满了抱负,姜主席编辑了一套《中国传统相声大全》值得看看,他虽然不会说,但他为保存传统相声也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结束语
郭老师对德云社的定位,和对太平歌词的反复宣扬,可以看出郭老师背后有高人出谋划策,既复活了传统曲艺,又巩固了德云社传统相声的地位,同时还削弱了主流相声演员的霸气和傲气,一举三得,造诣了本日的德云社,也让全国相声不雅观众重新认识了传统相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