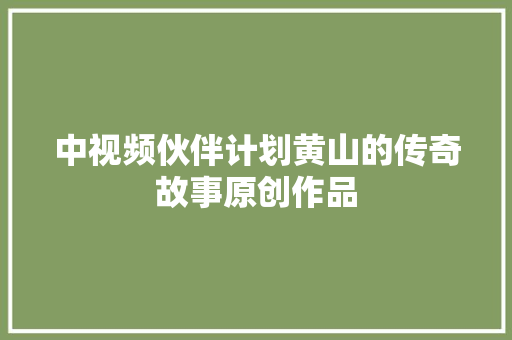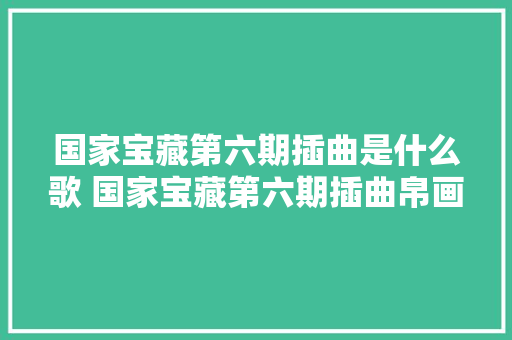线条是河流、公路,余下的那些点、团,还有不规则的条块,每每对应着聚落。最初是什么样的人群来到这里生活,又是依据什么样的特色给它命名呢?大多数时候,唯有演化为城市景不雅观的街区、建筑在其历史简介上讲述着前世今生。我们大概未曾想过一个问题,在当代社会,如果一处聚落未得到国家(state)的命名或承认,并不会涌如今舆图上,只管在坊间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叫法称呼它。当城市大开拓延展至这里,未被承认的聚落,以及与它有关的统统建筑,也就成了“违建”。它是被否定的,是被认定须要改造的。
在我国台湾台北有一处人气颇旺的景点,按时下的说法,或可叫它著名网红打卡地。而它,实在是一个由违建社区整建而成的新“历史名胜”。在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陈映芳与我们聊一聊宝藏岩。地处台北市中正区的临虎空山北麓(小不雅观音山南侧),因阁下的宝藏岩寺而得名。不过2007年1月陈映芳去那儿时,它还不是现在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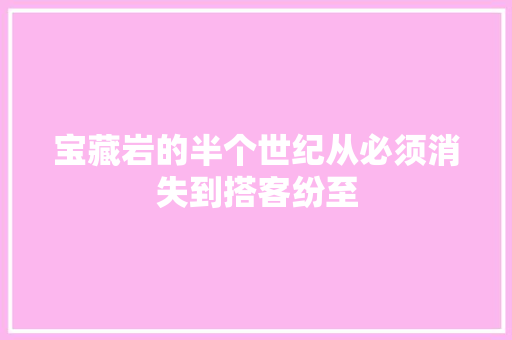
宝藏岩。作者摄于2007年1月。
“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天下取得联系。这并不虞味着人们就此“不打仗”。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气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影象、某次与家人告别或相逢的感情、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各类,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落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过去多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贯致力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研究。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思辨精神的学术文本。去年她退休了,书评周刊借此约请她开设专栏,换一种身份和视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访和查找资料中碰着过的聚落、场所,还有人。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凡添入个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并无特定的撰写章法,不过是有感而发。
本文为第三篇:从违建住宅群到共生聚落——宝藏岩的半个世纪。
“聚落·场所·人”往期推送:
第一篇:那些是村落吗?被误读的山西沁河流域城堡群
第二篇:上海世博园区的前世今生——“后滩”的故事
眷村落的事
新竹眷村落博物馆。作者摄于2007年1月。
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编者注:指2007年初),为了参加台湾的文化研究年会。会议结束后,台湾“清华大学”的吴介民师长西席和他的研究生激情亲切地带我坐高铁去新竹看几个他们的野外。去之前他们搜聚我见地:“有没有你自己想看的地方?”我不假思虑地回答说:“想看看眷村落。”
当时的我,对台湾现实社会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影视作品和学术文本。和许多大陆人一样,对付半个多世纪前迁往台湾的军宦海、文化知识界等各界职员,还有他们的家眷及后代的命运的关注,是我们试着将民国时期与现实中的台湾社会对接起来的紧张办法。而在各种“外省人”的故事中,“眷村落”无疑是一个主要的符号。
吴介民师长西席见告我,台湾各地的眷村落已经陆陆续续被拆除了。不过,新竹市里有一个眷村落博物馆可以去看一下。
新竹原是国民党的“空军”基地之一,那儿曾建有一批眷村落(馆中先容为46个)。“新竹眷村落博物馆”是一个民营机构,里面的事情职员多为外省人的第二代。馆内陈设的,紧张是各种照片、证件,还有食品供应票证,以及生活用具实物——不少是用炮弹壳等做成的,其余还搭有一些街景。想来,在眷村落二代的心目中,那些场景和实物,是大历史的见证,也承载了他们动荡岁月中的童年生活影象。
新竹眷村落博物馆。作者摄于2007年1月。
没想到隔天在台北,却看到了一个现实中的另类的眷村落。
那天,台湾艺术大学的孙瑞穗博士带我和几个朋友去参不雅观了几个城市更新项目,末了一个点,便是宝藏岩。
宝藏岩聚落并不属于正式的眷村落,在很永劫光里,它一贯被台北市政府归入“违建住宅”一类,大部分台北市民实在也不太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980年,由于台北市政府以整顿市容与水利坚持等情由,推出了拆迁该地所有违建的操持,由此引发了当地居民抗争。再后来一批学者、学生、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还有租住在里面的艺术家等开始参与纷争,这个社区的存废问题于是成了舆论焦点,宝藏岩也由此进入到大众的视野。
山崖上的历史聚落
2007年时,关于宝藏岩建筑群的整建方向,台北市政府已经开始妥协。但环绕详细的方案和操作方案,当地居民和文化局之间,依然处于僵持状态。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它原来的大致样貌,并碰着了几位原住居民和在那儿致力于表达、抗争的“行动艺术家”,还听到了由他们讲述的一些宝藏岩故事。
宝藏岩聚落是一个建在山崖上的贫民社区,从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上去,两边全是错落地搭建于岩石间的自建房,有一些已经在拆迁过程中人去房空,有一些还住着人。还有的成了行动群体的办公室——险些所有屋子的外墙面上,都被他们涂上了色彩斑斓的各种涂鸦和口号,还张贴有不少公开信的复印件。在一些屋子的墙面上和门窗上,还可以看到标志着“外省人”家国情怀的旌旗和对联。
宝藏岩违建房最初的搭建者,是驻扎于附近军营的老兵。那儿的山麓早在日据时期便是军事要地,战后又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台北北区“司令部”所在地。加之附近还是台北主要的水源地,有自来水园区(“私邸净水厂”),以是一贯驻扎有不少军队。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两岸关系稍现松弛,一些驻军老兵想要在军营外边有个自己的去处,便来到山崖边,就地取材,用鹅卵石,荒弃堡垒的旧砖块等垒建起简陋的棚屋。再后来,有些退伍老兵由于渴望有个家,也陆续来到这儿,用捡来的或便宜的材料——木头、空心砖、水泥钢筋和铁皮等,搭棚居住。同期间,还有一些外地来台北谋生的低收入新移民也来到了宝藏岩。干系信息显示,至上世纪80年代止,聚落规模已靠近四公顷(个中有几栋屋子是原军营宿舍),居住有两百多户人家。
宝藏岩。作者摄于2007年1月。
除上面这些群体之外,还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也租住在里面。那天我们碰着了一位正在激情亲切地投入行动的画家,他说:“我们住进来一看,这儿正要被政府逼迫拆掉,那怎么行?”于是他们开始用艺术的办法参与到行动中。在宝藏岩,那位画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外面和气质完备没有那时候的大陆画家们的文艺范儿,可他正在带领一群年轻人,用音乐会、涂鸦、标语、网络、公开信等形式,为当地居民发声,同时也主见着他们自己作为驻村落艺术家的居住权。
宝藏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居民,是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兵。他坚持着没有迁居,也没有住到当地政府在宝藏岩为他们搭建的过渡房里去。
那天他就站在家门口——他那花了几十年韶光、一点点搭建起来的家的门口,跟我讲述他的来历、他的诉求。我现在都记不太清楚他详细说了些什么,只是记得他的脸,他的样子,他的屋子……当时就只想着要用相机拍下来(经他赞许,我还拍摄了他的客厅和厨房)。那一刻,我以前脑筋里的“台湾老兵”等抽象的历史观点,以及一堆数字,溘然变成了面前这一个活生生的老人。他的表情、声音、身体措辞,还有他家里的各种细节,带给我莫名的情绪冲击。
老兵和他的客厅厨房。作者摄于2007年1月。
可视的城市文明
关于宝藏岩聚落的形成历史和后来政府的整建过程,如今海内外网络上已有很多先容,大陆学者对这个项目的更新方案也有比较专业的剖析,这里不再赘笔。
就我而言,虽然在那以前已经调研过上海的棚户区,也参不雅观过国内外城市的一些形态不一的穷苦社区,但那天匆匆的宝藏岩之行,还是让我对“人类聚落”观点,多出了一点感触。在当代的城市社会,人的聚落并不会由于它的形成本身而天经地义地被确认,它的存在须要得到干系政府部门的方案和认可。否则,纵然里面的居住者是合法的国民、市民,纵然城市管理者暂时会容许它的涌现和存在,它依然可能是违规违法的,是随时可以被革除的。在台北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宝藏岩建筑群直到2011年,才由台北市“文化局”公告登录为该市的一个“聚落”,并进而被定义为一个公共的“文化资产”,其情由是“私邸小不雅观音山下宝藏岩聚落为战后台湾城市里,非正式营造过程所形成的聚落,是荣民、城乡移民与都邑原住民等社会弱势者,在都邑边缘山坡地上独立造屋的代表,有历史的特色”。
而在此之前,为了它不被拆除,社会各界已经作了30年的努力——除当地业主、租户的申说外,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师生团队也投入了相应的调研和建言,当然还有驻村落艺术家的长期抗争。而作为更大的背景,同期间的台湾社会本身也经历了历史性的迁移转变。
当地文化部门张贴的宝藏岩海报。作者摄于2007年1月。
就这样,经由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社会博弈、社会协商过程,那个原来被认为毫无存在代价、必须消逝的违建住宅群——有人将其形容为所在城市的“边际之岛”“化外之地”,在重新方案、整修后,保留了整体上的聚落形态,个中不愿迁居的部分居民也得以保留了他们的住房产权或租住权。宝藏岩聚落由此变身成本日作为台北市亮丽地标的“国际艺术村落”,它被授予了各种文化历史代价,并被冠上了“共生聚落”的新定义。
不难想象,本日的游客们,在参不雅观天下各地城市的历史聚落时,实在不仅是在不雅观赏建筑群及当地的文化遗存,同时也是在感想熏染城市文明的演化历史及内涵,当然也会由此而对当代文明的可能性产生各类遐想。
今日成为游客去处的宝藏岩。拍摄者王菱授权利用。
作者/陈映芳
编辑/西西
校正/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