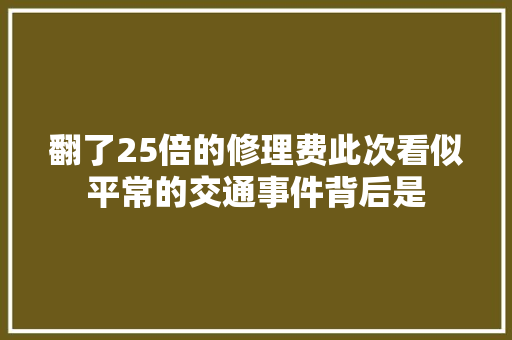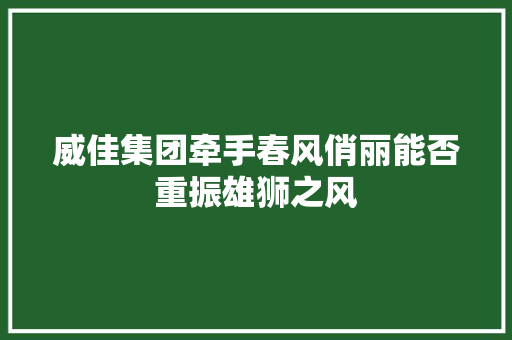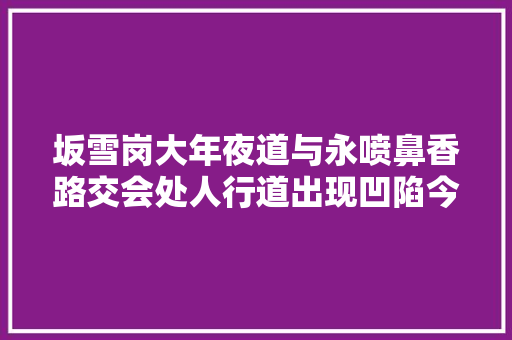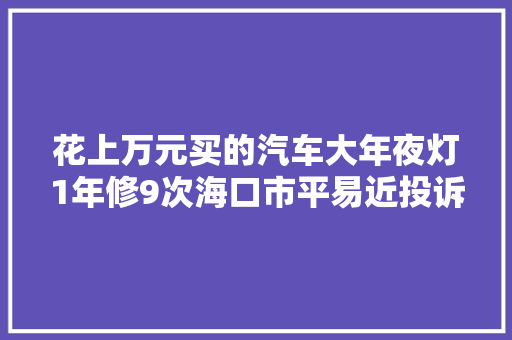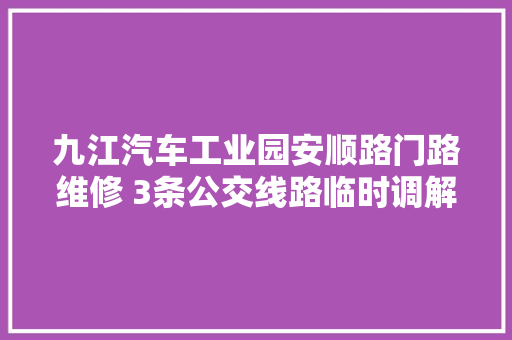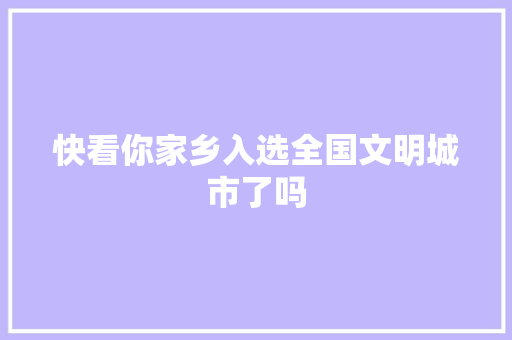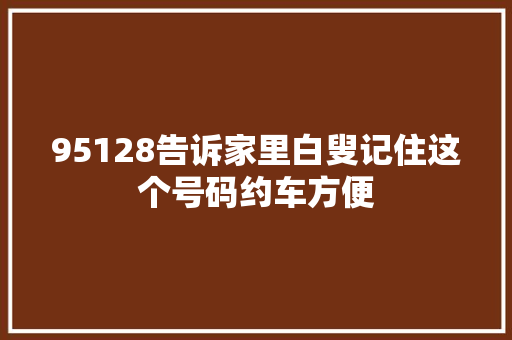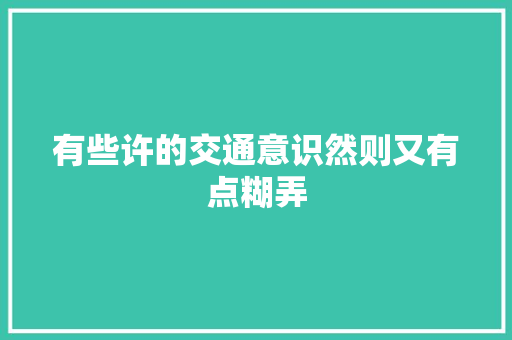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蠢掉队,谢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付汉文化,采纳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执拗地坚持旧习俗不变,乃至到了很晚的期间,才禁止同姓通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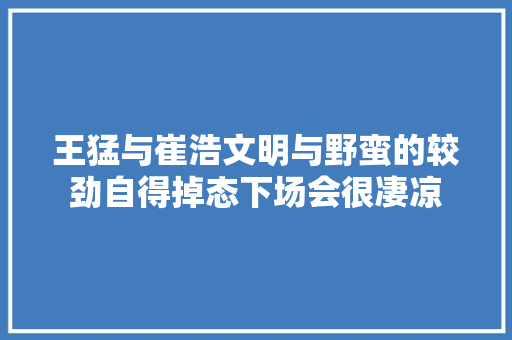
以是,越阔别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酷,一定要把表示文明精神的统统,视作烧杀劫掠毁坏毁灭的工具。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神往,和对野蛮的痛恨。
以是,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以是,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生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干事,而且担当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师动武,其本色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故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匆匆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役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相互残杀罢了。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互助。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zuo做出精彩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
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蛮夷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身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以为成了贵族。
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随着家学渊源,或登时书柜起来一样,都是一厢宁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抵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抵牾。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疆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付高等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以是,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乃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革,抱残守缺,恐怖文明。
历史上时时涌现的文明倒退,便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
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期间。撇开特定的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生理是分不开的。
因此,野蛮掉队而执拗守旧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降服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恐怖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上风文化之上,这便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涌现空缺的由来。
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该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征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便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王谢,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扫而空。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降服文明的苦果。
以是王猛崔浩等人跟少数民族天子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由于“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打仗,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因此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复苏的缘故原由。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难免不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胜,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百依百顺,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高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
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正,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
一贯到他病重的末了时候,“坚亲临省病,问往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生平,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付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付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寻思卿言也。’”信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拓跋焘】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往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身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真,太子晃登基,“旁边忌浩正派,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须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乃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利用的人,忘却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短长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常常要溢出来,这便是忘乎以是。
仔细剖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忘形,则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得意,是自我生理上的知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为得意,或别人管不着的暗中得意,与外界无碍。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张扬虚假,或无耻癫狂,影响到大家,就会遭到物议了。
如果崔浩复苏,那就赶紧收敛,还来得及。但他已经太忘形了,罔顾统统,就不可救药了。实在他提倡玄门,攻讦佛教,已惹众怒。他阻挡拓跋嗣南征刘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连昌部落,也使将领反感。他主见规复门阀制度,与鲜卑贵族分庭抗礼,经营官僚姻亲集团把持权力,都是很不得民气的。
这个陷入困境的崔浩,还自我觉得良好,在编撰北魏《国史》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将拓跋氏这个野蛮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秽行丑闻,恶风污俗,“务从实录,以彰直笔,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洋洋得意。且刻在大石碑上,立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来见者咸以为笑,北人无不忿恚,相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超出的界线。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由于一旦忘乎以是,而又不知节制,失落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要牢记的一点是:野蛮,固然是野蛮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时野蛮起来,乃至比食人生番还起劲。
崔浩被抓了起来,装进一个木笼里,比后来戴高帽游街示众还惨,押送城南,置于地坑。“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
文明落在野蛮的报复狂手里,那种费尽心血的折磨凌辱,便可想而知的胆怯残暴了。《魏书》的作者,出于一种文化人的同情,不禁叹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复苏,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抵牾激化,历史又会是其余一个样子了。
以是,有的人,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末了,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了局,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