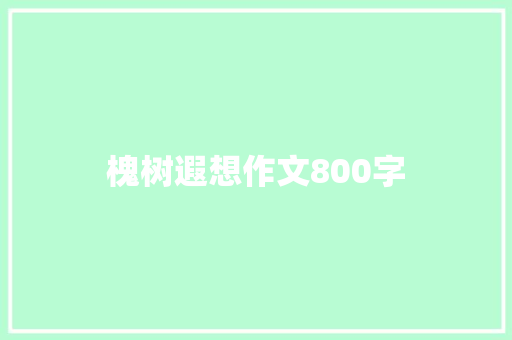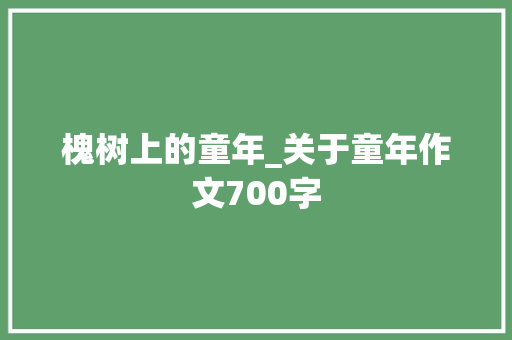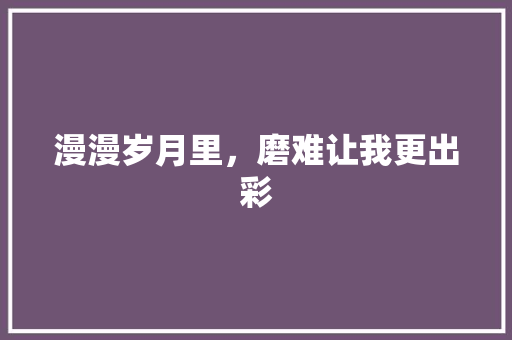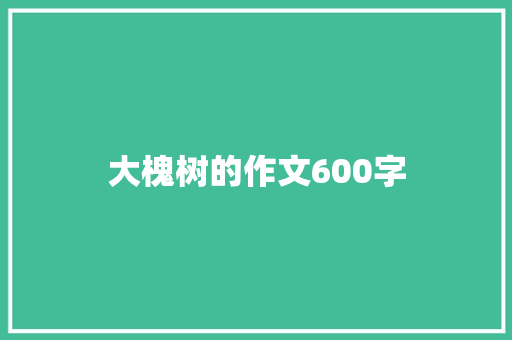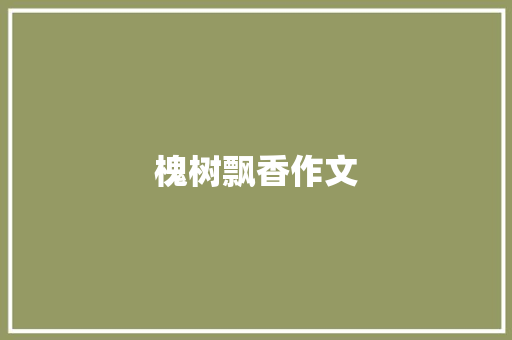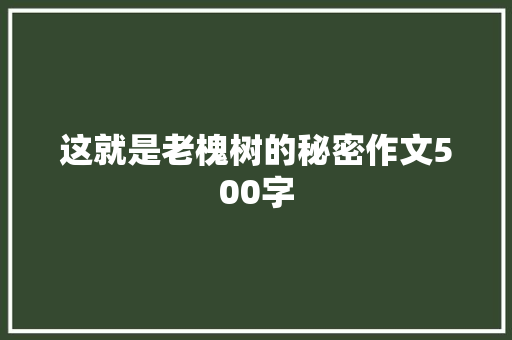我至今还能清楚的记得,一个老奶奶去我家门口大槐树下面的供销社,拿出五分钱说:给我称三分钱的盐,剩下的两分钱买烟。
这个烟是岗南牌子的,一整包20支一角六分钱,零卖便是一分钱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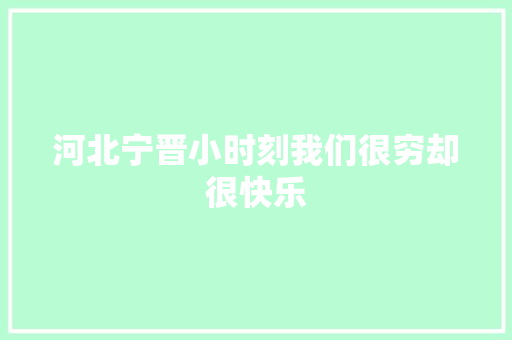
由于这个年代,是人们还没有办理基本温饱的年代,很多人家,一年也便是吃两次白面,一是麦收期间,而是过年的时候。
可是,在缺少物质的童年里,我们从来不短缺精神,虽然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和老咸菜,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但我们却是非常的愉快。
没有钱买玩具不要紧,广袤的大地上,随便捡几个小坷垃、烂砖头,然后在地上画上一个留个空或者八个空的方格,小伙伴儿们就开始“走地”,而且还“走”的废寝忘食,不亦乐乎……
有人用玉米换了黑枣,他们吃黑枣,我们就捡他们吐出来的黑枣核,在地上弄个乒乓球大小的小坑,离坑一米旁边画一条线,然后开始一人守桩,其它小朋友就拿出一个黑枣核放在线上,开始用手蹦,一边蹦黑枣核一边大声的念着:一蹦蹦,二吃鹰,三黑狗,进城柳……
这个童谣中的一二三,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但这个城柳,便是老家话:城里;
恰巧的是,我家门口那个康熙年间的大槐树下,属于当时大北村落的经济文化中央,无论是学校,卫生院、还是图书室、供销社,乃至往后的面粉厂、电影院,都在大槐树的周围,而供销社一个长得傻大呼玛黑的大哥哥,就叫三黑,因此每当我们高喊着“一蹦蹦,二吃鹰,三黑狗,进城柳”愉快快乐的蹦黑枣核的时候,三黑就黑着脸从供销社里喊道:走走走,起其它地方玩去……
那个年代,作为屯子交通工具的自行车,也是少的可怜。可是,我们依然高枕而卧,便是去四公里开外的外婆家,也便是那个叫做“轱辘儿”的铁环,再拿上自己用铁丝制作的推柄,愉快欢快的推着“轱辘儿”,一起小跑的就到了外婆家……
女孩子们也是一样,他们从家里拿一根绳子,几个人就开始念念有词的跳绳,从地上捡几个小砖头或者小石子,就开始“抓子”,一个玩的像的野小子一样的愉快……
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虽然穷却活得很快乐,现在的我们虽然不愁吃穿却活得很累?就像现在,有时候一顿饭便是几万元,却也没有了以前的味道;现在为了一点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大笑,大哭,却也很难像小时候一样尽情的猖獗;或许,小时候很大略希望就那么小,现在大了想要的越来越来越多,乃至都不知道要什么……
(作者:张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