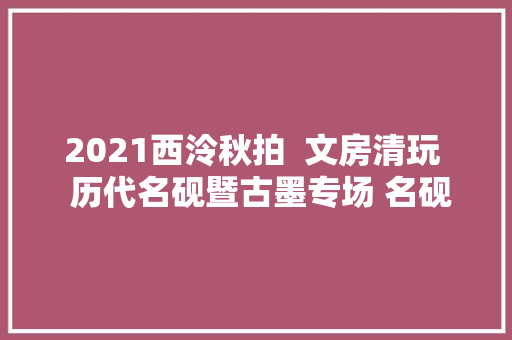中山三器自1970年代出土以来,以其历史文献代价之高、刻制铭篇之长、器物制作之精创下三个世间之最。三器上的铭文到底是铸上去的,还是刻上去的,一贯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经由多年研究并利用当代技能助阵,省博物院研究员郝建文师长西席得出了“铸铭”的见地,有关剖析请关注2021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战国中山三器铭文图像》。今摘编片段供中山文化爱好者们先睹为快。
大型历史记录片《中山国》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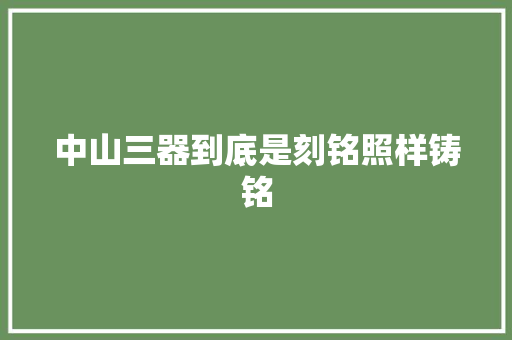
——中山三器上的铭文是刻上去的还是铸上去的?
刻铭还是铸铭
——战国中山三器铭文之不雅观察
(摘选)
郝建文
战国中山三器因其长篇铭文有主要的文献研究代价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代价,自出土之日起就倍受众人关注。四十余年来,人们大都认为那些笔墨是古人镌刻在青铜器上的。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中山国文化的普遍关注和更深入的理解,那些笔墨究竟是刻的还是铸的,自然也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我曾多次零间隔不雅观摩铭文。那些铭文高约2厘米,肉眼看上去,字形幽美、线条流畅。
但是,当把用微距镜头拍摄的铭文照片在电脑上放大10倍、20倍后就会创造,有的铭文某一笔画也并非一笔完成,有接笔和补笔,而且,笔画凹槽底部平缓调皮,看不到刀刻痕。从事铜雕和铸造的朋友见告我,没有凿刻痕不符合常理。铜水有紧缩性,只有铸造的铭文才会涌现这种征象。后来,我创造方壶器身下半部有的铭文有二次加工(补刻)痕迹。有的补刻笔画和铸造的笔画错位明显,且线条质量反差很大。
方壶的“子”“徻”等字,笔画被堵,添补物和器表一样平滑,可能曾一起进行过打磨。又如圆鼎的“否”字,正射光源下,可看到竖画高下是贯通的,而光源在侧面的情形下,“不”字的竖画中间被添补物隔断。我疑惑那些添补物是铸造残留物。故意思的是,铭文中的圆点底部平缓,似用圆头的“硬笔”点成,而非镌刻。在方壶铭文中,倒是有两个补刻的圆点,一个是沿着圆点的外轮廓刻线,其余一个则是在铸造涌现问题的圆点上刻了一个小坑。看来,古人并没有削铜如泥的“神器”。此外,圆壶铭文中的 “先”字,末了一笔有修正痕迹,似在模具上“书写”时涌现失落误,随手一抹,之后又重新书写;还有一些不是笔画的线条,似古人手中的“笔”欠妥心留下的划痕。彷佛也可以证明,这些铭文是在比较软的泥模或蜡模上刻的。从以上情形剖析判断,战国中山三器上的笔墨从整体上说是铸铭,只是对铸造涌现问题的个别铭文进行过补刻。
作者简介
郝建文,1967 年生于平山县,文博研究馆员,现任职于河北博物院陈设研究部。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博事情30 余年,书法师从张守中师长西席。出版《战国中山三器铭文》等。
郝建文在拍摄刻铭方壶
伐燕本是白狄人,
胡服骑射发豪情。
中山酒好万人醉,
金银错铜九门春。
炉火千日烧罍觗,
大鼎三器记英名。
邀来淄川饱学士,
篆书惊到座上宾。
——为郝建文师长西席解中山青铜器“铸铭”、“刻铭”新说作
诗 作 者:张志平
书法作者:檀砚龙,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平山县书法家协会主席。
专家点评
刻铭还是铸铭?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最宝贵的是笔墨。大河光石上有,陶器上有,成白刀币上也有,形式上有锲刻阴文、模铸阳文。最有代价确当属铜器铭文,个中又以“中山三器”为优。铭文有1101个字,不但详记了中山历代王的历史,歌颂祖宗功德,而且字形幽美,洒脱奇丽,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宝贝。省中山国研究会于2017年举办了“中山篆书法篆刻全国约请展”,共有海内外的300多位书法家、篆刻家参展,对继续弘扬中山国书法艺术产生了主要影响。长期以来,关于“中山三器”上的笔墨是“刻铭”,还是“铸铭”,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经由多年研究并利用当代技能助阵,省博物院研究员郝建文师长西席得出了“铸铭”的见地,有关剖析请关注2021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战国中山三器铭文图像》。
作者简介
张志平,河北省文史馆馆员,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会长,平山县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历史文献记录片《平山影象》《中山国》《滹沱影象》及大型历史文化地理调查工程《平山村落落考》总策划、总撰稿。有研究平山、西柏坡的专著十余部,300万字
(本文来源:亚洲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