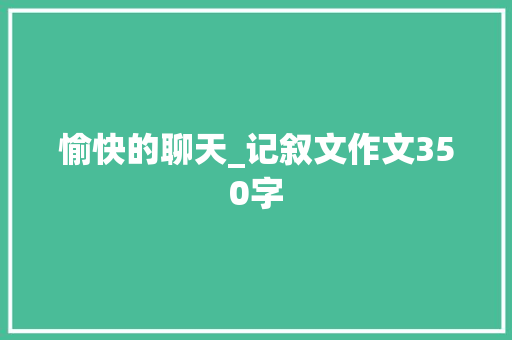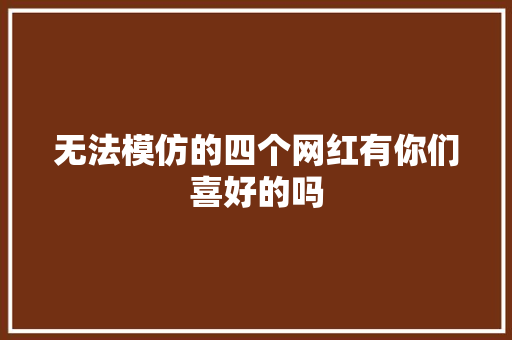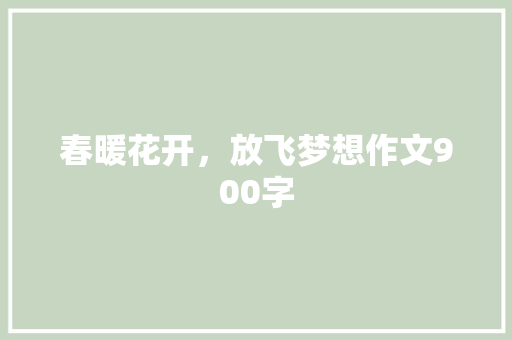听歌人或许总被旋律击中,即便歌词烂俗又意义不明,也总能隐没在旋律后面被体谅。在民谣中我们听了太多南方、北方、成都、兰州,也听了太多和姑娘的恩恩怨怨,当唐映枫的“雨后有车驶来,光阴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遇上民谣如日中天时的末班车进入大众视野,当代诗一样洗练的笔墨准确地描述场景,又随着旋律蒙太奇一样平常切换流动,这对付习气了含混浅白的民谣歌词的听众来说实在太精细和故意蕴了。
《空想三旬》所在的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是唐映枫制作的第一张专辑,个中许多歌曲都是雾蒙蒙的,《途中》写:“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你要去的地方,四野小雨春芒”《浓烟下》写:“秋后的浓烟引燃起诗意的哑弹/而舆论的道友他们以孤独执笔”,合营着陈鸿宇低沉的嗓音,整部专辑都弥散着一种颓然的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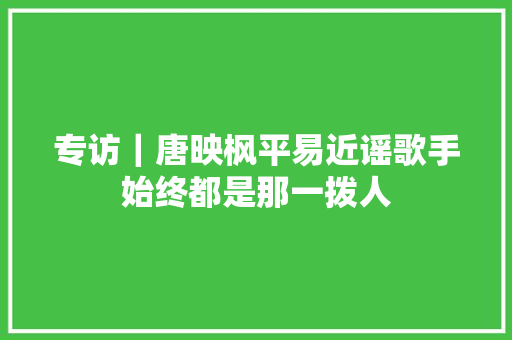
而这种意境的由来不过是唐映枫写专辑的四、五月份时,是老家烧桔梗的时令,田地里到处都是浓烟,“诗歌电台”这个名字则是唐映枫以为现在的电台里播放广告的很多,而溘然窜出来一个诗歌电台就很不合时宜。“我喜好这种浓烟的画面和这种不合时宜的内容”,而这种可能只是印象中很浅的一个印记,唐映枫就可以用整张专辑来演绎出个中的氛围和故事。
成立于2014年的枯鱼肆音乐工作室,几年间不紧不慢地制作新歌,唐映枫说“我要的比一样平常的词作者更多”,因此他更喜好策划、制作整张专辑这种形式,当被问起是否会主导一张专辑的风格时,由于寡言而总显得有些怯怯的温吞的唐映枫溘然武断地说:“他们都听我的。”是的,在知乎上、在百度的原创歌词吧里,唐映枫还有一个名字叫唐魔。
唐映枫
在1991年出生的唐映枫身上可以看到的年轻世代的词人的那种自傲和游刃有余,而不须要任何措辞上的自我附丽或者行为上的出奇怪异,唐映枫本人安静又很给人间隔感,但是谈起写词却非常诚恳,而除了写词,他自己的经历也非常有趣。
最近出版的《六日改》一书是唐映枫对从2013年到2019年险些所有作品的总结,书中收录了《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鱼干铺里》、《一如年少样子容貌》、《硬骨见鹿集》、《鸟的世相》、《无法清分的事物》、《三旬》等专辑词作与作者近年创作的随笔、杂文等。是对他创作进程的完全回顾。
值其新书出版,澎湃新闻专访了唐映枫,我们聊到他的个人经历、他的经历如何被“化用”到歌词中,他对民谣的意见等等。
《六日改》
“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赛过爱贫穷和思考”
大多数90后一代的发展由于高度相似常乏善可陈,大家或许有短暂的村落庄履历,但很快去向样貌相似的大城市,读相似的初中、高中,留在故乡或考到一个更大的城市,再去应聘一份稳定的事情。《在路上》的一位译者说:不要认为后来世代的人就一定高明,他们很难想象在80年代时我们曾若何逐日怀着弘大的自傲和对未来的任务去创造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在90年代往后,这种由青年人牵头、社会中洋溢的自傲很快消散了,一个稳定社会所建立的代价标准攫住大多数的年轻人,而唐映枫是例外。
唐映枫镜头下的故乡
从他的经历来看,唐映枫迄今人生中的一小半韶光都跟音乐不怎么沾边儿,他童年在四川德阳的城郊的楠木院中度过,乡里连一台座机电话也没有,神游发呆霸占了唐映枫童年大部分的光景。“我小时候是一个很乖巧、学习也挺好的孩子”采访中,唐映枫一边捏着咖啡的吸管一边回忆,“但是,我月朔就辍学了,开始无所事事地在社会上游荡。”
故乡
“之前一贯在一个秩序中,但溘然有一天跟同龄人完备脱节,这个觉得很奇怪也很没有安全感。我混沌了险些一年,期间在酒吧当过做事员,朋友来了我就跟他们玩儿没再好好事情了;我还跟朋友去成都开过早餐店,但他们四点得起床,我起不来,被骂了一周往后也就结束了。后来有一天,我爸说朋友刚好在一家搞机器加工的业务的公司,你要不跟他们去跑业务吧,我就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只做了一天。”唐映枫说。
去那个加工公司是2008年,“我当时去的第一天老板给我一张图纸,我正在看图纸就听到表面咚咚咚响,觉得楼底下有人在用锤子砸地板。当时同屋的财务老大姐反应快,说是地震,我们就往外走,我看到楼上的天花板掉漆了,我就开始有点焦急了,从走变成快走。到表面才看到各种屋子都在摆。之后,我就又失落业了。”
故乡
后来的几年唐映枫在一所专科学校读了康复专业,已经开始操持就业、结婚、贷款买房,准备按部就班地步入中年。直到传说中是天下末日前夕的2012年11月,“我之前在5sing上互助过的一位音乐人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签约唱片公司去到了北京,邀我过去一起互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且寄来了条约。……我当时没有犹豫,由于对方说包来回机票,我没有坐过飞机,以是就答应了。”唐映枫在《六日改》中写道。
到2014年,唐映枫有了自己的录音棚,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位音乐人在征集歌词,唐映枫点开这位音乐人之前唯一的作品,创造他的音色憨实,就用不到半个小时的韶光写了一部分歌词投稿,很快这首歌词被征用,这首歌便是后来让陈鸿宇和唐映枫火起来的《空想三旬》。对付唐映枫来说,这个成名作有一点草率:二十分钟写好主歌(歌词),在女朋友喂鸽子的间隙填了一部分副歌和歌名,而无论如何,正是这首歌给的鼓励,唐映枫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接下来的几年,唐映枫成立了枯鱼肆音乐工作室,与易烊千玺、伏仪、刘昊霖和陈鸿宇等人互助,不急不缓地往前走。
我们可以预测在村落庄的童年,在社会上游荡的少年以及近八年的北漂生涯能够留给一个创作者什么:或许是如“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玩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又纳鞋坐院坝”的像是脱口而出的流畅丰富的素材;可能是“线上盲从的意见意义将投契变现/朝城乡投掷情怀的骨头”的深奥深厚思考;也可能是“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赛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迟夏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的自我和敏感。
歌词的游戏
“我正式写词便是在月朔”,但唐映枫将自己最开始写词称为笔墨游戏:“音乐和MV里面已经呈现了一个画面,我就考试测验抹掉这个画面,用我自己的词去还原他的场景,比如《以父之名》原词的构架是《教父》那部电影,我知道那些黑帮都是穿洋装、戴墨镜、有乌鸦,我就用我的笔墨去描述他们怎么戴墨镜之类的,就很中二。我脑筋里会涌现一段旋律,整篇词都是根据我脑筋里的极简和弦不断重复写出来的,那个旋律在我心里实在也很模糊,词险些是卡不进去的,而且从现在看,根本就没法唱。但当时以为很愉快,那时去模拟歌词,实在便是模拟构造和逻辑。”
唐映枫当时写的词都是压尾韵,但是转得很生硬,并不符合歌词的标准:“举个大略的例子,盛行歌的作曲基本是三段式:主歌、桥段和副歌,最套路的盛行歌写法:第一段5到8个字,第二段3到6个字,然后第三段和第四段再重复第一、二段,主歌部分就完了。桥段同理,只是字数的是非问题。副歌也是这样,一样平常是四段,这是基本的歌词格式的逻辑。但是我当时是没有这个意识的,那些起伏和平仄,开口韵、闭口韵这样的我根本不懂,比如歌曲的旋律往上走的时候最好选择开口韵,往下时选择闭口韵会让音色发挥的余地更多。”
后来打开唐映枫词思路的是那个时期的港乐,“但是我当时又跑偏了,粤语本身是九声六调,我搞不明白,我自己写的时候我又不自觉想用粤语里的词,就搞得国语不国语、粤语不粤语的。但是,那时候我开始考试测验自己去探求题材写,不是跟随着谁。”唐映枫说。
现在唐映枫能够考试测验各种风格,他利用的最多的还是诗化的自由韵,“自由韵看上去随意马虎,实则不然,由于它哀求整体语感有当代诗一样平常的内在韵律作支撑,否则会显得干瘪无味。我个人方向在平实舒缓的旋律中利用自由韵去填写,让歌曲在表达上更靠近口语,去技巧化地娓娓道来,朴素的修辞也会让人声和情绪更为突出。例如《不再让你孤单》写道:我从迢遥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好看你胡乱说话的样子容貌/逗我笑……整段没有重韵,但入曲没有丝毫牵强。”唐映枫在《六日改》中写道。
2018年,唐映枫推出了个人专辑《鸟的世相》,除作词之外,作曲和演唱也是他自己亲力亲为。
在以下的对话中,我们仍旧从他的词的创作开始聊起。
《鸟的世相》
[对话唐映枫]
澎湃新闻:你自己也做了一张专辑《鸟的世相》,可以谈谈吗?
唐映枫:我当时就想试试作曲,以是我自己这张专辑里七首歌的发布顺序实在便是我刚开始作曲的全体顺序。《我纷扬的世间》是我人生中写的第一首曲,《关于风起时》是第二首曲。我想要差异于之前互助过的音乐人的既定印象,你会创造一个人去给别人画人像很大略,但是你画自画像就会特殊难画,特殊是你已经把你很多表述放在了别的地方,你自己能用的地方实在已经不太多了。
《鸟的世相》在制作的时候就不期望它有盛行度,你会创造所有的盛行歌它们常日是第一人称或者第二人称的,在旋律悦耳的条件下,用你或者我这样去讲故事,但是全体《鸟的世相》我实在定的视角都是第三人称,它的英文叫Look Down,这整张专辑的视角都站得很远,然后去描述,这整张专辑都是,会给人一些代入困难。
澎湃新闻:你的其余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叫《儿时》,可以聊聊这些灵感的来源吗?
唐映枫:我写《儿时》是由于90后这代人想听童年还是要回到罗大佑、高晓松,但是他们的词写的也不是我的童年,我就想写一首跟我们这代的童年有联系的歌。《儿时》的歌词非常工致,我的整篇歌词都是按照四个小节写的。《儿时》就写了一个晚上,一点到五点大概。
当时创作完这首就发给刘欢老师听,刘欢老师也很热心,发了很长的语音,说这个歌挺好,但是也有问题,主歌和副歌之间短缺变革,承接不住,我听完汪峰老师在舞台上唱,创造的确有这个问题,作为舞台演绎的话,歌词的信息密度太大,一贯在跳转而不是情绪叙事,的确不那么适宜舞台化或是盛行化的呈现。
澎湃新闻:你的词很多都是阐述性的,比较平缓舒张,没有那么刻意的韵脚,这样是否会对曲的哀求比较高,而且也间接失落去了那种韵脚密集的歌词的澎湃和节奏感。
唐映枫:我并不是特意这么做的,我的一首词里的问题都会想办法在另一首词里办理。比如《骑自行车的人》这首歌也是写童年,但是我只写了一件事,便是读幼儿园的时候我爸爸接我放学,这就很适宜舞台化,有叙事有起伏,但是它实在便是童年中的一个小点。
叙事是得当舞台的,比如刘昊霖的《北区楼四》,“北区楼四”便是我身份证上的地址,写的是家门口的所见所闻。它的密度也很大,但是通过纯叙事的讲述去表达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儿时》的问题不是叙事,而是给画面但须要较长的韶光去想象那个画面,这就不太适宜舞台化的演绎,盛行化比较困难是由于很多时候我只给了意象,我不参与叙事、不抒怀、不说话。
澎湃新闻:比如《途中》《浓烟下》这样的意蕴比较深,意象大概多的,要怎么构造成一首完全的歌词。
唐映枫:通感吧,由于我会把一首词想象成一个画面,跟方文山不一样,方文山是做蒙太奇,但是我只想一个画面。我是想这个画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觉得,那个画面是一个艺术拍照还是纪实拍照,是一个工笔画还是简笔画,还是一幅油画、还是一幅国画。脑筋里首先会有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去想这个画里面会有什么。你不能去写一个在这幅画里不能涌现的东西。一幅古典油画画了个冰箱也可以,但是全体语境就不一样。
澎湃新闻:可以谈谈一首词是怎么有了灵感,逐渐被添补成形的吗?
唐映枫:我特殊喜好听那种空间特殊大的作品,我到后来基本不会听有词的音乐,就听纯音乐去了,或者听电影配乐,听古典,就听这些东西。由于我须要的是那个空间,但是你作为一个词作者的话我就在想怎么能让歌词不要去打扰到音乐。我以为像盛行音乐,我的这个打扰的意思不是在评价一个歌词的好坏,打扰的意思是他完备把它变成了另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像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首歌,写得很好,但是那个旋律本身出来的话你是不会想到什么《好久不见》的,歌词加入之后,一个主题确定了下来,就变成了一首非常好的盛行歌。
以是我再去写词的时候,我的全体思路便是只管即便地去淡化歌词的主题性子,去呈现一些零零散散的画面,想着不要打扰音乐。但这样子的时候会涌现一个问题,便是习气于听表述的人会以为听到末了你居然啥都没说。比如说像几个意象,那我现在可能看到的便是咖啡杯、吸管、书、窗户、表面白色的烟尘。那你可能就做一个排列由近到远把它写上去,这个场景是不可能再复刻的,所有的感情都在这样的场景里,那有些人可能就会以为不理解你要说什么。
写词:在每个人身上放不同的东西
澎湃新闻:提及写词,你若何评价之前最有名的几位词人,比如方文山、罗大佑等?
唐映枫:方文山是一个特殊有灵气的词作者,基本可以说首创了一种写词方法。这实在跟周杰伦的作曲构造、本人的咬字发音之类的有很大的联系,周杰伦的“口齿不清”的特点使得中文全体的咬字的颗粒感变成了像英文一样的韵律化的东西,以是这个时候给方文山去入词、合辙的时候,空间就变得更多了。他们后期全体编曲的思路和风格给方文山补充了很多东西,这非常主要。以是我说方文山很有灵气,没有人这么做过,他是用电影分镜式的写法,蒙太奇的办法来写词。
方文山之前的话,比较有参考性的便是罗大佑还有李宗盛,李宗盛本人对付词曲的拿捏就有点像是“强制症”的状态,他非常讲究合辙——“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久不凋零的花”,再配上它的旋律,像是说着一样就唱出来了。罗大佑又不太一样,他有点像在给早期民谣运动后的台湾盛行歌定下一个高度和规范,三位在歌词创作领域在我看来都是首创性的。
澎湃新闻:方文山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写“中国风”的词,但现在的“中国风”或者“古风”歌曲又有一点俗气化的方向,比如一味堆砌词华。
唐映枫:我自己对所谓的“中国风”“古风”打仗得很少,作为一种亚盛行文化,它离我太远了。但所有的音乐类型里,喜好的人多了,创作者多了,就一定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这是很正常的事。这不是“中国风”的问题。
澎湃新闻:你谈到方文山的词能被关注和周杰伦的作曲有很多的关系,两个人是相互造诣。你和你的歌手,比如陈鸿宇,有这种相互绑定的关系吗?
唐映枫:我以为没有。旋律给到我的只是一个写作空间,什么样的音色和个人特质适宜去诠释什么内容,这是写词本身就须要去考量的事情。鸿宇没有我,也可能会以别的面孔出来,现在的结果不是一定的。
《空想三旬》
澎湃新闻:你紧张互助的几位音乐人陈鸿宇、刘昊霖、伏仪等,可以先容一下跟他们各自的音乐的特点以及互助的形式吗?
唐映枫:形式实在都差不多。便是他们先出旋律,我听了往后决定根据哪个旋律填词。我会去想全体旋律的空间,他们初期给的旋律每每都是很大略的,但是也不主要,我只要抓到全体旋律的一个部分就可以了。比如听前奏我就听两个东西:一是前奏的全体框架,也便是它的字数能给我发挥的空间;二是听它的动机。像《途中》的主歌对我来说实在不主要,我要的是他副歌部分的动机,前面的字数只是确定我怎么写它。
跟刘昊霖互助就比较方便,我会跟他说我要一首这样子的歌,他就会给我写出来一首这样的,我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填词。由于刘昊霖非常会作曲。伏仪也是,他可能不像刘昊霖作曲那么灵巧,他的所有东西都偏朴素和日系的,这也是我当时乐意和他互助的缘故原由。由于你会创造,不管是陈鸿宇、刘昊霖还是伏仪,虽然大框架都是盛行的,但是音乐的动机都不太一样。我就可以在每个人身上放不同的东西。
所谓的动机实在和作曲的逻辑有关。我要写一首歌,我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根据一段旋律做向上的延展或是向下的延展,然后把它完全成一首歌的段落。这跟配器也有关系。陈鸿宇和伏仪便是用吉他,吉他是和声乐器,基本上作曲思路就相对自由一点。刘昊霖吉他和键盘都用,用键盘和用吉他作曲的风格非常不一样,以是我看重的还是个人特质吧。
澎湃新闻:你和歌手们互助基本上都因此“专辑”为单位,你也谈到“我要的比一样平常的词作者更多”,一样平常大众不太会给词的作者太多的关注,但是你的非常光鲜的个人风格彷佛都旁边了全体专辑的呈现。这也表现在很多歌中直接用了念白的形式,很突出词,比如《浓烟下》。
唐映枫:由于我对全体音乐制作的观点是从李宗盛那一辈人那里学来的,这是传统制作人的思路,一张专辑能让音乐立住的话,企划很主要,它不能是零散的东西,而该当是完全的一个观点。我不太会和演唱者去沟通,他们有时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样的互助须要足够的信赖。像是陈鸿宇第一张专辑全体的听感,吉他编曲给到了很主要的部分。第一张专辑的《途中》、《早春的树》到《来信》,我更喜好从编曲的思路上参与创作。比如《早春的树》,一开始编曲老师给的是一段指弹旋律的前奏,我说不要给我这个,只要给我几个有影象点的根音,便是极简和弦就可以了。
像《浓烟下》的念白便是最开始写的时候就不知道有什么可用的旋律,我说搞个偏实验性的,念念吧。这个也没办法作曲,它不是歌词的构造。
澎湃新闻:之前的访谈中,你和陈鸿宇都说《空想三旬》实在是一看就有“火”的气质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讲?以是这首歌和陈鸿宇的走红都有有时性吗?
唐映枫:有时性中也带有一定性吧。有时性便是我们全体的互助都非常有时,一定便是这首歌包含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会买账的东西。
我现在越来越不爱去聊这些内容了,很多时候你会创造那是你和你的听众在相互搪突,他在搪突你,你也在搪突他,这不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不要去冲破一些没必要冲破的东西。
“触不到的民谣”
澎湃新闻:你怎么认为现在的民谣领域的生态是若何的,包括民谣歌手和他们的创作?
唐映枫:民谣歌手在我的脑筋里始终都是那一拨人,现在互联网上的这一些,我个人不太把它往我认知的新民谣里面放。全体的民谣生态,是随着大家认识的提升,逐步就比较边缘。民谣我最初关注的那个时期,民谣实在就约即是是站在音乐圈鄙视链顶端睥睨众生的一个音乐类型,还有一些文学性非常强,根源性的东西。你再往上追溯你还可以去听到像胡德夫、像贵州那一片非常非常多的民谣,这些民谣一贯都在那,但没有什么变革,表面的听众触不到也不须要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触不到是说?
唐映枫:便是全体听感上或者认知上就直接忽略掉这些了。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民谣的创作就会沿着《董小姐》、《南山南》这个路数走。
唐映枫:对,我以为也挺好,和刚才的“中国风”谈论一样,参与进来的人多了,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会出来,被更多人听到总不是坏事,你只有听到了,才有选择,才有良好劣汰的可能。
澎湃新闻:杨波的一篇名为《李健们的背后是一群僵尸文青》的文章中写到的“一人一首代表作”民谣歌手们以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接下来的便是沉寂或者消沉,这可以理解为网络的快速迭代造成的每个人都只能在大众面前短暂勾留一小会儿,而也可以是由于创作者本身的后劲不敷,你若何看待呢?
唐映枫:一个是创作力的问题,它不可持续,或者过于短暂。另一个我以为和受众也有关系,便是新鲜感。现在全体音乐的制作门槛变得很低,出来的人就非常多,但是大众是不断须要新鲜感的,哪怕他们对付音乐的需求整体没有变,但是我便是要换个人去听。实在实质还是一样的东西。你没有给到足够好的内容,也不能怪听众走马不雅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