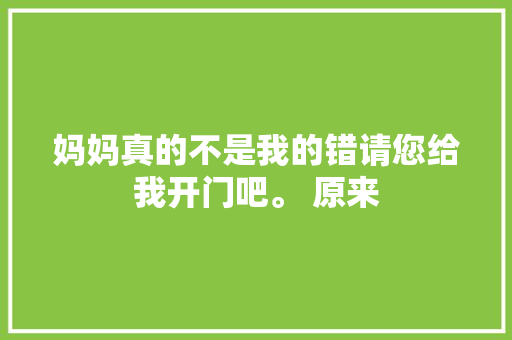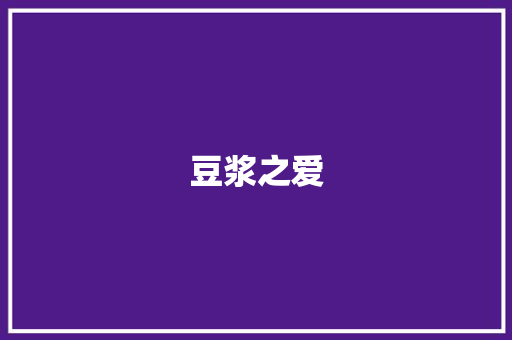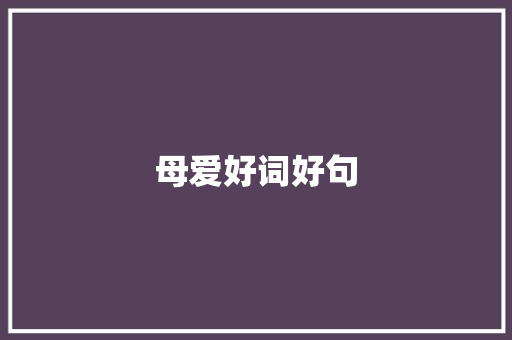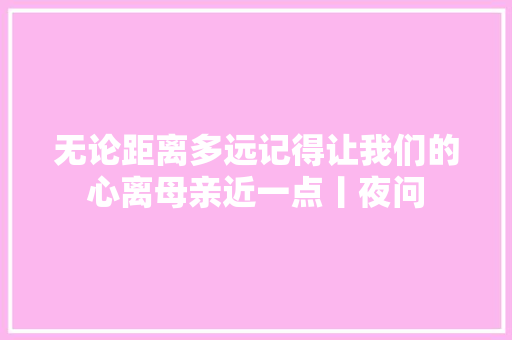自打有影象开始,我们一家人就住在一所老旧的庭院里,直到十几年后,父亲由于事情缘故原由,我们才搬离了,以是,那便是我影象中的家了。
影象中的家是一个带有门楼和院墙以及两间花岗岩砌成的瓦房拼凑起来的小院落,听父亲讲,那是祖父成家时置办的,传到父亲时已经由去了五六十年。两间瓦房是坐北朝南的,分别是正屋和偏厅,正屋带有厨房,田舍的厨房里砌着烧柴火的灶台,我的床离灶台只有一墙之隔。童年里,冬日的清晨非常寒冷,母亲一早就在灶前燃火烹煮。田舍的晚稻喷鼻香米在灶火的炙烤下粒粒受热,滚烫的米汤在锅中翻滚,加倍浓稠,喷鼻香气扑鼻。这让原来寒冷的冬日变得十分温暖。偏厅放有一张方桌,是一家人用餐的地方,你大概没有见过谁家的餐厅的墙壁上用粉笔写满了数学公式和古诗词吧?那里也是父亲的家庭讲台,他是一家人里最晚用餐的一个,每天晚上从地里劳作回来,早已怠倦不堪且年夜肠告小肠的他却不得不间断性的用饭,孩子们早已将他围成一团问这问那,什么奥数,解方程、历史典故、歇后语等,他总能不厌其烦,逐一解答。对他来讲,孩子便是希望,为了让家族喷鼻香火传承,他毅然放弃了原来海南省农垦局营级单位文书的事情,和母亲回家务农,硬生生把十个孩子拉扯终年夜。当然,代价也是残酷的,那便是半辈子的平庸和潦倒穷困。我曾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写的“困惑歌”——穷苦像无影的幽灵总是盘踞我家,掉队似无声的咒语始终环抱脑际,生活是如此尴尬,日子是这般困惑。希望登上那小康的石阶,祝愿乃是自我安慰,咬牙坚持是唯一的出路,黑夜的尽头总有黎明和曙光。瓦房前是一个天井和一堵院墙,院墙大概两米四旁边,八岁时,我站在一米高的书桌上,踮起脚尖,可触摸到院墙上的盆栽。门楼向东,约三四米高,上有前后屋檐,没有大户人家宅院里的雕梁画栋,墙体是散石砌成的,门楼上铺盖着大略的灰色陶瓦,门框由四根方形石柱直立横放而成,大门是两块厚重的杉木板,听说,那是祖父在二十几公里外的两英镇翻山越岭用扁担挑回来的。跨过门楼则来到天井,在我六岁那年,天井的院墙边上打了一口十来米深的水井,听大哥说打井时放置了二十几个井圈,每个井圈有半米高。在此之前,一家十几口人和圈养的几头猪的生活用水都靠母亲一人从一百多米外的公井挑回来,由于打这口水井,母亲持续高兴了好几个月。可不嘛?装满三个大水缸和两个水桶要来回十几次,可这也只是母亲一天事情里的一小部份而已,但在我的影象里,却没有听过她一句埋怨。母亲对生活的那份乐不雅观和坚持至今还传染着我,每当我碰着困难时,她当年挑水的画面就会在我脑海里回放,给我鼓励和提高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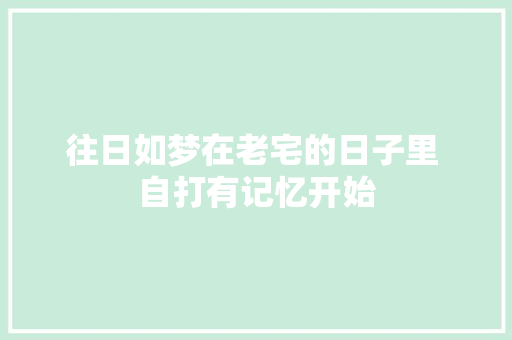
许多年过去了,我家早已搬进了楼房,然而,兄弟姐妹们嬉戏打闹、母亲灶旁烹煮以及父亲灯下授课的画面,时时在我心头浮现,永久不能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