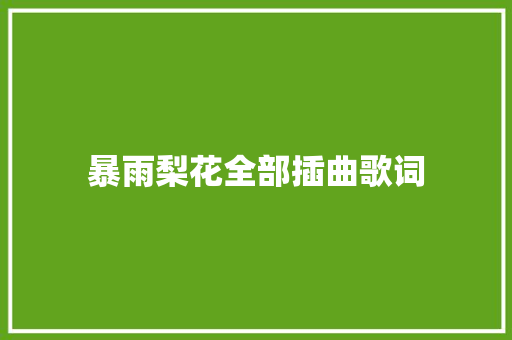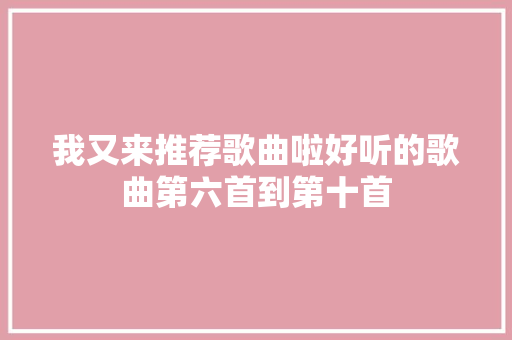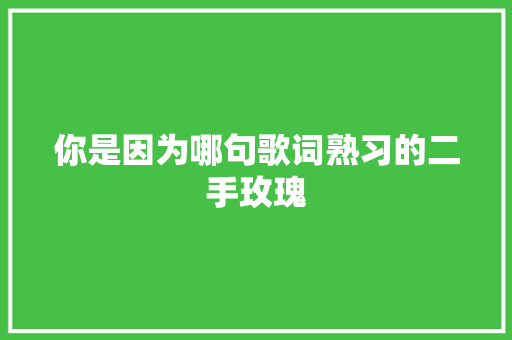西方的摇滚乐千姿百态,咱们这边儿园地宽阔,也该寻些新的种子来个百花乱放了,于是,奇葩二手玫瑰开了。我最早听到这个名字,就一愣:玩低调是吧,二手车也有好开的,二手的婚姻也有实惠的;或是,二手便是一手都不留,都亮这儿了;玩二手美人计是吧,玫瑰扎人。
乐队主唱梁龙以妖妇妆扮登台,嗓子却是爷们,这是一种反差,颠覆了男性旦角女声的传统,先让不雅观众面前一亮。不玩梅派,不装女神,要干嘛呢。不是不可以哗众,要看你取什么。噢,二手玫瑰要替大众说话。社会转型了,时期丰富了,一部分人变革了,一部分人迷惑了,既有“一群猪飞上了天”,也有“一群海盗淹去世在沙滩”。梁龙在不雅观众正琢磨他的媚眼和腰肢时,已发出对现实的思考与揶揄。

这是摇滚么吗?但这也不纯是二人转呀。这种二者杂糅的音乐主格,刷新了听众的耳膜记录,把折腾化在调皮中,把重音放在斜坡上。“枪炮玫瑰”太硬了,咱弄的是二手玫瑰;前者令人审美疲倦,而后者把玫瑰绽态已经换了姿式,它不喷鼻香你而是扎你;二手玫瑰这名字实在隐去了一个字,但真叫成“二手玫瑰刺”便嫌直白了。
音乐新鲜,耳朵就会喜悦,都是先听调调再听词。我以为,二手玫瑰在创作伊始,也是先犹豫而下了孤注的狠心的。二人转生在白山黑水,受众上亿人,咱东北的老百姓(603883,股吧)习气它就像美国南方黑人习气布鲁斯一样。一方音乐水土也养一方人,但作为哈尔滨出身的梁龙也不能惯着乡亲,咱得把天下的劲揉进去,把二人转摇滚起来。
反过来说,创作先锋音乐,梁龙熟习潮流的特色与技能,这是他的本钱,而东北的民间音乐却是一份大家可取用的公共资金。不用白不用,他用的巧,把东北大媳妇配给时期的革命者,生出一个新品种——虽然有人说是怪胎。它已经上路了,“火车往哪里开呀”,先开着呗。
从世纪之交,梁龙和苏永生草创的二手玫瑰乐队,到现在已有多少专辑和浩瀚名誉,也有多次国外演出的热烈场面。民族化、东方化,让洋人们领略到酸菜和大酱的摇滚,虽然有人说他们“用变态的服装、低俗的腔调,以东方病态媚谄外国人,就像画界的××君和××君展现的都是丑陋俗艳的中国人”。但我个人以为:艺术有启示精神的任务,也有反射生活的责任。
丑陋便是丑陋,不必故意示人,也不必藏着掖着;人性中的愚蠢或者俗艳大多时都是真实的靠近实质的,若要问罪也得指向其背景。“我是一只贪婪的耗子/我被富人收养起来”,以是,二手玫瑰的不少歌是从小丑嘴里吐出了批驳,是求乞子的脏手打向假正经脸上的耳光。
有人说有一种艺术形式的一个特点是通过挥霍自己来挥霍天下,二手玫瑰并不是这么大略。看起来它“娱乐江湖”,实则把悲哀化成了笑脸,让人想起里昂卡瓦洛丑角的《穿上戏装》;贬损了自己,指向的却是自已的氛围,比如“我就嫁了那条狗呀”。社会对人的影响,金钱对灵魂的堕落以及人在各种规则下的无奈,二手玫瑰都有谈笑般的表露。
梁龙,栋梁的梁,腾龙的龙,但他不玩顶天立地,而是采纳一种半风趣半媚俗的姿态,表现出批驳现实的力量。让人先乐后思,或是让人在哭笑不得中理解天下的荒诞。“我被活活逼成了贩子,我被活活逼成了墨客”。是生活选择你,还是你选择生活,抑或双向选择,这大概是个哲学问题,梁龙的思考中有这般探索。
我一贯以为,精良的相声都有半个哲学大脑,同理,好的歌词也应有形而上的指向。笑剧大师卓别林就说自己是个严明的人。梁龙的严明可能藏得很深,日常中也擅于捕捉玩笑,骨子里也有狂欢情结。他们的演唱一开始,节日气氛迎面,彩装花灯,唢呐锣鼓。
谁的心里没苦呀,谁没有过晦气呀,有人把苦、把压抑当成炸弹扔出来,二手玫瑰却把憋屈变成段子甩出来。我们不能一味地批驳阿Q精神,没有它,多少人会憋出病来。我去过二人转或俚曲场所,也听过不高雅的相声,当我看到台下面孔沧桑的工农发出忘我的笑声时我总是挺冲动。
有人说二手玫瑰谄媚大众。我是个墨客,我还想谄媚大众呢,我还想拍老百姓的马屁呢,可惜我没那样的本事。实在梁龙是狡猾的,起调是让人们喜闻乐见,展开和深入的是对摇滚乐的推进、对当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思考。我不太懂音乐技能,但也听了很多当代中国的民间乐队,我以为二手玫瑰的作品不只展示了新思路,而且流畅地贯彻了,万一它要深刻呢,就算老天爷饶上的。
梁龙是个喜兴的人,也擅喝啤酒。听说,一次他和大家议起伍德科克摇滚节,应搞一个中国化的、啤酒化的,说那就包一个拍浮池全部灌上啤酒,不雅观众们边游边喝边看摇滚演出……他乃至打算了一个两千多平方米的泳池需多少吨啤酒。
他说,中国人活得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