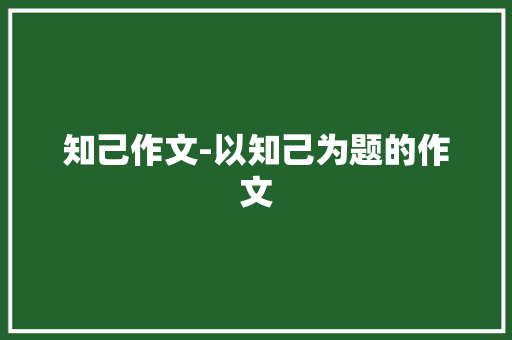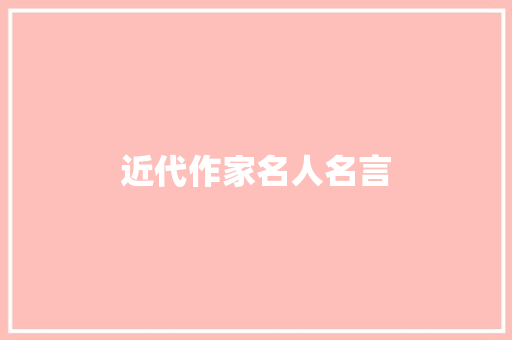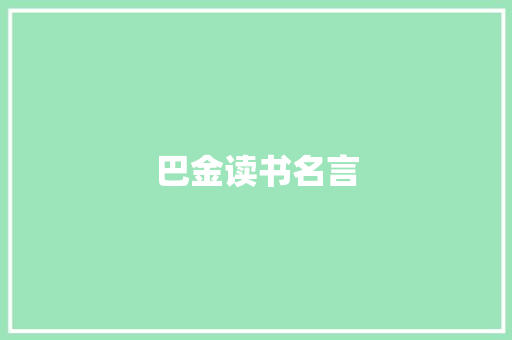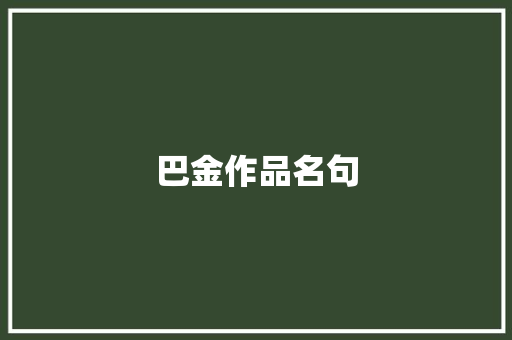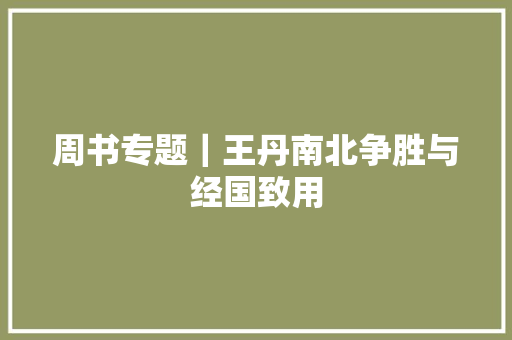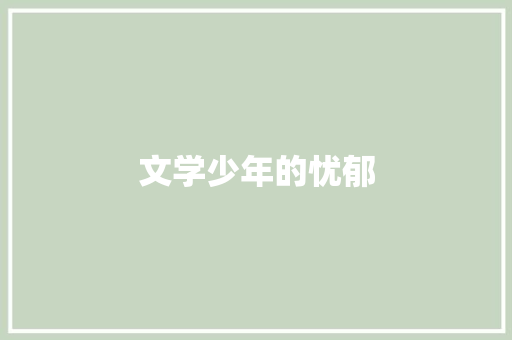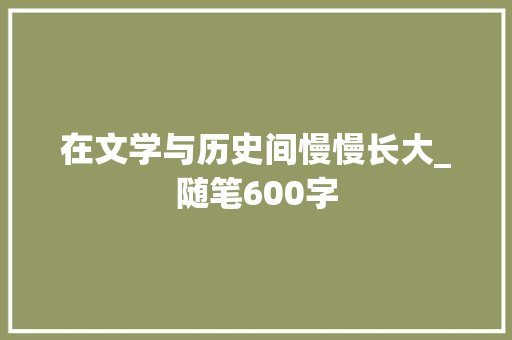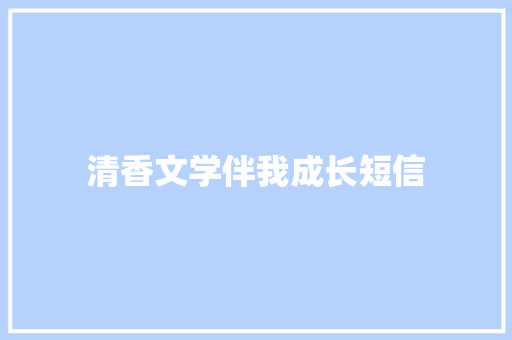作者:王秀涛(中国公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们仍旧须要巴金,这是本日很多人的共识。虽然巴金写作所面临的时期已经远去,但巴金生平的思考、探索、追求、奉献仍是值得继续的精神遗产,我们本日还能从他身上感想熏染到温暖和力量。他在作品中的诚挚与激情亲切、崇奉和空想、挣扎和呼喊,还是能让我们从中汲取“让生命着花”的勇气和希望。巴金的存在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作为二十世纪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已然超越了时期,得到了某种永恒性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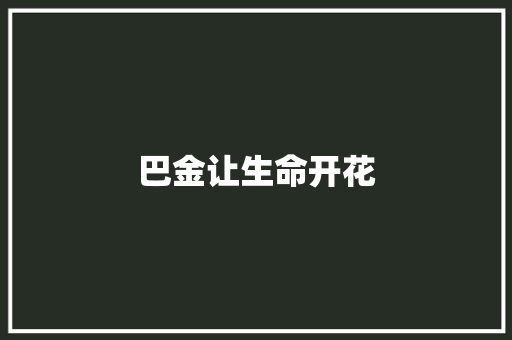
巴金(1904—2005)
1 谢绝无病呻吟,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
巴金的文学不雅观是非常明确的,他拿笔写作并不是出于文学的目的,完备是为了给自己的思想找到表达的路子,为自己的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他和鲁迅一样并不追求所谓“文学家”的名头,乃至声称“我不是文学家”。
比较于文学,巴金实在更希望从事实际的事情,“去做一点有用的事情”。他乃至认为,当一些人正为着光明、爱、幸福而奋斗、耐劳以至于去世亡时,那种躲在书堆里用稿纸花费生命的行为是“伪善”乃至是“该谩骂”的。因此巴金投入很大精力经营出版社,主编书本和报刊,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培植和文学救亡的详细奇迹,同时也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通过这些实际的事情来实现作为知识分子的代价。
《寒夜》 外语译本
巴金的文学不雅观念受到“五四”的影响,他曾坦言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之以是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师长西席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公民、爱生活、爱文学”。同时,巴金的文学创作从法国开始,伏尔泰、卢梭、左拉等人对他思想不雅观念和文学不雅观念的形成影响颇深。从在法国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灭亡》开始,巴金的文学创作就一贯致力于社会批驳,试图改造不合理的制度和旧的传统不雅观念,控诉、戳穿专制和阴郁,追求光明和自由。因此他的写作谢绝无病呻吟,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他始终关注的问题是若何生活得更好,或者若何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若何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有所贡献。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是从社会状况和现实人活泼身,目的是实现文学的现实功能。
在文学创作之前,巴金试图通过社会运动改变现实。他十五岁就打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成为激情亲切的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通过行动建立一个平等、公道的天下。但他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教条式的接管,而是想从中找到人生和社会的出路。巴金反对从理念和口号出发把“主义”教条化,曾经批评那些以思想为“事理”的做法。在他看来,事理“该当运用到实际问题上,由实际问题来证明它。假若事理不能阐明实际问题时,我们也不妨改动它”。因此他对付无政府主义从不是通盘的接管,而因此一种开放的态度在现实中加以改造,并与爱国主义、人性主义等其他思想相领悟。正由于如此,1936年,就徐懋庸对巴金的批评,鲁迅进行了回嘴,高度肯定巴金是“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纵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事情者联合的战斗的宣言”。就像1941年巴金在小说《火》第二部的后记中所说,他虽然崇奉国外的无政府主义,但仍旧是站在中国人的态度上看事情、发议论,并非机器演绎某种主义和思想。
值得把稳的是,巴金看重文学的功用性,他明确说他关于抗战的小说《火》是“一本宣扬的东西”。不过,文学在宣扬、教诲等方面的特有代价只能通过“文学”的办法来得到,因此他的作品始终遵照着文学创作的一样平常规律。1934年,巴金在面对“没有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批评时,回嘴批评者不顾及构成作品的艺术条件,只是用一个模子来批评作品,用政治纲领的模子来框作品,他认为这是对文学的侵害。巴金也反对理念化、口号化的写作,他说之以是在《寒夜》中末了照“批评家”的嘱咐加一声“哎哟哟,黎明”,并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的人已经没有力气呼唤“黎明”了。这种立足于现实和人的写作,授予其作品既属于时期又超越时期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永久性代价,这也是他在本日仍旧深受读者喜好的一个主要缘故原由。
1980年,巴金(右)与曹禺在巴金寓所闲步
2 好的文学作品是指路灯,好的作家是人生西席
“人为什么须要文学?”对付这个问题,巴金的回答是:“须要它来肃清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须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瞥见更多的光明。”
事实上,探索人生、探求人生的出路正是巴金走上文学道路的出发点。他始终信奉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样平常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巴金的写作一贯在回答“若何做人?若何做一个年夜大好人?”的问题,他的空想也一贯未变: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
巴金的文学始终关注青年群体。他希望青年有更好的人生,并通过笔下人物的彷徨、挣扎和选择试图为他们指出一条未来的道路。《家》便是以家族中的青年为原型的,巴金想要通过小说为同时期的年轻人控诉、申冤。他看到了太多官僚地主家庭中青年如何失落去了自由的权利,看到太多青春的生命遭到戕害,因此在作品中对青年的命运感同身受,并把自己也放进这些人物的生活中,和他们一起经历情绪的颠簸。在创作《灭亡》《家》等作品时,他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一起哭,一起笑,写的时候,仿佛在跟他们一同耐劳,一同挣扎。“青春是俏丽的东西。”这构成巴金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他便是要站在青年的一边,为青春和生命的自由发展而写作。
巴金关注青年,目的是要为他们探索如何实现生命的代价。在他看来,人生唯有和生活进行搏斗才能实现自己的代价。1931年在《〈激流〉总序》里,巴金写道:“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搏斗’。”要实现自由和空想,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得到。其余,捐躯和奉献也是实现生命代价不可短缺的。他主见“生命的着花”,也便是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个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着花。齐心专心为自己,生平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在这里,“生命的着花”意味着个人的生命要融入群体的生命才能实现更高的意义,由于“个体的生命随意马虎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得到永生”,哪怕捐躯自己的时候也不会孤独,由于“他所瞥见的只是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灭亡”。在抗战中,个人就要融入民族这个整体,哪怕为民族的生存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去世亡,由于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巴金所指出的新生和出路,武断了一大批青年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决心,很多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巴金始终关心自己的文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他要把从前辈作家那里得到的火种传给别人,“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楚中送安慰的人”,要把自己的同情、爱慕、眼泪分散给别人,这是作为一位作家该当具有的道德感。巴金认为文学具有两大浸染,潜移默化、塑造人们灵魂的浸染和宣扬的浸染,而前者更为主要,由于它会使作品具有“一些带永久性、长期性的东西”,让作品得到较长的生命力。因此,他非常重视文学对人的教养功能,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读者的指路灯,年轻读者更随意马虎把作家当作他们的人生西席。“究竟给读者什么呢?是养料还是毒药?”这是每个作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巴金正是通过“好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欢迎和认可,由于他的小说给了他们“一个疼痛的针砭,当头的一棒”,美好的结果是“他们都被唤醒了”。
1980年春,巴金(右一)与冰心(右二)访日期间留影
3 取出自己燃烧的心,讲心里的话
巴金从不把小说当作纯粹的艺术来看待,他认为作家不同于文学西席和评论家,不会刻意关注“人物要怎么样,情节要怎么样”这样的文学知识,相反,他写文章的时候,“常常忘却了自己,我切实其实变成了一个工具,我自己险些没有选择题材和形式的余地”。他的作品不靠技巧取胜,而是取出自己燃烧的心,讲心里的话,诚挚与激情亲切是他最主要的“武器”。他晚年所创作的《随想录》因此极大的勇气“讲真话”的文学典范,就像他曾经说过的,写作的最高境界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巴金作为具有天下视野的作家,从域外汲取了丰富的文学养料,在第一位老师卢梭的《后悔录》中学到老实,不讲假话。他高度评价《悲惨天下》和《复活》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虚假技巧的作品。他把托尔斯泰当作一壁镜子,“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撒谎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这些评价反响出巴金的文学不雅观念是非常朴素的。他从不想通过打扮自己媚谄于人,更不用甜言蜜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在巴金的作品里,很少看到繁芜的技巧、花哨的措辞、含混的隐喻或者暗示,由于他所追求的是更明白、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思想的表达、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把握、反响时期的深度和广度,这些才是文学魅力的来源,才能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的功能。
比较文学技巧,巴金更看重情绪的朴拙和诚挚。他希望用真情实感谢动别人,明确表示不喜好那些浓妆艳抹、忸怩作态、编造故事、散布谣言的作品。他谢绝成为那种“玩出各类花样”的“纯粹的作家”,时候提醒自己不要让作品成为“藏书家的所谓珍本”,成为“风雅绅商沽名钓誉的工具”。他曾经坦言创作《家》不是用笔墨技巧,而是用真实情绪打动读者,鼓舞他们提高。在《沉落》中,同样没有蕴藉、诙谐、技巧,但是里面跳动着这个时期的青年的心。巴金对内容至上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充满着朴素、诚挚而又动听的力量,也更随意马虎实现他所要达到的文学目的。
为达到这样的文学效果,巴金强调作家人格的主要性,强调生活和写作的统一,看重作品与人品的同等。作品要表现出作家的人格,而不能遮盖作者的内心,因此他十分厌烦“那些虚张声势、天花乱坠、把去世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乃至认为“纵然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在巴金心目中,“讲真话”便是作品与人品雷同一的范例表示。在作品中,他力求把自己写进去,把自己的经历、情绪、思想写进去。
有人问巴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他回答道:“我哪里有什么窍门!
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晚年巴金更是通过《随想录》直面自我,“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年夜胆坦露自己的短处,诚挚地反思历史和过去。其反思的深刻性和彻底性在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是罕见的。巴金的“讲真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影响已经超越个人,成为反思知识分子态度和操守、事关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思想资源。
对读者的重视使得巴金一向保持着与读者的联系和沟通。在他看来,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是由于读者买了书,更主要的是读者给作家“送来精神的养料”。这些养料成为作品的主要素材来源,以是他说自己写得最多的时候也便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同时巴金也极为重视读者评价,认为作品的最高裁判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是靠读者保留下来的,读者的接管和认可才是实现作家代价的终极路子。无论如何,文学只有做到“群众能接管,群众会喜好”,才是真的有成绩。这仍旧是本日的文学该当具有的一种意识:文学作品只有被读者所接管,才能真正成为时期发展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1日 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