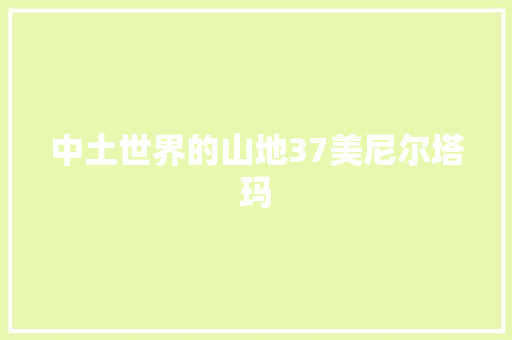该片于2018年6月23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同年10月26日在中海内地正式上映 。当时排片有点少,口碑却是不错。
影片讲述了妻子俄玛执意要去拉萨朝圣,却向丈夫罗尔基遮盖了自己身患绝症的实情。罗尔基知晓后劝其就治却遭谢绝,只能下决心陪她前行,然而同行的俄玛与前夫所生之子诺尔吾(赛却加饰)却对两人一贯心存心病。俄玛半路病发,罗尔基这才知道她此行是为了完成对前夫的承诺。俄玛去世,心情繁芜的罗尔基决心带着诺尔吾,连续俄玛未完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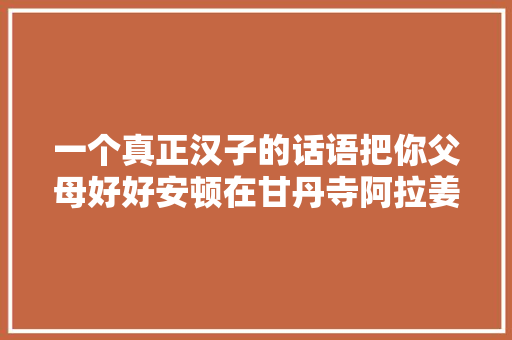
妻子亲口讲出,她磕头上路去拉萨朝拜,只是为了圆去世去的前夫托来的梦,临去世也要嘱托他让孩子带着他爹的擦擦做的书包——即作为个体的信物——去拉萨,大叔遭受的生理冲击是巨大的。
《阿拉姜色》剧照
于是我们非常理解他听说妻子执意“去世在路上”的缘由是她对前夫的爱之后那种妒嫉、失落望,也理解他听寺庙里的和尚说,两夫妻一起仙游,命真好,之后,不甘心地把照片撕成两半,分别贴在墙上。孩子把照片拼回来随身带着,他惊愕地创造自己在这个三口之家永久处于局外第四人的位置。妻子爱的是前夫,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妻子的错,孩子爱的是亲生父母,不爱这个后爹,更不是孩子的错。如果爱之伤是一个恒定值,总是须要一个人承受,那么善良的罗尔基便是那个注定耐劳的人。
爱情是不是公正的,看的不仅仅是行动,还有内心。罗尔基全心全意对待妻子,但妻子心里依然有前夫。至少,没有忘却和前夫的诺言,带着他的遗物踏上了路。
电影上半部分讲完了,下半部觉得才是导演要讲的意思。记得影片中有句话深得我心:统统都是缘分。也正是这句话,让罗尔基放下了心中的怨念,将心中的爱升华,连续了亡妻的朝圣。也这是下半部一大一小的主旋律。
《阿拉姜色》剧照
那张撕了又被粘回的照片实在已经在不经意间揭示了许多隐蔽在画面背后的事实——罗尔基无疑深爱俄玛,是那种最普通意义上的丈夫对妻子的爱,但他无疑又不足理解俄玛,就像他之前始终无法理解俄玛为什么要走这一程朝圣路一样。
同时,他当然也无法理解俄玛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诺尔吾,至少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把他视作一个有生理问题的叛逆儿童,从未曾设身处地去试着理解对方。
俄玛走时或许带着遗憾走的,罗尔基这样想到。没能去完成朝圣,没能去孝敬父母,没去当个好妈妈。可是这统统是不是罗尔基造成的呢,或许是或许不是。但是这些都不主要了。俄玛的溘然离世却逼迫他不得不开始试着去理解诺尔吾,去理解已逝的俄玛。他开始考试测验去照顾孤独无依的诺尔吾,尤其是在后者不慎弄伤了自己的脚之后。罗尔基在夜里趁诺尔吾熟睡之后,给他的伤口抹药的镜头,就极其耐心地描写了这种奇妙的生理变革。
《阿拉姜色》剧照
于是一个痛楚的决议之夜后,罗尔基决定接过妻子的“衣钵”,连续向拉萨进发,连续朝圣,而诺尔吾和小毛驴成为他朝圣路上的伴侣,帮助拖运物资。在这个过程中,罗尔基的个人的狭隘的爱与恨,逐步转让为对生命的尊重和实现对妻子承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实现了同自我的和解,逐渐放下狭隘与自私的爱与恨,扛起了博爱与任务。原来可以选择火车进拉萨的他,坚持用妻子的办法,朝拜提高,从而让这部影片在静默中实现了升华。
而朝拜的过程,自然也实现了罗尔基与诺尔吾的和解,这对路途中的冤家,逐步的在互帮互助中原谅了彼此,罗尔基教授诺尔吾一些人闹事理,比如“男人不能总走在人们的后面,不要老低着头”“男人的头发,剪掉后要放在人们踩不到的地方”等等,大略却深刻的生活道理,通过一个大男人,口口相传给面前这个不断终年夜的孩子,可以说在不经意间触动了不雅观众内心最优柔的地方。
在即将到达拉萨时,诺尔吾激动的一口气爬上了南山坡,从山坡上看到远处的布达拉宫,就那样悄悄的耸立着,随即返回问罗尔基,啥时候进拉萨城,而罗尔基则说好好整顿一番,理一下头发,整顿干净再进城,不焦急,影片在罗尔基为诺尔吾一剪一剪的理发过程中,闭幕。
也有一句真正成熟的男人的话语:“把你父母好好安顿在甘丹寺。”对着诺尔吾说这。
“阿拉姜色”为实际上源于藏语的一种音译,指的是一首藏族民歌,意思为“请您干了这杯美酒”。俄玛对付罗尔基来说便是一壶美酒。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鲍勃·迪伦这句歌词恰好可以作为罗尔基这样一个中年男人的完美注脚。一次次的妒忌与不甘,一次次的哑忍与泪水,但他在朝圣之路上逐步了放下了狭隘的血缘不雅观念,逐步超脱了自私的俗世情绪。人只有在哑忍中放下,或者超脱于俗世情绪,才能真正活出大我。罗尔基在这一起上,真正活出了大我。